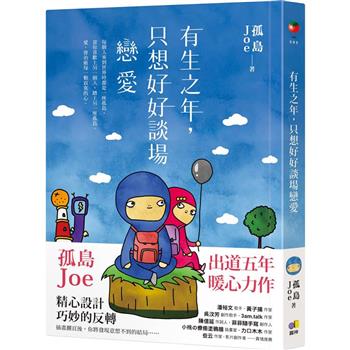第一話
一
風聲一嘯,輕易拂去萬物根基。
越過謊言綿延的山,浸透謗議叢生的雨,悲慟伴潮汐升漲,淚腺宛如蒼空。比擬素白絨花飄零,幾個轉身,幾番起落。而後墜入泥濘,歸於塵埃。
唯有闃靜沉澱千年,方能心平氣和提及「曾經」。
那些「曾經」,在酷暑嚴寒中刻骨銘心。它們消解於雲淡風輕,重現於被蠶食至斑駁的蜃樓幻景,經漫長年月去噪打磨,又加諸柔光與濾鏡,最終竟有了幾分和暖氣象。
氣象殊異,幸而你依舊是你。
給予我索驥之圖,不能視一切為虛無。
二
殘秋九月,晴天霹靂落下,感情線走出一個新分叉。
「夕夜,妳先冷靜,我的意思是,妳還像交往之前那樣把我當學長,我們一樣出去,我要能找回以前的感覺我們就繼續,好嗎?」
暮靄從落地玻璃窗外擠進來,使店裡正在播放的慢搖泰國歌像是因空間不足而變得鬱結壓抑。
冗長的沉默中,手指關節因緊壓著玻璃杯冰冷的外壁而麻木。
某種情緒走成醫院裡垂死者心電監護儀所呈現的圖形,上下幾個大幅度顛簸,繼而扯出一條消失於盡頭的水平線。
夕夜在沉香色光線中緩慢眨眼,揚起空漠的聲音:「她是誰?」
「她?」男生臉上閃過一絲慌亂。
「你知道我在說誰。」一字一頓。
視線移向身側的地面。「是……單若水。但不管有沒有她,我們都不可能再繼續下去,夕夜妳實在太……讓我怎麼說呢……」
女生趕在對方說出更傷人的話之前突兀地打斷:「你說完了嗎?可以走了嗎?拜託別再來煩我了好嗎?噁心。」
一如既往的平靜語氣使男生備受打擊,滿臉錯愕地逃離了分手現場。
其實早該有所覺察,每次出去約會時他都會說起單若水。
一個女生,為倒追某男生居然大喇喇地搬到男生寢室去住了二十多天,宿舍管理員怎麼趕都賴著不走;聚餐時玩真心話大冒險,居然當著很多男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脫黑絲襪;喝HIGH了居然在回校的地鐵裡跳鋼管舞,驚擾得連員警都出動維持秩序……天知道這種人怎麼會是國貿系系花。男友一遍遍地嘮叨八卦,結果連夕夜都對單若水的事蹟了若指掌。
雖然每次都刻意加上批判評價,但提及次數多得反常,本身就意味著關注。
雖然嘴上說瞧不起那種女生,但心裡卻覺得那是種活潑開朗的好個性。
「夕夜妳實在太認真,讓身邊的人也輕鬆不了。」
「妳漂亮、聰明、有氣質、有涵養、一直很安靜,但是太安靜,在妳身邊就像進了墳塋。」
「對不起,我還在要玩樂要瘋癲的年紀。」
有些話,前人做好了鋪墊,後人的重複也就出現在意料之中,熟稔於心。
大二暑假,第十一次分手,還是一樣的原因,還是一樣猝不及防,甚至比以往傷得更深,因為總覺得「11」是自己的幸運數字,第十一個或許會是轉折。
真可笑,像個傻瓜。
總是無視自己被不斷拋棄的命運,懷揣著可悲的忐忑,希冀未來會出現轉折。
一扇門,一條路,還是一束光?連自己都不知道在期待什麼。
母親去世前說過,是因為有期待人才會變得不幸。
內心像拉滅了燈的長廊。夕夜悵然若失地望著面前沒喝完的兩杯冰飲,身體的某部分神經向大腦發出警覺信號,幾秒後才感受到停留在右腳踝外側的毛茸茸觸覺,又愣過一秒,才從座位上彈跳而起:「啊啊啊啊啊老鼠……有老鼠……有……兔、兔子?」
揉了揉模糊的眼睛,再次定焦,兔子君也正一臉無辜地用紅眼睛瞪著自己。
什麼情況?
「看來妳不冰山嘛。」懶懶的男聲從鄰桌傳來。
視線抬高一點,桌上擺著書、飲料、itouch、上網本、小籠子?幾片被咬過的青菜葉?
再抬高一點,囫圇掠過面頰眼眸,最終定格於深棕髮際。
某些似曾相識的細節受記憶委派而來,點燃致人心悸暈眩的引線。二十歲,十九歲,十八歲,十七歲,十六歲,任憑時光在面前逆向洶湧流淌,重又憶起那個曾讓自己失去重心步履踉蹌的人,以及與他的身影一同暗地生長的欣喜與沮喪……
所有的少女情懷、少年心氣,以壓倒性的姿態與毀滅性的氣勢,捲土重來。
此時方才知曉,希冀的終點所歸何方。
失落的戀慕所歸何方。
固守成習的徒然期待所歸何方。
三
其實並不十分相像,只是整體都有那種年輕男生獨具的健康又英俊的氣息,其中又都摻雜著幾分略超年齡的敏銳和沉著。
一貫不知該如何與初識者自然相處的夕夜,卻因為這麼點熟悉感幾乎立刻就和鄰座的男生坐到一起,毫無障礙地溝通起來。
女生抽抽鼻子:「再確認一遍,遠親中也沒有姓賀的嗎?」
「沒有。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沒有一個姓賀。問這麼奇怪的問題幹麼?」
「因為你長得很像我初戀男友。」
「可以自動理解為:我是妳最愛的類型嗎?」
長吁一口氣:「不要拿剛失戀的人打趣。」
「沒打趣。」男生微微蹙眉,有點可愛的委屈神情從臉上一閃而過,語氣卻依然冷冰冰,給人宛如齒輪錯位的不協調感,「我很認真。嗯……為了表示誠意我也確認一下,妳初戀男友不姓程吧?」
「姓賀啊,要不然剛才問那麼多遍幹麼?誰姓程?」
「我爸。」
女生不解地眨眨眼睛。
男生繼續解釋道:「我是私生子,跟我媽姓。」
思維有點短路。真的假的?怎麼會有人以這麼隨意的語氣把這麼重要的身世告訴第一次見面的人?反應了長長的幾秒才領悟對方的重點,內心有點無力:「我怎麼可能對你爸那種年紀的老人家感興趣?」
「很難說哦,妳這種怪人。」
「哪裡怪了?」
「男人用花言巧語腳踩兩條船的手段一下就被妳識破,分手後也不像一般女生怨天尤人哭哭啼啼,然而,就是這樣睿智而堅強的女性,」往嘴裡填了口蛋糕,賣了個不大不小的關子,吃完才繼續說下去,「竟然被可愛的小白兔嚇得花容失色、淚流滿面。」
「我以為是老鼠。」
「竟然被可愛的小白鼠嚇得花容失色淚流滿面。」男生改口道。認真嚴肅的神情讓人實在無法判斷真假虛實。
回想起剛才一瞬間的失態,夕夜有點惱羞成怒:「你才是怪人吧。沒見過男生帶著小白兔來咖啡館餵青菜。話說回來,門口明明寫著『禁止攜帶寵物入內』。」
「這不是寵物,是約會對象。」
夕夜不禁打了個寒顫:「快說這是冷笑話,不然我三秒鐘之內就會逃走。」
「不是冷笑話。」男生故意等了三秒才解釋,「大概因為我是個礙眼的燈泡,我死黨的女友一直給我介紹各種各樣的女人,想把我從她男友身邊打發走,但是每次帶來的女人都被我氣跑,今天她絕望了,沒帶人,帶來了她們寢室養的兔子。前因後果就是這樣。」
「聽起來挺可憐,不過仔細一想,誰讓你那麼挑剔。」
「我喜歡有點骨氣的女人,不喜歡過分主動的腦殘系。」
都是嘴上說說冠冕堂皇的話,根本沒有人會以此準則左右喜好。
讀高中時,喜歡的男生喜歡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有點繞的關係。
乍看之下,那個女孩無論哪方面都不如自己,但細究起來,擔任班長的她因積極主動、活潑可愛的「好個性」而廣受好評——只有熟悉她如夕夜者才能看透那全是偽裝。就這方面而言,夕夜覺得自己踩著風火輪都追不上。
該機靈的時候機靈,該懵懂的時候懵懂,該耍白癡的時候耍白癡,該裝可愛的時候裝可愛,偽裝到收放自如的境界,相貌天資再平庸也能成大眾情人。
夕夜不是不懂這道理,只是許多年來,依然學不會。
在這喧囂浮躁時代,有骨氣,只不過多一重束縛而已。
男生的這句話,是她當天最後的清晰記憶。
四
在陌生環境中醒來,時空都令人感到彆扭,夕夜撐著床沿坐直,環顧四周,是旅館房間。雖然意外但沒有體會到受驚後的虛熱,也沒有緊張感。俯身只見床邊自己的涼鞋被擺放得很整齊,但由於懶得處理鞋帶,索性就赤腳踩著地毯往外走去。
套間的會客廳沙發上斜靠著昨天在咖啡館遇見的男生,左手鬆鬆地枕在後腦下,從夕夜的角度其實看不出是睡著了還是沒睡著,但聽得見熟睡的綿長呼吸。
這種狀況讓女生有點左右為難。搞不懂究竟發生了什麼使事態變成眼下這樣,又不能叫醒唯一的知情者問個明白;就常理而言不該不清不楚地繼續留在這裡,又不能不知會對方什麼都不解釋就一走了之。
正猶豫著,一小團白色的東西從視界中橫躥過去,夕夜不由自主發出一聲輕微的「欸」。須臾便看清,又是那隻兔子。但正是這聲「欸」,成功導致男生窸窸窣窣坐起來看見了她。
女生努力讓表情和聲音顯得自然:「睡得真淺。」
「從小養成的習慣。」男生戴上眼鏡,讓出身側的一個空位示意她坐過去。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
「這要問妳,」男生挑挑眉毛,笑得亦正亦邪,「為什麼喝RED EYE都能倒。」
「酒嗎?我喝過?」
「我點的,我一杯兔子一杯你一杯。」
「兔子……啊,那是酒?我看兔子喝以為是飲料。」有點哭笑不得,「哪個正常人會餵兔子喝酒?」
「嫦娥吧我想。」男生板著面孔講冷笑話這一套夕夜已經適應了,「只不過是啤酒加番茄汁,妳居然能不省人事九小時,有什麼立場跟我提『正常』二字?一般而言,正常人用它來解酒。」
「我本來就是一點啤酒都不能沾,而且不是都說,心情不好更容易醉嗎?」夕夜的目光在地上轉,發現那隻兔子這回安分地鑽進籠子睡下了。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曾有你的天氣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7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曾有你的天氣
夕陽瀰漫在高中教室裡,
美的不是溫暖的夕陽,
而是從我的視角看過去的,你曾經的桌椅。
玻璃窗外狂走著沙石,
美的不是疾捲的風,
而是從我的視角看過去,你曾經站立的位置。
鐵絲網分隔著被白雪覆蓋的操場,
美的不是純潔的白雪,
而是我曾站在那裡,
一轉頭,就看見了你。
在我的眼裡,天氣沒有好壞之分,
那些有特殊意義的全是因為曾經有你。
氣象殊異,
可於我而言,你永遠是你。
《曾有你的天氣》是《8分鐘的溫暖》與《日界線》中人物在大學時代的故事,風格又有些變化。《曾有你的天氣》是作者實際生活的回憶和記錄,從大四到就業,從學業到感情,每段故事真實而美麗。小說結局令人意外,夢境與現實互相交錯,殘酷與美好並存。
作者簡介:
夏茗悠
在網上搜索夏茗悠,你會得到80後,青春文學,美女作家,人氣寫手,北大才女……
有關夏茗悠的頭銜,你會發現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萌芽》雜誌明星作者,陽光雨辰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監,《光年紀》雜誌主編……
章節試閱
第一話
一
風聲一嘯,輕易拂去萬物根基。
越過謊言綿延的山,浸透謗議叢生的雨,悲慟伴潮汐升漲,淚腺宛如蒼空。比擬素白絨花飄零,幾個轉身,幾番起落。而後墜入泥濘,歸於塵埃。
唯有闃靜沉澱千年,方能心平氣和提及「曾經」。
那些「曾經」,在酷暑嚴寒中刻骨銘心。它們消解於雲淡風輕,重現於被蠶食至斑駁的蜃樓幻景,經漫長年月去噪打磨,又加諸柔光與濾鏡,最終竟有了幾分和暖氣象。
氣象殊異,幸而你依舊是你。
給予我索驥之圖,不能視一切為虛無。
二
殘秋九月,晴天霹靂落下,感情線走出一個新分叉。
「夕夜,妳先冷靜...
一
風聲一嘯,輕易拂去萬物根基。
越過謊言綿延的山,浸透謗議叢生的雨,悲慟伴潮汐升漲,淚腺宛如蒼空。比擬素白絨花飄零,幾個轉身,幾番起落。而後墜入泥濘,歸於塵埃。
唯有闃靜沉澱千年,方能心平氣和提及「曾經」。
那些「曾經」,在酷暑嚴寒中刻骨銘心。它們消解於雲淡風輕,重現於被蠶食至斑駁的蜃樓幻景,經漫長年月去噪打磨,又加諸柔光與濾鏡,最終竟有了幾分和暖氣象。
氣象殊異,幸而你依舊是你。
給予我索驥之圖,不能視一切為虛無。
二
殘秋九月,晴天霹靂落下,感情線走出一個新分叉。
「夕夜,妳先冷靜...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夏茗悠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3-06-20 ISBN/ISSN:978957104909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