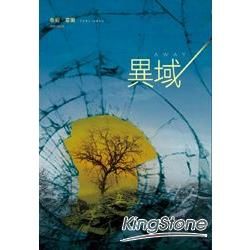◎越界的少女,失控的命運──新銳作家泰莉.霍爾,一鳴驚人的《邊界》系列二部曲!
◎《青少年之聲雜誌》盛讚:「文筆引人入勝!喜愛飢餓遊戲的讀者一定也會喜歡。」
◎全美逾12,500位學生票選肯定!2011國際閱讀學會/美國童書協會(IRA/CBC)年度選書。
充滿生死抉擇與黑暗陰謀的冒險之旅。
頁頁充滿令人心跳加速的懸疑時刻!
封鎖全國邊境的防衛系統中,有一部份被稱做「戰線」。
為了拯救一名陌生男孩性命垂危的父親,瑞秋決定帶著藥品,冒險私渡。
如今她置身異域──一個慘遭禁用武器轟炸,又被政府所遺棄的地方;
受輻射影響的人們身懷異能、劃分為數股勢力的地方;
父親多年前失去蹤跡的地方。
在這裡,沒有科技、沒有電力、沒有醫療用品......就連希望也所剩無幾。
但在這片荒土上,瑞秋找到了人生的意義。
只要時猶未晚。
作者簡介
泰莉.霍爾
出生於東京,畢業於剛薩加大學(Gonzaga University)。生活中多數時間投入寫作之中,其他時候則忙於參詳萬物意涵,期望能賦予事物新意。《邊界》是霍爾的首部著作,作者現居於美國華盛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