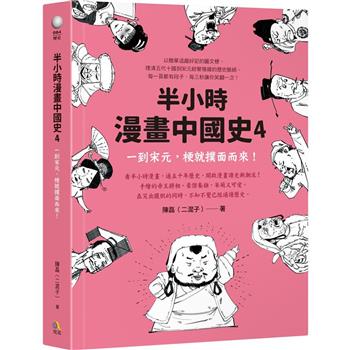※收錄番外篇──〈艾力克斯〉!
曾經愛過的,現在愛著的;
三個絕望的人,一場絕望的愛。
愛是一種癡,醒不來、出不去,越明白越要命!
大結局扣人心弦──《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報》《出版人週報》一致推薦!
★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自為愛女選書,購入系列作《妄愛》與《唯愛》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全球小說譯本已超過三十種語言
★榮獲科克斯書評星級推薦
★榮獲2013年好讀網精選獎提名其為最佳青少年幻想及科幻小說
★獲選為亞馬遜書店2013年最佳圖書
過去與現在,平靜與戰鬥,真愛與最愛──
她到底能挽回哪些?
艾力克斯沒死!麗娜先是欣喜若狂,接著卻如墜冰窟。
在他為她搏命付出之後,她以為已死的愛人活著回來了──
但對方那雙冰冷眼眸中的她,卻早已變心。
為了阻止叛軍,政府的監察機構無孔不入的滲透,
眼前情況危及,她必須專注,
但她無法逃離愛情帶給她的癡狂痛苦。
陪她逃亡的男人真心不容質疑;與她共患難的男子誠意毫無雜質。
麗娜的心被撕成兩半、難以抉擇,誰也不能滿足。
也許愛真是一種病,也許最安全的,
就是沒有愛的生活……
媒體佳評
「在開始閱讀之前,讀者應該關掉手機,並取消日程安排,因為一旦打開了這本書,他們就無法停止!」──《科克斯》書評
「對青少年讀者而言,哪裡還有一種故事主軸比告訴他們:選擇你想要的生活,而不只是服從要更好?這獲得巨大成功的三部曲,應該在震耳如爆炸的伴奏與廣告下出場!」──《Booklist》書評
「這悲傷的故事利用了所有形式去闡述愛情,還特別用力去談愛的選擇與愛的自由;無論這手法是對是錯,都牢牢地將讀者的眼光釘在書頁上。奧立佛將最好的,留到了最後。」──《學校圖書館期刊》
「我無法不用溺愛的語調去闡述《輓愛》的最後一幕,那也許是整個系列中最淒美的部分……不管奧立佛接下來打算寫什麼,我都等不及看了。」──英迪格書店評論
「看到最後一頁,我想提醒自己,也希望我的孩子知道這件事:『讓高牆倒下』。不要在自己周圍建立路障,否則你將永遠生活在恐懼中。我極力推薦大家這個系列。愛情不是一種疾病。恐懼是。」──諾貝爾蜂巢獎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