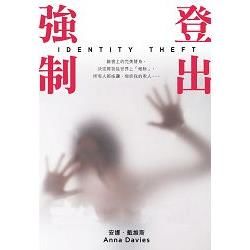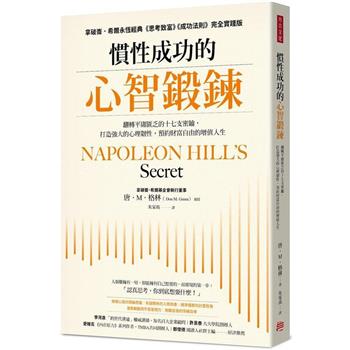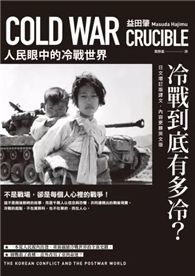我迅速地咬了一口三明治,並從地板上拿起筆記型電腦,打開電源。在等待電腦開機的同時,不知不覺想到克里希先生對社群網站的不屑。他當然不知道我經常在網路上搜尋我自己,我甚至很清楚Google網站會出現的搜尋結果:一連串漂亮的辯論戰績、榮譽榜和學業成就奬。我在搜尋框裡,打上我的名字。
我瀏覽過第一頁,它和以前一樣,全是辯論紀錄和「鐘奬」的最佳提名人,當然也不會再出現姬莉高一使用過的輕型網誌Tumblr。但這時,第三頁的網頁底部有個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海莉‧凱瑟琳‧威斯汀的臉書。
我按下連結。這可能是和我同名同姓的海莉‧凱瑟琳。
我眨眨眼。
那是一張全身照,照片裡的女孩身上塗滿了奶油,幾乎快看不到她身上的彩虹色比基尼。她對著相機開懷大笑,顯然很開心被拍照。淺灰色的眼睛,深棕色的頭髮滑過瘦削的肩膀。我點了一下照片,照片立刻放大,充滿整個螢幕。我倒抽一口氣,抬手摀住我的嘴。賽迪抓住機會搶走三明治,跳下床舖,但我沒有阻止牠。我的視線無法離開那個酒渦、瀏海下的美人尖,以及長長手臂上的雀斑。猴子手。這個辭冒了出來。小時候在遊樂場玩耍時,姬莉都這樣叫我。
這個臉書個人首頁是公開的,於是我匆忙地往下瀏覽,想弄清楚怎麼會有這張照片、這個女孩──也就是我,但又不是我,更不可能是我。這沒有道理,它就像我無法理解的哲學問題,但必定有個說法。
上午九點零二分時,有個狀態更新,而我當時正在上英文先修班,在討論《馬克白》劇本裡的魔法和迷信的涵義。
週間狂歡,棒呆了。如果再加上大學帥哥,滿分!
狀態下方有兩個留言,其中一個是姬莉寫的。
我以為妳的數學很棒?不過,顯然我錯了,因為海莉這個名字永遠不可能和帥哥放在一起。
應該是週間大哭吧……可憐那些必須和妳在一起的帥哥。
這必定是姬莉的傑作。我的臉頰發燙,我瘋狂地點開其他照片。同一個女孩穿著超短的紅色短褲和白色絨毛小可愛,及肩的頭髮上戴著聖誕老公公的帽子,深棕色的頭髮上有金色的挑染。我從沒染過頭髮。那女孩和一個肌肉男在擁吻。我從沒接過吻。
但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照片上的,的確是我。我看著她的照片,「我」又一次和那個男人接吻。但她並沒有看著男伴,而是盯著鏡頭瞧,她的眼睛張得大大的,臉上的微笑足以去拍牙膏廣告了。我的舌頭滑過牙齒,發現儘管經過數年的牙齒矯正,我的門牙還是突出的。
這不是我。我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可是……
我閉上眼睛,按摩著太陽穴。我的思緒突然跳回到克里希先生的辦公室外,等待中的亞當。沒錯。克里希先生必定也提醒了他,關於社群網站的事,所以他才想出這個方法來扯我後腿。他知道我沒有臉書帳號,也知道我可能永遠不會發現這個首頁。他知道如果我也成為候選人之一,他就沒有機會得到安斯渥斯奬學金了。
我放開拳頭,發現掌心之中有深深的指甲痕。呼吸。我要列印出這個無中生有的首頁,帶著它去找克里希先生理論,並要求取消亞當申請奬學金的資格。一切都會沒事的。
既然搞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後果,於是我允許自己瀏覽整個首頁。我的朋友人數已經累積到四十個,還上傳了十七張照片。假海莉似乎參加某所大學的兄弟會派對。又一張她和一個男生的接吻照,她背心的吊帶滑落,露出清晰可見的胸罩肩帶。
淚水刺痛了我的眼睛。這一點都不有趣。
一段回憶湧進我的腦海。
九年級的時候,我生平第一次得到低於B的成績。我的幾何學報告只得到一個C-,不過我知道這是因為我根本沒有花心思讀書。我瞥了亞當的報告一眼,看他得到A。
就是那個時候,我發現我必須退出旱冰曲棍球隊,專心在學業上。再加上,那個秋天,我已經很清楚我在社交方面,永遠無法和姬莉、英格麗或是艾蜜莉相比。學業是我唯一的強項。如果這表示我必須完全放棄社交生活,我也願意。於是我去找史密斯教練討論,但她不願意讓我私下退出球隊,她要求我參加星期六的練習,順便歸還制服。我試著向姬莉、英格麗和艾蜜莉解釋退出球隊的原因,我告訴她們我必須專心讀書,我無法像她們一樣滿足於不上不下的成績,但我不認為她們理解我即將採取的生活態度。
那天下午之前,一切如常,直到我發現她們都沒有來找我。我們星期六下午都會一起出去玩,不是逛購物中心、看電影,就是在大街上閒逛。而且我並沒有漏接的電話或未讀的簡訊,我上網檢視電子信箱,只收到學校最受歡迎的男同學的信件,他們告訴我,我這個人有多麼的失敗。
我檢視臉書時,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她們掃瞄了所有我寫過的HIKE名單,並且以我愛的男人為標題,貼在我的塗鴉牆上。最糟糕的是,我根本沒喜歡過我寫的那些男同學。我不認為喬恩‧偉伯比雷神漢斯沃兄弟帥氣,也不覺得把我的初吻獻給賽斯‧柯恩是何等的光榮,更不想和馬克斯‧懷特發生性關係。我之所以寫那些名單,只是因為姬莉一直把這些男同學掛在嘴上,而我又想融入話題,只好附和她們。
我當時立刻衝出屋子,跳上腳踏車,去找亞當。他知道如何查詢電腦的IP位址。隔天早上,我刪除了臉書帳號,封鎖電子信箱,並且一步步地移除網路上所有的私人資料。
我絕不讓姬莉看出我有多難過,絕對不能讓她稱心如意。我決心重塑自己的形象。我捨棄了色彩明亮的緊身上衣和貼身牛仔褲、撕下布告欄上的照片,甚至改變了我的筆跡,從經常以紫色原子筆寫的、圓而大的書寫體,改成小而整齊的印刷體。
沒有人知道我其實很脆弱──亞當除外。他是唯一一個看過我哭的人。隔天,我去學校上學時,刻意忽略耳邊的流言蜚語。事情總有一天會平靜下來的,但是,怒氣和傷痕永遠不會消失。我在別人的眼中,向來都不太正常。他們覺得我是為了分數不擇手段的怪胎,永遠不會有男人來向我告白──如果有,那就是奇蹟了,太陽要從西邊出來了。
我從包包裡抓出手機,好恨通訊錄裡的第一個人就是亞當。我討厭他,我希望他被退學,希望他搬得遠遠的,讓我從此看不到這個人。
電話只響了一聲,他就接起來了。「海莉,怎麼了?」
「你很清楚我為什麼找你。」我聲音低沉地說。
「我雖然才華洋溢,但就是不會讀心術,至少,現在還不會。」亞當慢條斯理地說。「妳有什麼需要?要請我教妳做微積分作業?」
「我不想在電話裡跟你談。我們半個小時後,在醜怪馬克杯見。」我的聲音在發抖。
「等等,什麼?」亞當問。「我在寫作業,不能明天再談嗎?」
「不行!」我爆發了。「你今晚就必須跟我把話講清楚。我知道你做了什麼好事,你必須彌補,否則我就報警,告你騷擾。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海莉,妳到底在說什麼?我又沒有騷擾妳。我整個暑假都沒跟妳說過話耶。」
「閉嘴!」我尖叫出來。「你安靜,聽我說。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我必須跟你談。現在。」
「我知道妳不是開玩笑,但我不知道妳到底在說什麼,也不知道妳為什麼對我大吼大叫。」
「你會去醜怪馬克杯嗎?」我問,試著克制歇斯底里尖叫的衝動。
「好,我去。醜怪馬克杯,半小時後。我等不及去看失控的海莉了。」他挖苦我。
我根本不打算回應他,直接掛掉電話,砰地闔上筆電,然後朝樓梯跑去。
「我去鎮上自修!」我大喊著。但我白喊了,媽媽和傑弗森已經出門去吃晚餐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衝到醜怪馬克杯,打破了以往的紀錄。我環視一圈,沒看到亞當,只看到波西、一位主修哲學的咖啡師傅、幾個戴著超大耳機的孤單學生,以及在角落裡餵對方吃巧克力蛋糕的情侶。
「有事嗎,海莉?」波西斜倚著櫃檯問。
「沒有。」我乾淨俐落地回答。大門上方的時鐘指著七點二十五分。如果到了七點半,亞當還沒到,我就打電話報警。所以我還有四分半鐘的時間,思考如何向班布里奇警察局的警察解釋為何偽造的臉書首頁可以列入合法的緊急事故。
「和以前一樣嗎?」波西和善地問,並且已經朝濃縮咖啡機轉身過去。
「對。」我現在很激動,根本不需要再喝咖啡了,更不需要波西正在製作的大杯濃縮拿鐵。但我知道,如果我不點咖啡,他就會困惑地問問題,而我已經夠煩了。我來到小店的後方,在破舊的紫色絲絨情人沙發的邊緣,坐下來。亞當到底以為他是誰?難道他不知道,以我的聰明才智,他怎麼騙得過我?我無法相信,他居然以為我可以如此輕易地被整垮。
店門打開,我一看到穿著大學辯論校隊外套的亞當,立刻想放聲大駡,想衝過去,把他的眼睛挖出來。這個以為辯論校隊外套是項不錯的時尚穿著的傢伙,怎麼敢整我?
「這裡。」我生氣地喊著。
亞當對我點點頭,然後朝櫃檯走去點飲料。
「待會再點。」我忿恨地說。
亞當朝我走來,說:「真是的,妳甚至不讓我點咖啡?看來,事情比我想像的更嚴重。」他雖然以玩笑的語氣說話,但眉頭卻憂心地皺了起來。「怎麼了?」他連坐都來不及坐,就開口問了。
「你知道的,」我直視他的眼睛,設法冷靜地說話。我可以隱約看到他眼鏡鏡片上的我的倒影,我試著表現得更加冷靜。如果他知道我很難過,他就贏了。「臉書首頁。」
他一臉困惑地低頭看著我,說:「妳是想告訴我,妳終於想開了,決定加入二十一世紀的行列?恭喜。我會小心不加妳朋友,妳也不用大吼大叫地指控我騷擾。」
「不。」我站起來,這樣才可以直視他的眼睛說話。「你。偽造。一個。臉書。首頁。來騷擾。我。」我咬牙切齒地說。
「海莉,妳在說什麼?我沒時間跟妳瞎耗。」
「我就有時間嗎?」我幾乎尖叫出來。端著拿鐵朝我們走來的波西,嚇得停下腳步。
我放低音量,說:「你看,」我拿出筆電,叫出網頁。「亞當,我發現它了。」
亞當抓住筆電,而波西快步走到桌邊,他幾乎是把拿鐵丟在我的面前。我喝了一大口,滾燙的液體燒灼上頷,我更憤怒了。
「這不是我做的。而且這又不是妳。」亞當搖搖頭,把筆電遞過來給我。
「什麼意思?」我的確期待他否認那是他的傑作,卻沒想到他也否認那個女孩是我。「那是誰?」
「妳又不是兄弟會派對舞后,對吧?這可能是某個人,用Photoshop組合起來的,而且他的技術非常的好。他們可能找到和妳長得很像的人的照片,再跟其他人的照片重組在一起。」
「可能嗎?」我小聲地問,對他的懷疑開始動搖了。
「不知道。」亞當坦承道。「但這不是我做的,海莉。我不是為達目地,不擇手段的人。沒錯,我是很想得到安斯渥斯奬學金,妳也是,但我們從未讓競爭破壞兩人之間的友誼,不是嗎?」
「對,可是……」我發現我對他的懷疑,全是因為我已經斷定就是他在耍詭計。
亞當嘆口氣,說:「看來,妳今年會不太好過。」
我瞇眼,說:「你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聽著,海莉,妳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這我能瞭解,因為我也是。但妳不能任由別人來影響妳。沒錯,被人惡搞,很倒楣,但真的不是我。這只是某人在惡作劇,妳不需要太緊張,又不是有上百萬的人在網路上搜尋妳的資訊、調查妳。」
我瞪著他。他在開玩笑嗎?「我在乎的是安斯渥斯提名委員會。」我乾脆地說。
他恍然大悟,說:「妳懷疑有人企圖抹黑陷害妳?」
「對!」我憤怒地說。我待不下去了,不想在扮演業餘偵探了。
「海莉。」亞當的語氣堅定。他朝我的手伸過來,但被我揮開了。
「我很遺憾妳遇到這樣的麻煩。」他任由他的手垂落在大腿上。「海莉,看著我。」
「幹麼?」我不客氣地問。
「我知道妳懷疑我為了得到奬學金,而設計陷害妳。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能讓妳相信我,但我真的沒做。我永遠不會傷害妳。沒錯,我們這樣互相較勁,很過癮,但我不會……不會……」他沒把話說完。
「沒關係。」我緊閉雙眼,不讓眼淚流下來。我不是因為亞當的話感動得想哭,而是因為就算敵人不是亞當,也另有其人,有某個憎恨我的人,設法抹黑陷害我。
亞當疑惑地看著我,說:「有關係。」
「對。」我附和著。「但我什麼都不能做。」我看著有著一圈圈咖啡印痕的木桌。如果我看著他,很可能會失控,讓已經占優勢的他,更得意洋洋。而讓我更恨的是,我發現沒有人這樣對待他。他沒有很多的朋友,但他並不像我一樣不受歡迎。我不需要他的同情。
「我至少可以陪妳坐一會兒,直到妳的手不再發抖。」他說。
我用力地雙手合握,又發現這樣好像祈禱的手勢,於是把手放進口袋裡。「我沒事,非常的好。Je suis très bien。」我幾乎是喊出來的,我甚至用到法語,這表示我真的失控了。
亞當圓睜著雙眼,說:「哇,海莉,別慌。沒事的,只不過是有人開玩笑,開過了頭。我賭只要妳把事情告訴克里希先生,就會沒事的。而且現在好像只有姬莉和她的同伙看到而已。我不認為安斯渥斯提名委員會已經開始調查我們了。還有,我並沒有冒犯妳的意思,但妳現在都還沒被提名,而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進入決賽。」
「我知道,但……」
「聽著,如果妳想,我可以侵入姬莉的電子信箱,查看看是否有不對勁的地方。我跟妳打賭,她所有的密碼一定都是spray tan,用噴劑把肌膚噴成小麥色。」
「你覺得是她做的?」我沒有理會亞當的笑話。我回想著姬莉今早的留言。就連輸家也加入臉書了。她在諷刺我嗎?而我甚至沒有會意過來?這個可能性很高。
「她有可能,但也可能是妳去參加的辯論營裡的人。妳跟他們提過申請奬學金的事嗎?」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強制登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9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驚悚/懸疑小說 |
$ 246 |
驚悚/懸疑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強制登出
來自亞馬遜讀者APirsig的警告:一旦翻開這本書,你就再也停不下來了。
臉書上的完美替身,決定將我從世界上「刪除」,所有人都按讚,包括我的家人……
妳聽過這個傳說嗎?
這世界上有一個人和妳長得一模一樣,
妳們既不是雙胞胎,也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一旦妳看到她,那天就是妳的死期……
海莉沒有臉書帳號。
為了進入一個頗負盛名、極為優渥的大學獎學金獲選名單,
她有很多工作和目標需要完成,不能冒著在臉書上留下壞印象的風險。
要是像她以前的好朋友一樣(以前,因為她現在已經沒有朋友了。)
在臉書上炫耀玩樂的照片、留下令人遐想的文字,
她的獎學金之路就徹底毀了!
但有一天,網路上突然出現她的個人臉書,還有她飲酒作樂的照片。
海莉認定是某個聰明的競爭對手想害她喪失資格,
直到有張照片拍到了她從沒給別人看過的胎記。
照片裡的人難道真的是她?
但她根本沒去過那個地方,沒有喝酒,更沒有雙胞胎姊妹……
那個和海莉一模一樣的陌生人,漸漸開始和她身邊的人接觸,
沒有人發現她並不是海莉本人,大家甚至喜歡她勝過書呆子海莉。
她不僅僅想盜用海莉的臉書,更想徹底占據海莉的人生……
作者簡介:
安娜‧戴維斯
她是編輯,也是位作家。
目前共著有三本小說,擅長驚悚懸疑的主題。
章節試閱
我迅速地咬了一口三明治,並從地板上拿起筆記型電腦,打開電源。在等待電腦開機的同時,不知不覺想到克里希先生對社群網站的不屑。他當然不知道我經常在網路上搜尋我自己,我甚至很清楚Google網站會出現的搜尋結果:一連串漂亮的辯論戰績、榮譽榜和學業成就奬。我在搜尋框裡,打上我的名字。
我瀏覽過第一頁,它和以前一樣,全是辯論紀錄和「鐘奬」的最佳提名人,當然也不會再出現姬莉高一使用過的輕型網誌Tumblr。但這時,第三頁的網頁底部有個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海莉‧凱瑟琳‧威斯汀的臉書。
我按下連結。這可能是和我同名同姓的海莉...
我瀏覽過第一頁,它和以前一樣,全是辯論紀錄和「鐘奬」的最佳提名人,當然也不會再出現姬莉高一使用過的輕型網誌Tumblr。但這時,第三頁的網頁底部有個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海莉‧凱瑟琳‧威斯汀的臉書。
我按下連結。這可能是和我同名同姓的海莉...
»看全部
目錄
第1~23章
商品資料
- 作者: 安娜‧戴維斯 譯者: 李玉蘭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5-04-30 ISBN/ISSN:978957105881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0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