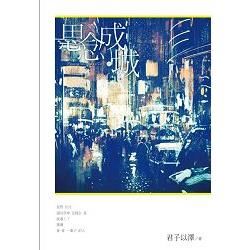※獨家繁體版序!最接近原作者的想法!
我們往往還沒學會怎樣去愛,就遇上了那個會愛一輩子的人。
◆晉江NO.1暢銷作者、《月上重火》、《花容天下》天籟紙鳶轉型代表作!
◆天籟紙鳶出道以來最浪漫優雅的愛情傳奇!
◆你無法想像會有這樣的戀愛,但你一定會想要談一場這樣的戀愛!
他是她念念不忘的城,她是他一言難盡的傷。
影后申雅莉,同時享受著高高在上的優越,和高處不勝寒的憂傷,一個回眸就萬眾矚目,凡人只要抬頭,就能看見她代言的身影。
可現實是,人生路上,再也不會有那樣一個人,對她說我比妳爸媽還要懂妳──十年來的今日,手機都設置提醒告訴她:明天去幫希城掃墓。
但這天,一個容貌酷似顧希城、名叫Dante的建築師突然出現,而她在他身上看見了少女時的夢想。
僅僅因為與相似的人互動就感到開心,什麼時候,她,竟傻到了這個地步?
那個連擁抱都讓她心臟隱隱作痛的人,就好像一條永不癒合的傷──
而他已經不在。
希城,我發誓再也不會愛你。
可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思念成城(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思念成城(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君子以澤
又筆名天籟紙鳶。
現代浪漫小說作家,其文風優雅精致,涉及人文、哲學、西方元素以及現代女性獨立思想。擅長以理性的文筆描寫出感性的故事。代表作《奈何》、《思念成城》、《夏夢狂詩曲》。作品暢銷大陸和臺港澳,遠揚海外,在中國新華書店及各大網路書店多次登上圖書銷量排行榜。在《新蕾》、《魔幻誌》、《第七感》等雜誌發表連載過作品。
《說文》中說:「澤,光潤也。」澤也指水深的湖澤,涵蓋光潤、包容與恩惠的意思。君子以澤,意為君子之間應當相濡以沫。
君子以澤
又筆名天籟紙鳶。
現代浪漫小說作家,其文風優雅精致,涉及人文、哲學、西方元素以及現代女性獨立思想。擅長以理性的文筆描寫出感性的故事。代表作《奈何》、《思念成城》、《夏夢狂詩曲》。作品暢銷大陸和臺港澳,遠揚海外,在中國新華書店及各大網路書店多次登上圖書銷量排行榜。在《新蕾》、《魔幻誌》、《第七感》等雜誌發表連載過作品。
《說文》中說:「澤,光潤也。」澤也指水深的湖澤,涵蓋光潤、包容與恩惠的意思。君子以澤,意為君子之間應當相濡以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