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進堂調合酒 1974
我的名字叫悟,寄宿於京都產寧坂半途中位置稍微深入的一戶民宅,目前正在升學補班上課,原因是我要以京都大學為目標重考。雖然我不曉得是否能考上京大,但這是我還待在鄉下時就無比嚮往的學校,所以我才能努力念書。
再來是我對京都滿懷憧憬,若非此處是京都,我實在無法熬過令人不安的重考生活。踏在石磚坡道上,還能眺望遠處的五重塔景致,時而邊聆聽鐘響邊步下斜坡,稍微在石磚坡道漫步一陣子後,因為市區電車通過而在路面引起震動,這一切的一切我都相當中意。我心想,假如我能永遠住在我座深愛的古都京都就好了。
我還有另一項熱愛京都到無法自拔的理由,那即是位於京大附近的咖啡廳「進進堂」。此處是京大生經常歡聚的地點,我在這間店鋪認識一名京大生,我每次都很期待和他聊天。
這個人每天大致上都在三點過後就會進店裡,因此我也每天超過三點就會造訪這間咖啡廳。儘管我抱持類似去見補習班老師的心態,但是與他相見比跟補習班老師碰頭要更愉快的多,所以我內心總是喜不自禁。
與他聊天的時間簡直棒極了,我們的對話經常從平淡無奇的地方開始,然而我真的會有這種感覺,那就是話題如獲羽翼,轉瞬間好似飛躍海洋般,接著我的心靈猶如大雕翱翔於世界各地。這實在是段不可思議的時光,對我而言這些都是初此品嚐到的經驗。
剛開始我只是很平常地找他諮詢該如何應考京大,以及日常瑣事的煩惱等,只是情況逐漸擺脫這塊範疇,話題開始變得自由奔放起來。我察覺到,我們之間的閒談已經脫離無謂的個人煩惱,比起這些老套的商量,儼然轉變成更饒富意義的對話。
御手洗先生他──這是這個人的名字,他當時正好才結束環遊世界一周的旅途返鄉,只要我希望,不論多少旅遊地點的體驗他都願意與我分享,這些話題總是帶給我無比樂趣,令人沉醉其中。
御手洗先生十分擅於陳述,他能不經意地幫我融入故事中的世界,讓我伴隨故事腳步時喜時優。他的故事總是令異國風景浮現在我眼前,我老是為此忘記時間。
我尚未遠赴過名為國外的地方,然而這個人卻知悉世界各個角落,他踏遍我所不認識的街頭巷尾,或許是我一輩子也未必會造訪的地點,熟識居住在當地的人們,這點首先就令我難以置信。
國外對我而言等同位於遙遠宇宙盡頭的行星,儘管我多少也在照片上目睹過海外風光,但這種情況與火星的沙漠並無二致。所謂國外,究竟是給人怎樣感覺的地方呢。泥土的顏色或海洋的色調會有所不同嗎,空氣的氣味與植物樹葉的色澤是否多少也會不一樣呢,這些景象實際攤開在眼前時,究竟會是怎樣的感覺呢,我總是思索這些問題。
總有一天我也能到海外旅遊嗎──不過,不論我如何思考都不認為有辦法實現。這是因為我在大學入學考上受挫,然而我卻絲毫沒有隔年就能突破難關的自信,我的內心也為此變得誨暗。
御手洗先生對於那些耳熟能詳的觀光勝地沒有半點興趣,他字裡行間登場的地點都是在印度或中國甚至南美諸國間,根本連聽都沒聽過的渺小村莊,或者位處類似大自然正中央的高原聚落。
雖然在這種地方每逢夜晚就缺少比月光更明亮的光源,但是在這裡生活的人們卻不會敗給不安,御手洗先生如數家珍地告訴我這群人的故事。
當我聽到著迷時,我彷彿能嗅到飄蕩在未知清風間的氣味,感受陌生異國居民沐浴在陽光下的髮絲。當我耳聞那些與自己同世代年輕人的生活時,我格外興致昂然,為此我也瞭解那些被我當成外星人般的異國居民,其實同樣會思考,同樣抱持情感過活,同樣身為人類。我自以為早就明白此番道理,其實我根本懵懂無知。
那些我未曾聽聞過的世界角落,生活在那些街頭巷尾人們的喜怒哀樂,以及他們內心深刻抱持的煩惱,這些話題總令我難以自拔。每當回到住處後,我就會獨自抱著膝蓋回憶起今天聽到的故事,然後明白到自己的煩惱究竟有多麼微不足道,心想自己非好好努力不可。
這件事發生在氣候異常嚴寒的日子,由於京都的冬季相當寒冷,當時似乎即將降下細雪般,因此我進入店裡後鬆了一口氣。我的身心皆彷彿蜷縮成一團,所以這天我們的話題沒有往海外發展,我只是一個勁聊起自己的往事。
話題未能獲得羽翼,或許是因為戶外冷峻,還有我因為快感冒而有點頭痛的緣故。
「今天我好像有點感冒……」
我對坐在對面的御手洗先生如是說,接著御手洗先生卻講道,
「啊,是喔,其實我也一樣。」
哦,原來御手洗先生也會感冒嗎,當我如此思忖的同時也對此感到意外。其實御手洗先生他就讀京大的醫學院。
「喉嚨會痛?」
御手洗先生詢問我。
「嗯,會痛。」
我以類似面對醫生的態度般回應他的提問。
「這個維克斯喉嚨噴劑很有效喔。」
御手洗先生如是說,他從口袋掏出一罐小瓶子給我看,然後他不暇思索將之置於桌面。
「這是美國製的噴劑,它是要這樣用,像這樣直接對準喉嚨噴入。」
接著御手洗先生再度執起小瓶子,他在我面前張開嘴巴,實際示範一次給我看。
「你試試看。」
他如是說,於是他把噴劑遞給我,我收下噴劑後,依樣畫葫蘆地張嘴並將朝喉嚨深處噴出噴劑。
「如何?」
御手洗先生說道。
「啊,好刺痛。不過真的很有效,感覺舒服多了。」
「是嗎,太好了。」
儘管御手洗先生這麼說,但是我卻在下個瞬間體會到某種感情,我因此變得無法言語。
這種情況也能形容為受到打擊,我心想「啊」,然後不禁陷入恍惚,我只能保持緘默。我用力嚥下口水,然而這味道──
御手洗先生望向閉口不言的我說道,
「怎麼啦?」
他如此詢問,我卻依舊暫時保持沉默,由於我無法答覆他的疑問而改提別道問題。
「這噴劑日本還沒引進嗎?」
我以爭取時間般的感覺如此詢問。
「沒有引進。」
御手洗先生這麼說的同時搖頭。
待我回過神時,我發覺自己有些淚眼盈眶,我不希望被御手洗先生察覺而稍微垂首,我彷彿在忍受舊傷裂開般的痛楚。
「啊啊,這味道很令人懷念。」
我只講完這句話就抬頭眺望窗外,因為我實在想不出更多的話可講。透過窗戶能窺見京大校園,以及圍牆上方的樹木隨寒風擺盪。
這懷念的景象呼喚我的淚水,接著淚珠融化我傷口上的結痂。當我稍微凝視這景色一陣子後,情緒總算沉靜下來。
「我生長在日本海沿岸的S市。」
當我忽然脫口而出這番話之後,貧窮的漁村風景於焉浮現在我眼前。
成群打撈烏賊的漁船,除此之外一無所有的港灣漁村,父親則在這種村鎮的街道角落經營一間小工廠,我孩提時代老在想究竟要不要繼承父親的工廠,要不然我就只能去當個打撈烏賊漁船上的漁夫。
「不過我不認為,自己能在充斥打撈烏賊漁船的小鎮當個烏賊漁夫。」
「為什麼?」
「就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不過我很喜歡在港口欣賞船隻,所以我經常跑去港口。我認為只要像這樣長時間獨自觀賞船隻,我就能變得喜歡船隻,然後可以下定決心當個漁夫。」
「你希望獲得這種決心吧?」
「因為我父親說這種工廠不必繼承也沒差。」
「是嗎,原來如此。」
「我喜歡天氣即將變壞,海面多少會捲起浪花的日子,成群的漁船全體上下搖晃,簡直像停頓在擺盪電線上的烏鴉。
不過海平面彼端卻是向陽處,耀眼且熠熠生輝。我心想,此時若是能乘風破浪朝那面向陽處發船就好了。」
當我望向御手洗先生,發現他好似強烈肯定般頻頻頷首。
「可是我仍舊無法下定決心當個漁夫。」
「是嗎?」
「那群會找我搭話的漁夫,老是莫名其妙就愛擺架子,還很低俗,他們總是表現出瞧不起我的態度。」
「是嗎。」
「他們一點也不溫和。我無法理解為何他們愛擺出那種態度,也不曉得這樣究竟有什麼意義,所以我無法尊敬他們。不過我之所以常去港口,是因為回家途中有間沿海建造的時髦美式酒館,那間店以木板建造再刷上白色油漆,貼在木板牆壁上的紅色霓虹燈管寫著『Fisherman's』的英文,只有這棟建築物和它背後那片海宛如異邦,簡直帥氣到不行。」
「哦。」
「夕陽西沉時分霓虹燈就會點亮,我因為想看霓虹燈點亮後的模樣,所以就坐在附近的石頭上悶不吭聲地等待日落。畢竟在夕陽照射下的霓虹燈實在漂亮,等天色暗下來後又會變得更像國外。」
「是嗎,原來如此。」
「我很希望欣賞這樣的景致。我沒有去過國外,因此我才認為國外肯定給人這種感覺。」
「所以這對你而言,是初次體驗到的異鄉。」
御手洗先生說道。
「確實如此,店裡不時有爵士樂流洩到外頭,那裡簡直像通往海外的入口……。仔細想想,現在這間進進堂也是如此。」
「你很崇洋呢。」
「我非常渴望能去見識下國外,我真的想去到不行,甚至不惜偷渡都想去。」
「就像高杉晉作或者新島襄那樣。」
「沒錯,而且Fisherman's之所以會給人國外的感覺,還有另一項理由。」
「嗯。」
「每當日落後室內就會點燈,因此就能透過窗戶看清店內的情況。點燈後可以在吧檯看見一位女性,她有沉魚落雁之貌,當我初次拜見她時簡直大感震驚,她實在貌美到宛如女演員般。」
御手洗先生頷首。
「所以我越來越將那間店與它周遭的環境看作國外,不論是明亮的店內或者外圍都很有品味,整潔又光輝動人。」
「國外絕非隨處都很整潔。」
御手洗先生笑道。
「是嗎?」
「是啊,絕大部分都是滿佈塵埃,寒酸且汙穢的環境。」
「沒有乾淨的地方嗎?」
「像電影裡拍的那種地方?當然有,不過整潔的環境同樣伴隨歧視。歧視與自豪,再加上道德心其實都大同小異。」
「咦?歧視與道德心?」
我稍微受到打擊。
「住在整潔環境的女性,無論如何都會輕視外觀不清潔,或者處理垃圾或穢物方面有所怠慢的人。美國民權運動的障礙,說到底也就是這麼回事罷了。但是這些情況多半偏向感性,並非是冷靜觀察下與經過理論思考而得到的結果。」
「這話是什麼意思?我聽不太懂。」
「你有去過豬圈嗎?」
「有去過。」
「會很髒嗎?」
「非常骯髒,還很臭。」
「所以你會不會認為豬很骯髒?」
「會,我覺得牠們跟狗或貓不同。」
「然而兩者實則相同,因為是人才會把豬看成骯髒的動物。因為豬是雜食動物,所以才有很多人把自己吃剩的食物灑進豬圈裡,是人類一意孤行認為就該這麼做,其實這並非豬自己的興趣使然。」
我陷入沉思。
「不論是多愛清潔的人,只要長了張被認為好像不愛整潔的臉,或者長了張被認為類似竊賊的臉,即會成為被蔑視的對象。一旦認知與事實相違,則會成為種族歧視的開端。」
「黑人?」
接著御手洗先生頷首。
「歧視人的那方其實充滿強烈的道德心,這些人泰半是女性,畢竟擔任家庭清潔工作的人多半是妻子。無法遵守倒垃圾規則的人會成為受輕視的對象,這點理所當然吧?」
「當然。」
「不過同樣遵守規則的黑人,不詳加確認就輕視他們,光憑外觀就認定他們不守規矩,這就是種族歧視。人類是種愛自作主張到可怕程度的生物,儘管他們能體諒他人的疏忽,但是他們卻能允許自己動員眾多理由和藉口,來看待自身面對弱者的傲慢。當這些行為經過道德的門面包裝後,情況就會一舉變得不知所謂,這就是這個社會的構造。」
我保持緘默並思考他對我訴說的這番話,但不管我如何思考仍舊不甚明白。
「意思是漁夫擺架子也是出自這個理由?」
於是御手洗先生笑道。
「在日本年輕人就是受歧視的對象,然後一切的優越感正是他們生存的動力。你後來認識那名女性了嗎?」
「我長時間都只待在外面看她,畢竟高中生無法單槍匹馬靠近餐飲店。不過Fisherman's離學校有段距離,又靠我家很近,菜單上還有咖哩與繪飯,所以我心想總有一天要光顧這間店,可是我卻老拿不出勇氣。」
「哦,然後呢?」
「某天我到港口時突然下雨,我跑到那間店的屋簷下避雨,然後就聽到有道聲音問我說:你沒帶傘嗎?要稍微進店裡坐坐嗎?」
「她對你這麼說?」
「是的。我定睛一瞧,發覺店門敞開,那位女性就站在我隔壁。」
「哦。」
「她對我說:目前還沒半個客人,你就稍微進來躲下雨吧。」
「是嗎,她真親切。」
「她實在很溫柔,而且打從我出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見有人對我如此親切。當我迫近眉睫地注視過她後,我發覺她簡直漂亮到像幅畫,比待在外頭時看起來更漂亮。那位女性身上擦的香水跟雨水氣味融為一體,散發出逼人香氣,當時我簡直猶如身處夢境,就好像電影裡的一幕場景。」
「然後呢,你進去了嗎?」
「是的。於是我被木匠兄妹的歌曲包圍,店內裝潢也很帥氣,因為沒有半位客人在,所以我就和那個人一起坐在餐桌前閒聊一陣子。她是個大好人,也很常笑,直到雨停為止她一直陪我聊很多話題。」
「嗯。」
「後來變成傾盆大雨,連店內都能聽見雨聲。偶爾不大聲說話,甚至會聽不見對方的聲音,總覺得我好像和她共享一段秘密時光,當時我真的很高興。」
「你們聊了些什麼?」
「聊學校的事,還有家裡跟我自己的事。」
「是因為她有問你吧?」
「沒錯。那個人的名字叫美紗小姐,後來我肚子餓了,她還請我吃咖哩。」
「好吃嗎?」
「好吃,不過味道算普通吧。她說咖哩是請製造商直接送過來的,店裡只是靠這種方式補充許多餐點而已。」
「這部份她很坦白告訴你呢。」
「嗯,她任何事都會仔細告訴我,所以後來我就變得很常光顧Fisherman's。」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御手洗潔與進進堂咖啡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文學 |
$ 253 |
日本驚悚/恐怖小說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御手洗潔與進進堂咖啡
★全系列暢銷突破330萬冊!名偵探御手洗潔的年輕時代!
★遊歷過世界各地的御手洗所描繪出的日本、英國、中國是什麼樣子的呢?
生活在這些地方的人過著怎樣的日子,遇到了哪些謎團呢?
在這間小小的咖啡館裡,青年開始環遊世界──
★推理之神 島田莊司 不能錯過的一部傑作
★尖端推理無國界11月強力主打:林斯諺《冰刃方程式──偵探林若平的解法》與島田莊司《御手洗潔與進進堂咖啡》。
【故事簡介】
──御手洗潔的年輕時代,
於京都咖啡廳「進進堂」所敘述的故事。
進進堂,是一間矗立於京都大學後方的老字號咖啡廳,此處為環遊世界旅行歸來的御手洗潔每天光顧的店鋪。正在補習班準備重考的學生悟,為了聽他講旅途中的故事而頻繁涉足此店──連結西域與京都的夢幻櫻花、於戰禍天空消逝的殺意、埋藏在欽札諾威士忌汽水的記憶……這是京大生時代的御手洗潔,在他成為名偵探前夕所描述的四篇充滿悲哀與鄉愁的故事。
作者簡介:
島田莊司
一九四八年出生於廣島縣,武藏野美術大學畢業。一九八一年以首部長篇作品《占星術殺人事件》出道,憑藉《斜屋犯罪》、《異邦騎士》等「御手洗潔」系列;《寢台特急1/60秒障礙》等「吉敷竹史」系列為中心,孕育出眾多高人氣作品,建立自身本格推理旗手無可撼動的地位。
著作曾多次獲獎及進入暢銷排行榜,包含《寫樂:閉鎖之國的幻影》、《21世紀本格宣言》、《星籠之海》等。目前擔任「島田莊司選 薔薇的城市福山推理文學新人獎」與「本格推理老兵新人賞」評選主審,同時在台灣也舉辦「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致力於發掘新人。
TOP
章節試閱
進進堂調合酒 1974
我的名字叫悟,寄宿於京都產寧坂半途中位置稍微深入的一戶民宅,目前正在升學補班上課,原因是我要以京都大學為目標重考。雖然我不曉得是否能考上京大,但這是我還待在鄉下時就無比嚮往的學校,所以我才能努力念書。
再來是我對京都滿懷憧憬,若非此處是京都,我實在無法熬過令人不安的重考生活。踏在石磚坡道上,還能眺望遠處的五重塔景致,時而邊聆聽鐘響邊步下斜坡,稍微在石磚坡道漫步一陣子後,因為市區電車通過而在路面引起震動,這一切的一切我都相當中意。我心想,假如我能永遠住在我座深愛的古都京都就好了。...
我的名字叫悟,寄宿於京都產寧坂半途中位置稍微深入的一戶民宅,目前正在升學補班上課,原因是我要以京都大學為目標重考。雖然我不曉得是否能考上京大,但這是我還待在鄉下時就無比嚮往的學校,所以我才能努力念書。
再來是我對京都滿懷憧憬,若非此處是京都,我實在無法熬過令人不安的重考生活。踏在石磚坡道上,還能眺望遠處的五重塔景致,時而邊聆聽鐘響邊步下斜坡,稍微在石磚坡道漫步一陣子後,因為市區電車通過而在路面引起震動,這一切的一切我都相當中意。我心想,假如我能永遠住在我座深愛的古都京都就好了。...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島田莊司 譯者: 北太平洋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6-11-08 ISBN/ISSN:978957106900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6頁 開數:菊16開(25K)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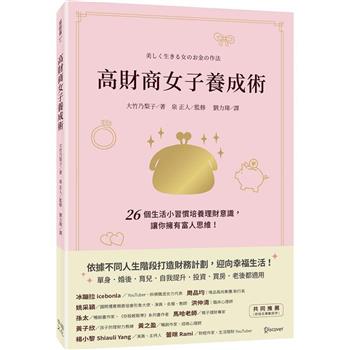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