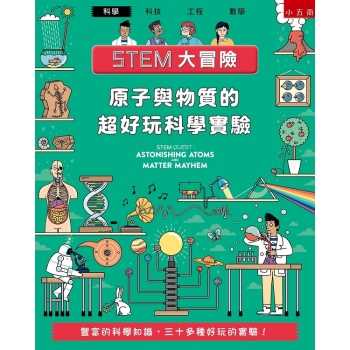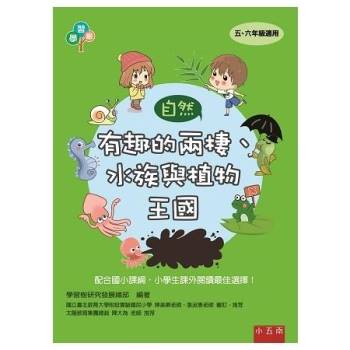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開始吧!」女人的聲音低沉地迴響著。午後的室內,放下的百葉窗帶來了神祕的陰影。女人身穿海軍藍色套裝,放下蹺起的腳,輕輕探出身子。沙發發出了微小的咿軋聲。
「……請報告調查內容。」
「是。──姓名,澀谷一也,靈異現象調查事務所『Shibuya Psychic Research』的所長。經過本調查員費盡千辛萬苦得到的情報顯示,生日是九月十九日,年滿十七歲。」
「什麼費盡千辛萬苦的就不用說了,調查員只須報告事實即可。──十七歲,這麼說來,他還是高中生囉?」
「他似乎沒上學。」
「這樣啊!」女人喃喃說道,再度蹺起了腳,倚著沙發椅背,仰望天花板,略微思索。
「──處女座啊?而且是性格惡劣的那種處女座。」
她斷然說道,語氣十分篤定。
「是啊!就我觀察,血型應該是A型或O型。」
「有可能。」
女人大大地點了頭,此時,一直默默聆聽談話的男人突然插嘴說道:
「這些事不重要吧?」
女人瞪了男人一眼。
「觀察員別發言。──調查員,請繼續說下去。」
「是。他的住址不明,住家電話號碼也不明。」
「徹頭徹尾的祕密主義。家庭成員呢?」
「同樣不明。雙親健在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確定的。父親據說是大學教授;是哪所大學不明,但經過確認,已知是超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者。」
「出身地呢?」
「不知道。不過,他對於東京的地理不甚了解;雖然知道地名及地點,卻不熟悉土地,尤其是觀光名勝、古蹟及名店,幾乎一無所知。從這些例子判斷,他應該不是在東京土生土長的;但要說是出身於地方,說話又沒有腔調。就我推測,他或許是出身於東京近郊。」
「又或者是出身於腔調不明顯的地方……。很難想像。」
「他的形象很難跟鄉下連結。」
「把地方和鄉下畫上等號,未免太直觀了吧?」
插嘴的是旁觀的男人,這回女人瞪了他一眼,讓他閉上嘴巴。
「然後呢?事務所的經營狀況如何?」
「不清楚……不過稱不上好。別的不說,經營這兩個字究竟適不適用,也令人存疑;至少看起來不像在追求利潤,甚至有敬委託人而遠之的傾向。有委託上門,通常是拒絕居多;就算一時興起接了委託,收取的調查費用大多只有工本費,沒有利潤可言。」
「不過員工倒很多,除了助手以外,還有兩名工讀生。他的資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不清楚。……或許是另有財源吧!」
一臉無聊地聆聽對話的男人輕聲笑了。女人又瞪了男人一眼。
「觀察員請保持肅靜,不然就要請你離席了。──這麼說來,工作量並不多囉?那他每天在辦公室裡做什麼?」
「詳情不明,因為他總是關在所長室裡不出來。就目擊情報顯示,不是在讀書、寫字,就是看著地圖沉思。有時也會像現在一樣出外旅行。」
「哦,他現在正在旅行啊?去哪裡?是為了調查嗎?」
「好像與調查無關,應該純粹是私事,所以我不知道詳細的目的地與行程,只約略知道是東北地方的某處,今天差不多該回來了。」
「目的呢?觀光旅行或溫泉旅行……應該不是吧?」
「我想應該不是。」
「那他到底是去做什麼?」
「不清楚。」
女人沉下臉來,隨即又裝模作樣地清了清喉嚨。
「算了。那助手呢?查出本名了嗎?」
「林興徐似乎是他的本名沒錯。出身香港,其他個人檔案不明。年齡、經歷、家庭成員、住址及電話號碼一切不明,但是據說和澀谷一也住得很近,只要敲敲牆壁就聽得到。」
女人沉默下來,不久後發出了高八度的聲音。
「搞什麼!?結果妳什麼都不知道嘛!」
「這個嘛……」
「真沒用。」
「沒辦法啊!又不是我的錯!全都是……」
我忍不住真的放聲怒吼。
「全都是諾爾搞祕密主義的錯!」
東京,澀谷,道玄坂。Shibuya Psychic Research。
在漂亮的辦公室正中央,我,谷山麻衣雙腳大開,肩膀上下抖動,承受著女人(松崎綾子,巫女)及男人(瀧川法生,原高野山和尚)的冰冷視線。虧我還是個閉月羞花的十七歲少女耶!真是的。
沒錯,全都是諾爾不好。Shibuya Psychic Research所長澀谷一也,容貌出眾,但是性格惡劣至極,旁若無人、傲岸不遜、唯我獨尊、專斷獨行。正因為他的個性無限自戀,所以才被稱為「諾爾」。
幹嘛什麼事都保密啊,臭小子!!
遠遠旁觀的小高(高橋優子,職場同事)拍了拍我氣得發抖的背部。
「乖、乖,先冷靜下來吧!把腳併攏,中指也放下來,聽話。所長搞祕密主義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對吧?來,克制點、克制點。」
「可是……」
啊,光是回想起來就滿肚子氣。
事情的開端──是起自於今年春天出現的某個女人。這個名叫森圓香的女人是諾爾和林的舊識;既然是舊識,就代表她知道所有我們不知道的事,對吧?我有堆積如山的問題想問她,但她幾乎什麼也沒說就離去了。
這件事點燃了我的好奇心。在森小姐出現之前,每個人對諾爾都是一無所知;如今出現了無所不知的人,我卻什麼也沒打聽到就放她回去了,這種懊悔當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啊!
──如此這般,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我開始積極地收集情報。在收集情報的過程中,我得知綾子也打著同樣的算盤,便從梅雨季節開始攜手合作,但是直到夏天依然一無所獲。每次提問都被拒答,跟蹤都被發現,還附帶冷嘲熱諷,最後甚至加上了這句話──「妳對我有意思啊?」
那~小~子~!
欸,什麼跟什麼嘛!我、我只是因為諾爾事事都神祕兮兮的,不知道隱藏了什麼祕密,才萌生了純粹的求知欲,並不是基於戀愛感情或特殊感情衍生的興趣而調查的。「對我有意思」?別開玩笑了,自戀也該有個限度啊!混帳。
……不,老實說,我還真的對他有點意思(臉紅),不過事到如今,就算只是為了賭一口氣也不能承認。
「不過,我覺得麻衣也有錯。」
小高說道,我回望她的臉龐。
「為什麼?」
「妳覺得所長會輕易透露他在隱瞞的事嗎?」
……唔。
「妳卻硬要去挖人家的隱私,在對方看來,根本是跟蹤狂的行徑嘛!」
「咦~~~?」
「總之不會是讓人感到舒服的事。就算換作一般人,也會抱怨幾句吧?更何況是所長,就算被埋怨嘲諷上一百句也是正常的。」
「話是這麼說啦……」
我垂頭喪氣。
小高又拍了拍我的背。
「哎,我也不是不明白妳和松崎小姐的心情啦!可是,不適可而止,以後說不定會後悔喔!」
「後悔?」
我反問,小高望著千秋學姊。學姊(笠井千秋,處於低潮期的超能力少女)輕輕地聳了聳肩。
「刻意隱瞞,就代表不想被人知道吧?」
「……嗯。」
「可是妳卻偏要查探,搞不好會把他逼回深山裡去。」
「妳在說什麼?」
「白鶴報恩的故事啊!既然被看到原形,就不能繼續待在這裡了──。妳不覺得這種情形很可能發生嗎?」
「不會吧……」
「可是,妳也不敢保證吧?比方說,所長其實是有錢人家的少爺,因為父母反對,只能偷偷摸摸地開事務所;結果查出他家的妳冒冒失失地登門拜訪,導致事情全被父母發現,他只好把事務所收了──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
「森小姐說他的父母沒反對啊!」
千秋學姊嘆了口氣。
「我只是打個比方。就算所長離開了,妳也無所謂嗎?」
「哼!正合我意。」
我說道,學姊伸出手指指著我。
「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妳再也找不到這麼高薪的打工了。」
……唔。
「這樣很傷腦筋吧?」
「……傷腦筋。」
我不情不願地承認。畢竟我是個窮學生,少了這份超乎常理的打工薪水,對荷包的傷害實在太大了。
興致勃勃地聆聽我們說話的和尚插嘴問道:
「這裡的打工薪水很高啊?」
小高大大地點了頭。
「嗯,就連我的薪水都比一般打工好,更何況麻衣好歹是個調查員,薪水更高,平均算下來,大概和低薪的粉領族差不多。」
嗯,進行調查的時候二十四小時都支薪,而且還有特別津貼。
「哦?」和尚歪頭納悶。
「怎麼了?」
「沒什麼。──之前我問過諾爾老弟為什麼雇用麻衣,他說因為便宜又耐操。」
小高也歪頭納悶。
「可是不便宜耶!」
「嗯,可以自由增加打工時間,薪水是時薪制的,缺錢的時候多排點班就好了。」
就拿現在來說,沒有調查的時候我都盡可能地留在事務所裡增加收入。
綾子發出不滿之聲。
「什麼跟什麼?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打工啊?在說這些蠢話的時候,妳們也有薪水可領?」
「因為現在就算想工作也沒事做啊!」
說著,我看了小高一眼,小高也點了點頭。
「是沒事做。」
和尚更加納悶了。
「妳們的工作看起來沒有辛苦到必須給這麼好的待遇啊!」
「去調查的時候就很辛苦了。」
畢竟是搏命調查。
「平時呢?」
和尚詢問,我和小高面面相覷。小高指著我說道:
「麻衣負責守在辦公室裡,接待上門的委託人。」
我也指著小高說道:
「小高負責的是事務工作,整理買來的書、打雜和泡茶。」
「現在呢?」
「林正在午休,所以麻衣得看家。現在沒有委託人,就算想接待也沒得接待。」
「小高剛才在打掃辦公室,已經掃完了。今天沒有新買的書,林和諾爾都不在,也沒交代雜事。」
「對對對,所以目前的工作只有泡茶……」
「招待來玩的靈能者工作夥伴,完畢。」
我和小高一搭一唱地報告,和尚沉下臉來,拄著臉頰說道:
「剛才我好像聽見電話響了幾次耶!」
「可是,有電話答錄啊!」
「既然看家是工作,怎麼不順便接接電話?」
「因為……」
「就是……」
我和小高互相點頭。
「我們不可以接電話,所長交代的。」
「對對對,也不可以碰郵件。樓下的信箱有上鎖,只有所長和林有鑰匙。」
「順道一提,我們也不打掃所長室,因為不能擅自進去。」
「再順道一提,也不可以碰錢。」
和尚與綾子不約而同地抱起頭來。
「諾爾老弟的金錢觀是怎麼回事啊?」
「就是說啊!要是我,才不會給這種工讀生那麼多薪水呢!」
「幹嘛這樣講啊!」
「當然啊!簡單地說,妳們現在就是坐在冷氣房裡喝著辦公室供應的茶打混。」
是可以這麼說啦!
小高鼓起腮幫子。
「可是所長說沒關係啊!」
「對,他有說過。」
「工作雖然輕鬆,可是人際關係很辛苦耶!」
「對啊,上一任工讀生一定也是因為這樣才不幹的。」
聽我這麼說,小高和千秋學姊都錯愕地看著我。
「上一任工讀生?」
「嗯,諾爾問我要不要打工的時候,說過前陣子有人辭職。」
「可是,森小姐不是說他們雇用員工讓她很意外嗎?」
經小高這麼一說,記憶突然甦醒了。……咦?這麼一提,她好像說過這句話。
綾子用冷冷的眼神看著我。
「『上一任工讀生』真的存在嗎?一般人才不會辭掉這麼好賺的打工呢!就算所長和助手再怎麼難搞,他們平時都關在所長室和資料室裡幾乎不出來,不是嗎?」
「這個嘛……說得也是。」
和尚盤起手臂來。
「這種用錢法實在超乎常理。上門的委託人不多,而且幾乎都拒絕了,怎麼還能在這種黃金地段開這麼豪華的事務所?而且又養了兩個幾乎沒在做事的工讀生,薪水還很高。」
「可是諾爾卻覺得便宜又耐操,這麼看來,他家果然是家財萬貫,所以金錢觀和我們是兩個世界。一定是這樣。」
「大學教授的收入是不錯,不過還不到『家財萬貫』的地步。」
「再不然就是本來就很有錢。諾爾的性格那麼傲慢,一定是因為他是大少爺。」
「真正的有錢人是很溫文有禮的。」
「這一點應該因人而異吧……」
說到這兒,門開了,林回來了。以沉默寡言、面無表情為註冊商標的他長得非常高,通過門的時候得稍微低下頭來。
林環顧辦公室,輕輕向和尚與綾子點頭示意。
「打擾啦!」
說著,綾子揮了揮手,又緩緩地探出身子。
「哎,林,在麻衣之前,有雇過別的工讀生嗎?」
「沒有。」
林斷然說道,從懷中的郵件裡抽出兩個看似裝了雜誌的信封遞給小高。抄錄雜誌目錄整理成小卡是小高的工作。
──話說回來,沒有?
「沒有?」
「對。」
林面無表情地說道,走向資料室。路上,他向千秋學姊使了個眼色。學姊接下來要和林一起進行念力訓練。長期的訓練沒有白費,最近折彎湯匙的能力出現了恢復的前兆。同時,千秋學姊也變得比較好相處了──這是小高的看法。從前學姊有點疑神疑鬼,總是強烈排斥陌生人,而這種傾向在這陣子略有改善。事實上,我也覺得她少了幾分固執。從前她一直執著於折彎湯匙之上,彷彿對其他事物毫無興趣;但是自從出現恢復徵兆之後,學姊反而不再熱衷於折彎湯匙,而是開始對音樂、書籍、戲劇──以及旁人產生了興趣。我想,這應該是好事吧!
就在我如此暗想,目送千秋學姊走進資料室時,和尚喃喃說道:
「……諾爾老弟到底在想什麼啊?」
小高沒什麼把握地回答:
「會不會是那個?刀子口,豆腐心……」
「不、不會吧……」我皺起眉頭來。
「妳想想,根本沒有上一任工讀生,卻特地撒謊雇用妳耶!說不定所長早就知道妳生活上有困難了。」
怎麼可……有可能。當時諾爾是來我們學校進行調查的,或許曾聽說過我的家庭狀況。──對了,建議千秋學姊進行訓練的也是諾爾。當時我覺得何必多此一舉,不過諾爾卻說「有些事物是在自然訣別之前不能失去的」。看到千秋學姊近來的變化,我才理解他的用意。就這點看來,或許他是同情我這個窮苦學生,才故意演那齣戲。
「無論如何……」綾子發出了不悅的聲音:
「麻衣,這樣看來,其實人家對妳很好耶!」
冰冷的視線朝我投射而來。
「不會吧……」
……不會吧?
唔……。事態越來越撲朔迷離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Ghost Hunt 惡靈系列(6):來自大海之物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0 |
日本驚悚/恐怖小說 |
$ 221 |
驚悚/懸疑小說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驚悚/懸疑小說 |
$ 252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Ghost Hunt 惡靈系列(6):來自大海之物
《十二國記》作者小野不由美,傳說之作復活!
吉見家在能夠一覽日本海的能登島上,經營餐廳。
據說每當家族經營傳承時,就一定會出現多數人們死去。
當委託人․吉見彰文的祖父去世時,年幼的姪子․葉月背上出現了不詳的戒名。
在追查讓此家族遭受詛咒的真正原因時,諾爾不知被何物附身。
最大的危機襲向群龍無首的SPR。
《Ghost Hunt惡靈系列》第六集,來自深淵陰晦的恐懼!
作者簡介:
小野不由美
12月24日生於大分縣中津市。就讀京都大學時參加推理小說研究社,學習小說寫作。1988年在講談社X文庫Teen's Heart書系出道。89年「Ghost Hunt」(惡靈系列)第一集《惡靈這麼多!?》大受好評,榮升當紅系列作。繼91年的《魔性之子》之後,又在92年發表《月之影 影之海》,自此展開「十二國記」系列。94年發表《東亰異聞》。98年《屍鬼》大獲暢銷,隨後改編成漫畫和動畫。2001年發行《黑祠之島》。02年4月,NHK電視台播映「十二國記」動畫。03年發表《倉房之神》。目前在怪談專題雜誌《幽》連載「鬼談草紙」。
本作最早發表於《惡靈這麼多!?》(1989年講談社X文庫Teen's Heart書系),經過大幅改寫重新出版。
相關著作
《Ghost Hunt 惡靈系列(05)鮮血迷宮》
《十二國記(11)黃昏之岸 曉之天》
《十二國記(10)華胥之幽夢》
《十二國記(09)-圖南之翼》
《Ghost Hunt惡靈系列(4)死靈遊戲》
《十二國記(08)丕緒之鳥》
TOP
章節試閱
「開始吧!」女人的聲音低沉地迴響著。午後的室內,放下的百葉窗帶來了神祕的陰影。女人身穿海軍藍色套裝,放下蹺起的腳,輕輕探出身子。沙發發出了微小的咿軋聲。
「……請報告調查內容。」
「是。──姓名,澀谷一也,靈異現象調查事務所『Shibuya Psychic Research』的所長。經過本調查員費盡千辛萬苦得到的情報顯示,生日是九月十九日,年滿十七歲。」
「什麼費盡千辛萬苦的就不用說了,調查員只須報告事實即可。──十七歲,這麼說來,他還是高中生囉?」
「他似乎沒上學。」
「這樣啊!」女人喃喃說道,再度蹺起了腳,倚著沙發椅背,...
「……請報告調查內容。」
「是。──姓名,澀谷一也,靈異現象調查事務所『Shibuya Psychic Research』的所長。經過本調查員費盡千辛萬苦得到的情報顯示,生日是九月十九日,年滿十七歲。」
「什麼費盡千辛萬苦的就不用說了,調查員只須報告事實即可。──十七歲,這麼說來,他還是高中生囉?」
「他似乎沒上學。」
「這樣啊!」女人喃喃說道,再度蹺起了腳,倚著沙發椅背,...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小野不由美 譯者: 王靜怡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7-06-16 ISBN/ISSN:978957107474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76頁 開數:14.50*21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