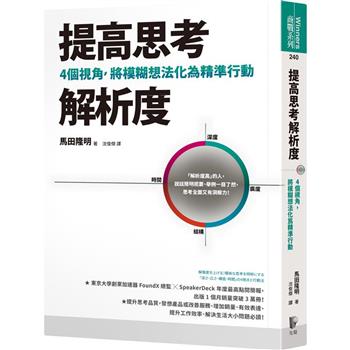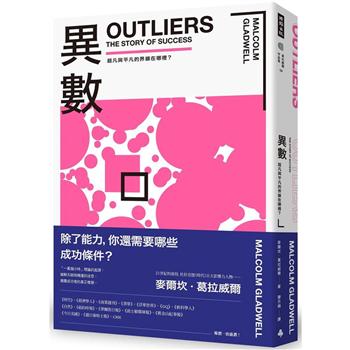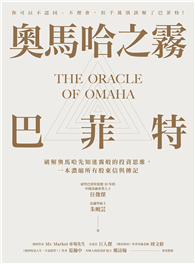★「每一章讀完後的感想,都是鮮明且美麗的,這本書好看到讓人無法抗拒。我想,這本書應該可以稱作是AV業界的《火花》吧。」──絕讚!日本媒體、讀者前所未見好評推薦!
★日本當紅女優紗倉真菜,將自身經驗與觀察化為文字,緩緩道出AV女優周遭不為人知的世界。
★已改編電影!2017年10月《最低。》入圍第30屆東京國際電影節競選作品!
由《64:史上最凶惡綁架撕票事件》提名日本奧斯卡最佳導演 瀨瀨敬久 執導。
★SOD大獎六項冠軍得主,Skypa!成人放送大賞史上首位三冠王 紗倉真菜 首次挑戰小說創作!
在這裡跌倒的話,就再也回不去了……
瞞著家人偷偷休學當AV女優,
被發現後遭到全盤否定的少女「彩乃」。
被AV製作公司誘騙到東京,
跟社長談起戀愛的浪蕩女「桃子」。
五年來不曾有過性生活,為了滿足欲求,
主動參與AV演出的家庭主婦「美穗」。
因為母親曾當過AV女優,
遭到同學冷眼以對的少女「彩子」。
以不同姿態尋找幸福的四位女性,
儘管不安、迷茫,仍堅持挺直身軀前進的故事。
讀者心得推薦
「內容充滿了溫柔且具有溫度的文字。主題環繞著AV女優,但卻是一本看了之後會讓心整個溫暖起來的小說,讓讀者對於故事中的女主角們能夠感同身受。」
「如果說小說家是『觀察的專家』,那麼將自己的性事公開讓人欣賞的AV女優,就可以說是被觀察得最徹底的一種工作。在這樣的業界持續居於領先地位的紗倉真菜,應該可以說是『被觀察的專家』……閱讀她的處女作《最低。》時,最讓我大感驚訝的,就是以這種被觀察的角度來撰寫小說的表現手法。」
「在這本小說裡,將各式各樣的元素全都聚集在一起,包含AV女優出道之後的各種衝突、家庭關係、人際關係,以及周邊的環境等等。如果作者之後再推出新作品的話,我會想要買來看看。」
「起初我以為這了不起就是AV女優所寫的情色故事罷了,只能說有這種想法的我真是太膚淺了。這是一本情節巧妙、故事動人的優質小說!」
「對於人生的酸甜苦辣各有不同體驗的大人們,也應該要來看看這本小說。我甚至覺得這部作品與芥川賞獲獎的文學作品一樣,具有細細品味的價值。」
「無法停留在同一個地方的主角們,像沒有根的雜草般展現出漂流不定、變化莫測的生命姿態。能依靠什麼呢?能仰賴什麼呢?或許她們都曾用自己的雙腳試著站穩身軀,並積極奮鬥努力讓自己留在原處,可惜結果仍舊得要四處漂流──不過,作者對此並未抱持著否定或肯定的態度。想要放棄的念頭,以及悲傷的情緒,全都淡淡地滲入,硬生生壓迫地著讀者。不管怎麼說,這樣的角度都讓本書的質感一口氣向上提升了不少。」
「我完全沒有看過紗倉真菜的A片作品,所以說起來並不是她的粉絲。這部作品描繪出生存在AV世界裡的人們各自的虛無、寂寥,以及悲哀,看似漫不經心的文字,卻能將一切表現得如此恰到好處,真是一本傑出的作品。」
「文章內容相當淺顯易讀,表現手法也相當柔和,因此會讓人刷刷刷地一直翻閱下去。書裡的故事真的很精彩,非常觸動人心,但在陷入紗倉真菜的文字世界裡時,偶爾會在腦海裡閃現可愛的『紗倉真菜的世界』,這種落差或許就是這本書最大的魅力所在。」
「書名上所標示出的『句點』,並非單純只是為了讓書名更加顯眼,我認為那或許是紗倉真菜希望自己所想的那些『最低。』的事情,總有一天能夠畫上句點、宣告終結,那個句點就代表著自己的決定以及期望。」
「看第二次的時候,對於登場人物以及故事結構會比第一次看時更加清楚,不僅讀起來更輕鬆、更容易投入感情,而且感覺也會有所改變,這一切都讓閱讀的樂趣增加不少,所以非常建議大家在看這部作品時,最少要看個兩次以上。」
「真沒想到,這部作品能夠好看到這種程度,我想,這真的是老天爺給紗倉真菜的第二個大禮。對於AV女優這份職業抱有偏見的人,一定要來看看這本書。希望你們都會臣服在紗倉真菜的才華之下。這是一本無可比擬的傑作!」
「若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我的感想,那就是『好有深度的一本書啊』!以平淡的語調描繪出四位AV女優的故事,每一位所遭遇的情況及身處的環境都各不相同,然而作者卻能鉅細靡遺地一一描寫出來,真教人感到驚訝。並且,雖然乍看之下是屬於悲傷的故事,可是四位AV女優卻都在最後為自己的人生踏出新的一步,也因此讓人在閱讀時更能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一本我會很想看好幾遍的小說。」
「每一章讀完後的感想,都是鮮明且美麗的,這本書好看到讓人無法抗拒。我想,這本書應該可以稱作是AV業界的《火花》吧。」
「同樣身為女性,對於書裡的某些部份我是頗有同感的。對於家庭或自己一直以來所屬的社會環境,不知為何總是無法習慣,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就這樣開始四處闖蕩,心裡滿是徬徨。對她來說,成為AV女優並不是最終目的,然而這份工作卻為她引來家人的斥責怒罵。於是,她又再次陷入迷惘,明明好不容易已經走到一半了呢。她所承受的痛苦,以及被丟棄在一旁的寂寞,我都能切實感受得到。無論是誰,尤其是對女性來說,應該都可以從小說中登場的人物裡頭,找到與自己相似的影子吧。」
「這本書讓人聯想到又吉直樹的《火花》,但相較之下,紗倉真菜的作品則更呈現了社會的結構問題,透過主角們傳達對於自尊及身分認同的種種想法……」


 2018/06/03
201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