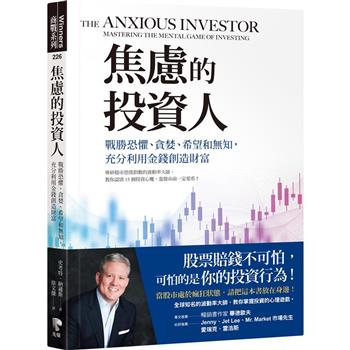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怎麼跑到外面來了?」
他的問題沒有帶主語,寫意拿不準是問她還是問那隻惡貓,所以半天不知該不該答,直到厲擇良揚起聲調朝她「嗯」了一下。
「我待得悶,就出來看看。」
「那回屋去吧。」他一邊說,一邊放下小貓騰出手解襯衣的袖口,走回屋子。那隻貓也跟在厲擇良身後,追進了屋。
寫意在後面看他的腳,義肢又裝上去了,不知是真的這麼快就恢復了還是他在強忍。不過,若是他真站著不動,幾乎看不出來那義肢和另一條腿有什麼不同。
厲擇良進門時回頭看了她一眼,寫意立刻埋下頭去。這樣在背後看人家,實在算不上什麼有禮貌。
「客房收拾好沒?」厲擇良問。
「收拾好了,樓上那間。」老譚說。
「嗯,沈小姐要多住幾天,看看還缺什麼,明天幫她拿下行李。」
寫意聽見這句,咬住脣,沒有反駁。
厲擇良在沙發上坐下後,示意寫意坐,那貓也盤起身子在厲擇良的腳邊睡下。
老譚上了茶,識趣地退出去,客廳裡只剩他們倆。茶壺裡沏的是鐵觀音,一陣茶香從壺嘴裡逸出。
厲擇良替她倒了一杯。
寫意原本是想說「我晚上不喝茶」的,可又覺得顯得自己有些矯情,便謝過就喝了一口。她不愛喝茶,對其沒有研究所以也品不出味道。
厲擇良喝過茶,用手指關節拂了下眉角,那個樣子似乎是累極了。
他習慣性地掏火點菸,可是想到什麼,又作罷,將菸盒放在茶几上。
「難道妳也是怕我反悔?」他說,「我一直是個說一不二的人,既然答應了妳就絕對做得到。」顯然,他指的是她主動送上門這件事。
刹那之間,寫意頓覺尷尬,臉上的緋紅一下子竄到耳根。她本來是已經說服了自己,但是讓厲擇良這麼突然說出口,仍舊覺得心氣難平。
她握住拳頭,憑她以往的個性幾乎快要扭頭就走,不但扭頭就走,還要冷嘲熱諷地回敬他兩句,讓他討不上半點便宜不說,氣個半死是最好。
可是,現下的寫意腳跟定在原地,臉色是紅了又白,終究是忍住了:她本是下定了決心要好好和他相處的。
「看來厲先生是以羞辱我為樂。」寫意淡淡道,這麼一句服軟的話被她說出來仍舊能扎人。
厲擇良倒也沒生氣。
「這倒不是,我只是對沈小姐態度的巨大轉變有些……」他頓了頓,在腦中找了找恰當的詞語,「有些欣喜。」
可惜,這種詞說出來嘲諷的味道更加濃厚。
寫意瞥了眼眼前男人那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心想,還不如他生氣時順眼。
「好了,時間不早妳去休息吧,上樓第二間是妳的房間。」說著他自己也準備回房間。
寫意呼吸一滯,他的意思是說今天就此為止。
突然,厲擇良又折回,「手給我看。」
寫意一怔,她以為他並沒有發現。
「沒事。」
「我看看。」
寫意被迫將那隻手伸出來。他將她的手攤在掌中,細細端詳,幸好傷口不深,稍微破了點皮,他去取了藥箱居然要為她上藥。
寫意有些意外。
他準備抹碘酒的時候說:「疼就吱聲。」
「不疼的。」
「貓這種動物性情陰晴不定的,不該亂碰。」
「人還不是一樣。」寫意說。
「說誰呢?」
「沒說你。」
「那說誰?」
「說我自己。」
這總成吧。
「嗯,」他點點頭,「深有同感。」
被他倒打一耙。
「難得我倆第一次達成共識。」他說。
這時,小貓很恰當地在此刻爬起來,躬起背叫了一聲,也不知是不是在迎合牠那個英俊主人的觀點。
寫意看了那貓一眼,說:「是啊,你倆居然都能達成共識,不容易。」
「……」
「……」
一會兒,厲擇良小心翼翼地替她擦碘酒,抹完以後居然孩子氣地朝傷口吹了
吹氣。
「明天一定要抽空去打疫苗。」
「嗯。」寫意點頭,隨後準備將手縮回去。但是,他沒有放手,手指微微使勁將她的手鎖在掌中。被他壓到傷口,寫意瞇了瞇眼,有些疼。
「我還以為妳挺能忍的呢,剛才背著手藏了半天也不叫疼。」厲擇良說話時,眼中有戲謔的成分。他好像一改最近的暴戾,恢復了他從前待她的那種個性。
「再能忍我也不是木頭人,我是有感覺的。」她吃痛地蹙起眉。
「我看也差不多。」
「呃?」寫意沒聽清他說的話,因為她突然嗅到了一陣奇怪的芬芳。
她掉頭一看,好像是小貓出去時將門蹭開一個縫隙,才使得香氣竄進來的。
「什麼味道?」她不禁問。
「夜來香。」
「夜來香?」她一直對這類植物比較好奇。小時候家裡給她買過含羞草,她一直想不通為什麼它要害羞。於是摸一下,含羞草合上葉子,過一會等它舒展開又摸一下。她樂極了,可惜不到兩天就將那株含羞草折磨死,活脫脫一個破壞大王。
那又是為什麼夜來香要夜裡才開呢?
「我能看看嗎?」她剛才在花園居然沒有聞到。
「有什麼可看的,不就幾朵花,聞久了會頭暈。」他十分沒有情趣地說。
既然主人家都這麼說,寫意只好訕訕地回客房。客房的浴室裡,居然還準備了換洗的衣服和睡衣。
她打量了下,睡衣是新的,但那套女裝是舊衣服,不過洗得很乾淨。一條鵝黃色的連衣裙,尺碼和她身段差不多,寫意揣測大概是厲家那位小姐的東西。有得換,總比明天還穿這一身好。
她洗了澡,呈「大」字形撲到床上。謝天謝地的是,厲擇良讓她住到這裡。若是回到上次那間公寓還不知如何和他相處,那裡僅有一間臥室,那究竟是她睡還是他睡,還是一起睡?
比她想像中好,至少今天熬過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她一個人躺在這棟別墅的二樓客房裡,眼睛依然睜得大大的。
她睡不著。
大概是剛才喝了茶的緣故,她躺在床上腦子裡將一群又一群的羊數了個遍也沒有睡意。一開始她研究了一下自己究竟要不要將這間房間的門反鎖,因為她明明白白地看到厲擇良的臥室就在隔壁。轉念想想又作罷,他要真有那個意思正大光明進來也行,倒不必偷偷摸摸地行凶。
然後她又研究床正上方的那個水晶燈究竟有多少顆,可惜數來數去數目總是不一樣,於是又無聊地再想點別的。
她看了下窗外,這家人愛好很奇怪,大半夜了還將花園裡的燈開得通亮,晃
得她更加睡不著。她起身去拉窗簾,突然靈光一閃,輕手輕腳地開門下樓去,剛進花園就聞到那股香味。她不認識夜來香,卻僅憑著嗅覺在魚池旁邊發現了
那東西。
白色的小花,花莖又帶了點淡青色,開成一團一團的,晃眼一看好像小花球,看起來平平常常還不如含羞草那麼有趣。她有些不甘心地準備蹲下去深深地吸口氣,卻見旁邊有一對幽綠的貓眼出現在那夜來香下面。
探下頭去,看到是那隻貓。
牠側著腦袋盯住寫意。
「這麼晚了,你還不睡做什麼?」她問牠。
這貓是厲擇良的小跟班,但是主人都睡了,牠還不睡。
上次吃過虧,她不會再被牠溫順的外表欺騙而伸手去摸。
「那妳又不睡要做什麼?」
這個聲音突然響起,嚇得寫意一下子蹦起來就想尖叫,而就在她張開嘴,嗓子剛爆出聲音的那一刹那,卻被人從後捂住嘴,將尖叫的絕大部分遏制在了喉嚨裡。
「噓!」聲音的主人說,「妳想給人家來個午夜驚魂嗎?」
寫意這才聽清楚那人是厲擇良。
他放開她的嘴。
「你嚇死我了。」害得她的心臟仍在狂跳,如果此刻她能轉過身來包准要狠狠剜他一眼。
「彼此彼此。」
「睡不著我就出來散散步。」寫意解釋。
「哦,」他調侃她說,「那我就是以為家裡進賊了,出來捉賊的。」
老譚聽到花園裡的響動,開燈走出來,剛好聽到厲擇良的後面一句。
「少爺,捉什麼……」那「賊」字沒出口,便嚥下,退進屋去。
見過捉賊的,卻沒見過這麼捉賊的。
此刻的厲擇良正從後擁住寫意,她的背面緊緊貼在厲擇良的身上,老人家看見這麼一個曖昧不明的姿勢,自然是識趣地退開,哪還提什麼捉賊不捉賊的。
雖說不是光天化日可惜也是孤男寡女,寫意立刻朝前跨一步拉開距離,然後迅速轉身面對他,為掩飾尷尬乾咳了一下。
「那我回房間了。」
「妳不是睡不著嗎?」
「我回房看電視。」
「妳房間沒有電視。」
「……」
她一遇見他,似乎智商就要減半。
他走到魚池旁邊的長椅上坐下,說:「既然睡不著,不如相互解解悶,一起
坐坐。」
這句話聽起來應該是個問句,可惜他是用一個陳述語氣說出來的,可見並非詢問意見,而是由不得她不坐。
若是在平時,能坐在厲擇良的身邊不知是多少女性拚得頭破血流也要爭得的榮幸。
既然這樣,她也索性大方地坐在旁邊。
清新的夜風微微拂面,將她的髮絲吹亂了些,可是拂過皮膚時又有一種別樣的安逸。她在月影中看見他英俊的側面,他的上脣薄一些,而下脣朝下巴的角度稍稍有一點捲,當他將之微微一抿的時刻就夠傾國傾城了。
咳──寫意收住心神,當然成語不能亂用,那是形容女人的。
「想什麼呢?」他問。
「我在想下輩子你……」
她突然頓住發覺自己居然一不小心說漏了嘴,於是再不敢往下講,總不能告訴他,我在想要是你下輩子做女人會不會沉魚落雁吧?那這男人肯定當場把她打入十八層地獄。
「下輩子怎麼?」他似乎瞧出端倪,追問。
「我在想我下輩子要投胎做個非常優秀的男人。」
「嗯?」
「然後一定要娶一個像我這麼可愛的老婆。」她的黑眼珠子一轉,好歹把這句話給說圓了。
他聞言微微一笑。
「妳以前一直都是這麼有意思?」
他說著,抬手抹平她額頭上被夜風吹起冒出頭的髮梢,輾轉又移動到她的下
巴上。
手輕輕一抬,他便使得寫意仰起頭來,接著,寫意看到他那副剛才被她仔細打量過的脣落了下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良言寫意(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5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大眾文學 |
$ 221 |
愛情小說 |
$ 221 |
現代羅曼史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大眾文學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良言寫意(上)
★長銷不墜的愛情經典
★中國熱門評論社區 豆瓣網7.3分暖心推薦
★湖南衛視 芒果TV已搶先買下影視版權
沈寫意自小被同父異母姊姊喚作「野種」,即便遭受嘲諷羞辱,她的性格依然剛烈倔強,從不吃悶虧,一旦與人起爭執,哪怕對方是男生,也照樣一腳踹過去!總是路見不平的她,長大後更成為伸張正義的律師,幫助了眾多女性。
她進入厲氏集團工作,原以為跟冷酷縱橫商場的總裁厲擇良,應該僅止於老闆、員工關係,不料卻撞見他亟欲隱藏的脆弱……
後來寫意為了促成厲氏與東正集團的合作,而和厲擇良爭執不休,他在盛怒之下霸道地提出不對等的合約,使兩人之間的相處產生劇烈變化——
書房裡藏著的泛黃宣紙,一句摸不著頭緒的稱呼,那滿溢柔情纏綿的熱吻……
腿部的疼,遠遠不及胸口的痛,相愛的緣分其實並非偶然。
作者簡介:
木浮生
80後暢銷都市言情小說家,文筆真摯動人,善於刻劃感情糾葛。
生於蜀地,自小喜歡看書,只愛書中那些有關兒女情長的橋段。一直記得亦舒的那句話:「做人凡事要靜。靜靜地來,靜靜地去;靜靜努力,靜靜收穫,切忌喧譁。」所以,惟願自己擁有一顆安靜的心。
代表作《良言寫意》在中國豆瓣網上擁有7.3高分評價,多年來暢銷不墜,並已售出影視版權。
TOP
章節試閱
「怎麼跑到外面來了?」
他的問題沒有帶主語,寫意拿不準是問她還是問那隻惡貓,所以半天不知該不該答,直到厲擇良揚起聲調朝她「嗯」了一下。
「我待得悶,就出來看看。」
「那回屋去吧。」他一邊說,一邊放下小貓騰出手解襯衣的袖口,走回屋子。那隻貓也跟在厲擇良身後,追進了屋。
寫意在後面看他的腳,義肢又裝上去了,不知是真的這麼快就恢復了還是他在強忍。不過,若是他真站著不動,幾乎看不出來那義肢和另一條腿有什麼不同。
厲擇良進門時回頭看了她一眼,寫意立刻埋下頭去。這樣在背後看人家,實在算不上什麼有禮貌。
「客房收拾...
他的問題沒有帶主語,寫意拿不準是問她還是問那隻惡貓,所以半天不知該不該答,直到厲擇良揚起聲調朝她「嗯」了一下。
「我待得悶,就出來看看。」
「那回屋去吧。」他一邊說,一邊放下小貓騰出手解襯衣的袖口,走回屋子。那隻貓也跟在厲擇良身後,追進了屋。
寫意在後面看他的腳,義肢又裝上去了,不知是真的這麼快就恢復了還是他在強忍。不過,若是他真站著不動,幾乎看不出來那義肢和另一條腿有什麼不同。
厲擇良進門時回頭看了她一眼,寫意立刻埋下頭去。這樣在背後看人家,實在算不上什麼有禮貌。
「客房收拾...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木浮生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8-12-13 ISBN/ISSN:978957107885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開數:14.50*21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