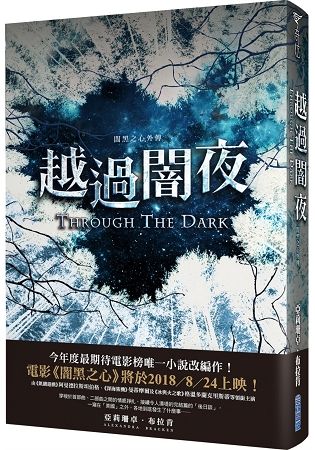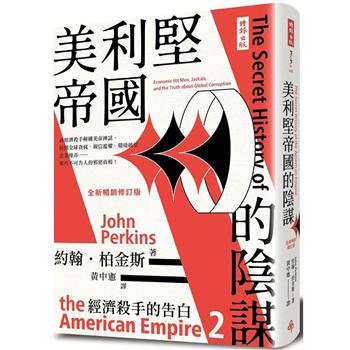千呼萬喚始出來!最初以電子書形式問世,因大受好評,終於集結成實體書,臺灣讀者敲碗多年,美夢成真!
在命定之刻,火花將飛揚於永夜之末……
▎福斯影業改編電影《闇黑之心》,2018年8月24日即將上映,今年度最期待電影榜唯一的IP改編作!
▎《怪奇物語》金牌團隊製作,由《飢餓遊戲》阿曼德拉斯坦伯格、《深海鯊機》曼蒂摩爾及《冰與火之歌》格溫多蘭克里斯蒂等領銜主演!
▎與《飢餓遊戲》、《移動迷宮》齊名,獲選為最佳科幻小說!
▎臺灣讀者盛讚為2015非讀不可的科幻冒險三部曲!
穿梭於《闇黑之心》首部曲、二部曲之間的情感掙扎,接續令人潰堤的完結篇的「後日談」,一窺在「美國」之外,各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外傳共收錄《命定之刻》、《火花飛揚》及全新番外篇《永夜之末》!
〈命定之刻〉
經濟崩壞後,蓋伯的生活遭到重挫。他想成為賞金獵人,卻因抓到的第一隻「獵物」──一名拒絕說話的女孩──而變得更加困難……
〈火花飛揚〉
莎曼的情緒,在看到紅印者出現時盪到谷底。原以為紅印者早已被趕盡殺絕,其實全被洗腦成冷血無情的衛兵。莎曼驚恐地認出了盧卡斯、那在她黑暗童年中唯一的光芒──
〈永夜之末〉
終於被莎曼救出營地的米雅,一心只想找到被迫分離數年的哥哥盧卡斯,卻發現難度遠超乎想像,而她渴望重拾的一切,早已不復存在……
各界推薦
「這是我讀過最棒的書之一。我甚至無法正確表達我有多愛這本書,它觸動了我的靈魂,它就是這麼棒!」 ──紐約時報暢銷書《玻璃王座》作者莎菈‧J‧瑪斯
「一個驚悚駭人卻又引人入勝的反烏托邦世界。露碧被迫成為這世界的女英雄,她身上無法控制的力量,使她同時堅強又脆弱。她絕對會是最受讀者愛戴的小說主角之一。」 ──《科克斯書評》
「書中場景是不久後的未來美國,一個經濟蕭條的醜陋世界,孩子們遭到追捕,深受成人畏懼,就連一間廢棄的沃爾瑪大賣場裡也危機四伏……緊湊劇情最終以令人心碎的結局暫時告一段落,讀者們必定迫不及待地希望這套三部曲的續作問世。」──《出版人週刊》
「反烏托邦小說的全新描寫,不容錯過的作品!」──《羅曼史時報》
「糾結且吸引人的魅力之作。這是你所能想像到最幽暗的世界……布拉肯小心翼翼地依序透露故事背景和解謎線索,逐步推高閱讀時的緊張感……她用真摯的情感來調和書中絕對的殘酷。《飢餓遊戲》系列的書迷一定會喜歡這本書。」──《童書中心雜誌》
「引人入勝、感人肺腑、欲罷不能!」──《紐約時報》暢銷作家梅莉莎‧瑪爾
「驚險刺激、動人心魄,而且殘酷無情……粉絲們一定會深受精心安排的結局所感動。」──《線上書單》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越過闇夜(闇黑之心外傳)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2 |
二手中文書 |
$ 289 |
小說/文學 |
$ 332 |
奇幻 / 科幻小說 |
$ 332 |
西洋奇幻小說 |
$ 33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科幻小說 |
$ 37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越過闇夜(闇黑之心外傳)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亞莉珊卓.布拉肯Alexandra Bracken
土生土長於亞利桑那州,後來前往維吉尼亞的威廉與瑪麗學院就讀。大二時正式嘗試撰寫小說,並在六個月後完成。二十一歲即與經紀人簽約,同一年順利賣出第一本小說。她最近搬去紐約市,在出版社工作,住在書滿為患的可愛公寓。如欲對作者有更多了解,可參考:
www.alexandrabracken.com
Twitter@alexbracken
譯者簡介
甘鎮隴
從事翻譯多年,工作內容涵蓋各種領域。小說譯作包括:《闇黑之心》、《骸骨季節》、《星際大戰》、《星河方舟》、《完美世界》、《玻璃王座》、系列,《末日預言》、《魔獸世界 黑暗之門》、《魔獸:崛起》、《天使殺手》等。
亞莉珊卓.布拉肯Alexandra Bracken
土生土長於亞利桑那州,後來前往維吉尼亞的威廉與瑪麗學院就讀。大二時正式嘗試撰寫小說,並在六個月後完成。二十一歲即與經紀人簽約,同一年順利賣出第一本小說。她最近搬去紐約市,在出版社工作,住在書滿為患的可愛公寓。如欲對作者有更多了解,可參考:
www.alexandrabracken.com
Twitter@alexbracken
譯者簡介
甘鎮隴
從事翻譯多年,工作內容涵蓋各種領域。小說譯作包括:《闇黑之心》、《骸骨季節》、《星際大戰》、《星河方舟》、《完美世界》、《玻璃王座》、系列,《末日預言》、《魔獸世界 黑暗之門》、《魔獸:崛起》、《天使殺手》等。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