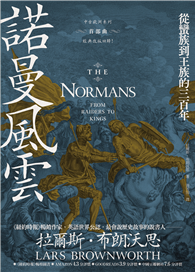/▌ 日子沒有把我們變成更好的人,可是青春有。
那些不好的我們,把我們變成更好的我們。 /▌
‧一場相愛卻也相恨的相遇。
‧如果青春是一場雨,那一定是為你才不停。
‧青春文學小天后「夢若妍」,帶著輕微痛感的純愛回歸之作。
‧微疼系愛戀,不敢忘記的那個人,我們都知道,是你。
▌甜美疼痛的青春之句 ▌
‧我愛你,愛到恨我,愛到恨你。我恨我們相愛,卻又同等分量的相害。
‧青春還留下了許多可能,推進我們向前,卻又扯住我們。所以我們再也放不開,再也被放不開。
‧歲月流轉,自私的情感成長為更純粹的愛。這都是滂沱又燃燒過的,人們稱之為青春所留下的。
‧妳不愛我無所謂,妳愛誰都無所謂──可是妳不可以不幸福。
‧時光會如漏斗,為妳篩出老的美好,與新的妳。被青春狠狠篩過,鑽過無數千瘡百孔、終於還是留下的,妳就安然接受吧。
▌內容簡介 ▌
「從今以後,我愛妳,可是和妳再也沒有關係。」
青春是一場下不停的雨。
但我討厭雨天,雨天總是沒好事,而世上有太多許諾,都不會開花結果。
這些年,我覺得自己善變得有些可悲,可或許有些事終將一成不變。
比如那天,那個人,我曾以為的,全世界。
十年後的許巧茉與十年後的洪文司重逢了。
「茉茉。」他這樣叫出,那個我恨也愛的,我的名字。「妳不愛我無所謂,妳愛誰都無所謂──可是妳不可以不幸福。」
當年曾愛過的一切,都成為難以提及的傷口,縫隙中,一片眼淚滂沱。
那,你還好嗎?我想告訴還在那裡的你,世界沒有毀滅。
日子沒有把我們變成更好的人,可是青春有。那些不好的我們,把我們變成更好的我們。
如果時光可以留住,如果那場雨可以下不停。
如果我可以,再愛上你。
好評推薦
▌青春文學作家真誠推薦 ▌
/馬蘇蘇
「依然靈動的文字,以及令人驚豔的故事安排,情感又真摯到位,讀起來完全停不下來。」
啊啊夢夢的故事還是很棒啊!
文筆依然很精緻,情節也都處理得很好,人物刻劃也很清楚!
功力依然深厚!真的很高興能看到這個故事,覺得能量超滿,整個被補回來!
/艾小薇
「看到結尾時,我一直緊張地確認剩下的頁數。如果青春滂沱,那麼我想雨後天晴也必能見到美麗的彩虹。」
迫不及待就把故事讀完了,很好看喔!👍
看開頭時,一直想到相愛相殺XD雖然開頭還不是很清楚茉茉和文司的過往,但是看到茉茉說我也很痛時,莫名心一揪,覺得好像可以感覺到茉茉的那種痛,我想這都是因為妳一開始就很好地營造出故事的氛圍,所以即便只是開頭,我也很快就入戲了。😄
若妍的文字一直都很有個人特色,雖然一陣子沒閱讀妳的故事,但閱讀時,很快就有了「果然是若妍的風格」這樣的想法,也非常喜歡茉茉每次獨白的部分,很有FU。
看到結尾時,我一直緊張地確認剩下的頁數,心想茉茉該不會真的要……了吧,結果......果然最重要的事,要重要到最後,哈哈!總之,兩個人最後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拭淚)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如果青春滂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56 |
文學小說 |
$ 204 |
愛情小說 |
$ 205 |
網路愛情小說 |
$ 229 |
中文書 |
$ 229 |
大眾文學 |
$ 234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如果青春滂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