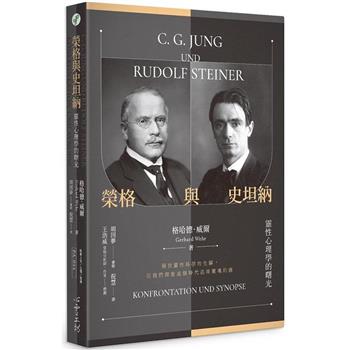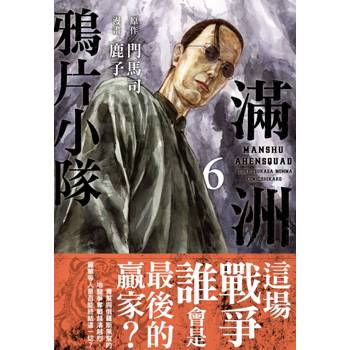序章
願我轉生 任何處與時 喜怒聖尊 權巧緣值遇
願我初生 即能言能行 願我具足 宿命智境通
最後一次見到爺爺時,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不用擔心,爺爺會一路陪著妳,看著妳長大的。」
那是有些沙啞的聲音,但是卻十分溫柔。
溫柔到讓我害怕。
害怕一但開口便會失去爺爺,為什麼呢?
即使我能感受到,爺爺的確就在我身邊。
我能看見他的胸膛正規律地起伏著,也能伸手觸摸他因年邁而起皺的肌膚。
活著──爺爺的確活著呀。
因為往生者的心臟不會再跳動,那爺爺的體溫也不可能自我指尖傳來。
感到安心、鬆了口氣。
這讓我能說服自己暫時忘卻父母親哭喪的面容。
但同時我也感到困惑。
對爺爺為何朝我微笑而感到困惑。
所以我開口了。
「爺爺,」我說。
「怎麼了嗎?」爺爺回道,聲符自他口中虛弱的不可思議,只是那隻輕撫著我的後腦勺的手讓我逼迫自己不去思考這個問題。
「好特別的床。」我指著放在神桌前的那口巨大箱子。
是箱子但也不是箱子。
若不是裡面鋪墊了鬆軟的床墊及枕頭,我便不會稱呼箱子為「床」了。
我並非不知道那口箱子代表著什麼,只是發自內心的不想說出它的正確名稱。
「那是爺爺的床。」爺爺說。「爺爺會睡在那裡面。」
於是,我又開始思考。
什麼是「睡」呢?
生物消除生理疲憊的方法之一,便是睡眠了吧。
一但充份休息後,便能繼續活動。
換言之,若是不再有活動的必要,躺在那口箱子裡的行為就不能稱作「睡」。
所以爺爺錯了。
因為一但在箱中睡去,便不會再醒來。這一點我還是知道的。
果然是謊言。
對爺爺的一字一句深信不疑的我,終究還是被騙了。
被我最愛的爺爺所欺騙。
淚水劃過雙頰,刺痛著我的皮膚。
一切是如此熟悉卻又如此陌生。
和爺爺腿上的那張照片一樣。
和爺爺所凝視的那片木牌一樣
黑白相片上,是爺爺的面容。
檀木牌上,是爺爺的名字。
它們在嘲笑著我,嘲笑我這個傻孫女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
爺爺他,不可以活著。
風鈴──應該是風鈴,在夏夜舒爽的風中任意擺動。
雲霞和星夜混融,緩慢但穩定地流動著。
和時間一樣。
緩慢,但無情地流動著。
再不開口就來不及了。
在我失去爺爺之前,我必須得到答案,得到爺爺親口給我的承諾。
「爺爺,」
因為我沒有選擇了。
「爺爺死掉了嗎?」
爺爺笑了,淺淺的笑容。
他緩慢地將目光從我身上移到我所注視的那片星空。
「對,爺爺已經死了。」
我原本以為自己會因為爺爺的答案而變得驚慌失措。
但是沒有。
因為我想,這只不過是一場夢。
夢境的發展再怎麼荒謬,都是可以被原諒的。
「不過,不用擔心,因為爺爺已經答應我最寶貝的孫女了。」爺爺握緊我的手,起初我並不知道爺爺的用意。
「就算爺爺死了,爺爺還是會陪著妳長大,我們打勾勾說好了。」
爺爺異常冰冷的小指牽動著我的指頭。
我感到視野再度矇矓。
「所以,」爺爺說。「要是爺爺沒有醒來,要記得叫醒爺爺。」
玩笑話。
但我還是像爺爺一樣笑了,數不清第幾次被爺爺逗笑。
卻是第一次,因為被哄騙而笑。
來自不同人口中的叨絮聲終於停止了,那時我在黑傘蔭下。
看著爺爺的棺木被泥土逐漸吞沒。
只是我絲毫感受不到悲傷。
「答應爺爺,不要為爺爺的死流淚。」
畢竟,只有我知道。
這是那天爺爺親口告訴我。
「因為爺爺和乖孫女約定好了。」
到現在我仍無法忘記那天窺探著祖孫倆對話的風鈴聲。
「所以,爺爺會回來的。」
還有爺爺給我的承諾。
直到最後一鏟土覆上棺槨前。
我會再次喚醒你。
因為我們說好了,爺爺。
第一章
秋意悄聲無息的來臨,若非窗外那槭樹上泛紅的葉瓣,想必我會就這麼與輕薄的汗衫度過人生的第二十二個冬天。
與其在這座小島上定義四季變化,不如將心力拿去提防午後的暴雨或是伴夜霄而至的寒流。我想這是兩千多萬人的共識。
因此,即使我沒有感受到明顯的溫差變化,還是形式般地披上那件被擱置於床頭的薄外套。
時鐘滴答作響。推開房門,尚未將睡意完全驅散的我視野朦朧仍能仰仗半年來的居住經驗找到浴室的正確位置。簡單盥洗後,才驚覺朝陽若晚霞似地落於廊上,茶褐色的布簾也無法阻止涼風無情地灌入室內,
此時,我才真正感受到涼意,沁透全身的涼意。
我試著關緊窗戶,但年久失修、有些變形的窗框僅發出膠皮相互摩擦,嘶啞的難聽聲音。
咿呀──
聲音再度響起,旋即萬物回復死寂。
我想自我離開房間,來往浴室時應該也製造了不少聲響,只是隔壁房內似乎完全沒有動靜,宛若空閨,不存在任何生氣。若要說在這屋齡超過三十年的老房子內發生了命案,那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遺體此時就僅與我相距一門板之遙。
為了避免同住一個屋簷下的人真就此長眠,我敲了敲門,飽受歲月洗鍊的厚重木門發出略顯低沉的聲音,約莫五秒後,宛若呻吟般痛苦的迴響才自門縫傳入我耳裡。
「去買早餐……」
還活著呢,真令人感到欣慰。
「想吃什麼?」我隔著門喊道。
只是沒有再得到進一步回應。
總之就是「老樣子」。那傢伙或許是覺得每天重複同樣的話題很無趣所以拒絕回答,也有可能只是單純被強烈的睡意再度拽回夢鄉,唯一能確定的是,短時間之內她都不會踏出房間。
於是,我也只能強迫自己停止無意義的猜測,帶上幾個銅板離開這不太溫暖的家。
一大清早的山色總令人迷茫,半年前剛從市區搬回老家的那陣子我還相當沉醉於晨間霧色溟濛的景致,只是如今熱情不再,徒留露水吸附在皮脂上的黏膩與煩躁。
走過被私人菜園夾道相迎的小徑,我才算是正式踏入人煙區,紅土泥地與低矮騎樓構築的環境讓人不用查看路牌也能意識到這裡的確是坐落於台北山區的某個不知名鄉里。
雖然小聚落的生活機能讓我在高中以後就不得不提早體驗離鄉背井的生活,但五年過去了,我仍像受到某種神祕力量驅使般,最終還是回到這個記憶早已淡薄的家鄉。
若要用我們這行的行話形容,那便是「落葉歸根」了。無奈的是,我是連同枝條一齊被扯下,連凋零的機會都沒有。
輟學生的身分讓任何藉口都顯得無謂。何況,當初我還是連一個像樣的藉口都拿不出來便向學校申請退學。
所幸,鄉里的居民並沒有對我這個突然放棄學業返鄉的青年報以過多好奇的目光。
──長大不少喔,上次看到你才這麼高而已。
巷口修三輪車的老伯看見我後,腦中第一個浮現的也僅是某個十歲小男孩的模樣吧──對他而言,男孩似乎是一種永遠無法成長的生物。
這對我當然是再好不過了,厚著臉皮回老家多少有些逃避現實的意味,若是有風聲又流竄於街坊間,恐怕我連這最後的棲身之所也會失去。
幸好,這終究是個時光也得在此駐足的無名小鎮。
我停止思考,拒絕讓意識再度沉浸於這略顯刻意的多愁善感中,取而代之的便是無意識地漫步於街頭。
「早安!」為了抓住分神的我,對方肯定叫喚了不只一次,早餐店的阿姨有著一副大嗓門,卻還是沒能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力,這可能也與她毫無魅力的發福身材有所關係。
「早。」
「培根蛋不加小黃瓜嗎?啊你咧?要吃什麼?」沒等我開口,阿姨連珠炮似地拋出問題。一槭從來不會更改餐點,所以在阿姨眼中我這口味捉摸不定的客人或許更棘手一點也說不定。
「蛋餅,不加料,最便宜的那種。」
若是不這麼說她會在裡面偷偷塞培根,而且絕對不會忘記要跟我多收十元。
「原味蛋餅,加奶茶嗎?三十五元。」她似乎根本沒打算給我回答機會似的,擅自篤定我一定會加購奶茶。
而我也確實這麼做了,可惡。
「要稍等幾分鐘,裡面先坐一下喔。」說完,她好像朝裡頭使了個眼色。
早餐店裡僅擺了兩、三副桌椅,在這目測五坪不到的小店面也是極限了,而這也無可避免地導致坐在角落的那名男子身型看來格外巨大。
打從我出聲起,他便放下手中的報紙,在等待最佳的介入時機。
那時機就是我點完餐,與煎鍋前的女人產生短暫空白的剎那。
「喂,一楓。」雖然男人已不再年輕,他半禿的頭頂與快撐破襯衫的肥胖身軀正好佐證這一點,但聲音仍富有威嚴,這與他的職業脫不了關係。
翁叔是附近派出所的巡警,和過世的父親是老相識,我私自認定是這層關係讓父親任職的禮儀公司接到不少額外工作。
不過我一點也不想和警察扯上關係,只是依稀記得公民教育期許每個善良市民與警方通力合作,才只能努力撐起笑容回應。
「你臉色怎麼這麼難看?簡直跟你妹妹一樣。」
看起來翁叔對我的笑容很不滿意。
「哎,總之先別站在那裡了,來來來來。」他招手示意我過去,和逗小狗玩的方式如出一轍。
不論是培根或是煎蛋一時半晌都不會離開煎鍋,因此我也只能任由這位人民保母擺布。
我拉開他對面的凳子坐了下來,他熟練地將報紙摺好後丟到一旁,隨後又從胸口口袋取出一支菸,整個動作流暢地像是預先演練多次一般,在每個受過本土劇薰陶的老百姓眼裡簡直就是準備開始偵訊的架勢。
「不抽菸吧?」他問道,是個不提起就無法延續對話的老問題,我很快地搖頭回應。
「很好,抽菸傷身,死得早,跟你爸一樣。」
「我爸沒抽菸。」
「我知道。」
銜在翁叔口中的香菸已經點燃,煙霧宛若未爆彈隨時會從他口中迸發,我下意識地屏住呼吸。
可惜,仍然逃不了被廢氣糊一臉的命運。
「最近生意如何?」
「一如往常。」
「一如往常地差嗎?真是完全不意外!」翁叔笑道,完全沒有掩飾幸災樂禍的態度。「能撐到現在也不錯了,不然早該趁你爸走了時候順便收掉的。」
「這是一槭的決定,我管不著。」
說是這樣說,但其實我們兄妹工作分配很清楚──一槭想管的歸她管,她不在乎的,例如打掃、洗衣服等雜務則歸我。
解釋起來有點悲哀,當我沒說好了。
「以前我就跟你爸說,現在這種時代啊!哪來的死人骨頭讓你撿,都馬燒一燒就沒了,還在那邊埋,多麻煩!」
一閃神,這名身型肥胖的員警不知何時竟開始說起教來了。
「當初你妹妹說要繼承你爸爸幫人撿骨時我們都勸過她啊!先把書讀好,不要想急著賺錢,有什麼困難大家都會幫忙。」
「經濟方面倒是沒有問題,我們是在老爸朋友的禮儀公司工作,對方到現在也沒打算要我們走路,我想一槭她應該做得不錯。」
我試圖辯解,只是胖大叔完全沒有要聽我說話的意思。
「而且一個漂漂亮亮的女孩子跑去做這種事,別說我們,往生者的家屬看到也會覺得奇怪,你們這樣生意也不好做,不是嗎?所以我就說了,你們還年輕,未來的路……」
唉。
已經不知第幾次了,果然還是無法溝通。
「翁叔,你有什麼事就快點說吧。培根煎好我就要走了。」我實在沒有耐心聽長輩的貼心叮嚀,何況是每次見面都會出現的老生常談,只能催促他盡快切入正題。
但這可能也在這名萬年巡警的算計中,他叼著煙,從懷中取出一張相片捻在手中。
「也不是我愛唸,只是每次碰到這種事就會想到你們。喏,最近你們有沒有收到比較難看的?」
當我想伸手取走相片時,翁叔又再度將那張相片收入外套內襯中。「這年頭土公仔賺不了錢,你們公司碰上那些不好處理的就會丟給你們吧?要不是你妹妹,那種叫小孩子做這種事的黑心企業我早就叫小夥子三天兩頭去拜訪!」
剛才苦口婆心的雞婆長輩現在倒是扮起正義使者了。
雖然他本來就是正義使者啦……只是喜歡用很不正義的方式處理事情而已。
我忍住挖苦他的衝動,回覆翁叔剛才的問題:「沒有,已經一個多月沒有碰上事故案件了。」
「不過,那時候殯管處的無主屍招標是你們公司得標吧?所以這一帶來路不明的屍體應該都被你妹碰過吧?」
把別人的妹妹說得好像有奇怪癖好似的,雖然某種程度上的確沒錯。
「平常有其他員工負責,通常是人手不夠或沒人想碰才會輪到我們處理。」
而且實際出力的都是我,妹妹她只會袖手旁觀,甚至連家門都不會踏出一步。
無暇糾正翁叔的措辭,我僅是簡單的解釋道。
「像是悶在家裡幾個禮拜才發現的、泡在水裡太久的、斷成好幾截的,如果只是單純不知道身分還輪不到我們。」
再說,我們也只是去現場回收而已,後續的工作……例如遺體修復這類細活不僅不是我和一槭能插手的專業領域,也不在正常的禮儀公司業務範疇,至於替亡者上妝則分屬在禮儀師的業務,不論是我或一槭的歷練都還遠遠不足。
說穿了就只是撿人家不想做的工作而已,並不是多了不起的活兒。
況且,這還是因為土葬式微後做出的妥協,僅是因為不想成為公司的寄生蟲而不得不兼任的工作。至少我是如此解讀的。
「那這種咧,算是你們負責的吧?」翁叔像是得到滿意的解答,這才像鬆口氣般,將那張照片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一片燒得如焦炭般的木板。
鋪蓋於上,黑與白的斑紋乍看之下無規律的交織著,若不是尚存的木頭紋理,這片木板又猶如爬滿了黴斑令人嘔心。
只是,這片木炭絕對不是尋常物,否則老警察也不會小心翼翼地將它收於懷裡。
仔細一看,碳化的木板似乎隱藏著某種紋路。
我瞇起眼睛,試圖專注於眼前這張畫質稍嫌低劣的四乘六吋相片。
紋路。
人形。
有人在上面。
頭、軀幹、四肢,隱隱約約有如人影顯現於木板上,好似拍響了巴掌印在板子上的昆蟲殘軀,黑壓壓地屍骸烙在上頭。
「好像有個人……印在木板上面?」我對自己的答案沒有十足把握,只是稍微推測翁叔期望我給予的答案罷了。
「不錯。」他又將手伸進外套的內襯口袋中。「平常看你總是被你妹妹牽著鼻子走,現在看來你也不是老在打混,對這種事多少還是有點敏銳度的。」
接著,他取出另一張照片,照片同樣是碳化的木板,和第一張照片一樣,旁邊也擺放著量尺,因此可以得知兩片木板大小幾乎一樣,不同的是,這張清楚勾勒出人類的輪廓在木板上。
木板中間的區域,顏色明顯比其他部分淡化許多,所以能很清楚識別人印。
「這一片是在土城那裡找到的,原本被人丟在橋下,剛好被遊民撿到。剛才給你看的那一片則是……嗯。」
「是……?」
「在你家門前撿到的。」
「靠杯喔。」
「沒啦沒啦,沒有離你家那麼近,是在你家隔壁的竹林裡找到的。」
那不是差不多嗎?
翁叔繼續說道:「別說你,這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出現在這搞得我們這種小派出所也跟著緊張起來。因為發現了這種東西,所以想問問你們那有沒有接到被人燒掉的。」
翁叔的問法簡直就是在宣稱他對這幾張怪異的照片已經有了解答。
我在剛才吃了這胖子的虧,因此也忍不住挑戰起資深員警的權威。
「單憑這兩片木板警方就推斷是命案嗎?說不定這只是無聊人的惡作劇而已。以現在的技術要從木板上採集人體組織啥的應該不難吧?」
畢竟人印木板就丟在我家附近,我當然沒辦法輕鬆看待。
沒想到我這番話反而引來一陣訕笑。
尤其是當他那肥大的肚子隨笑聲抖動時更讓我莫名惱火。
「你們這些年輕人真是電視看太多了!什麼東西動不動就要送鑑識中心,如果每件案子都照你們這樣辦國家有再多錢都不夠花!再說,都燒掉了怎麼驗?」
「搞不好還有沒燒乾淨的部份不是嗎?要想破案的確走這條路是最保險呀。」
「我可沒說這是案子啊。」翁叔搖搖頭道:「所以才先跑來問你們,你也說這一帶沒人領的都是你們公司負責,那既然沒收到遺體就代表根本沒有什麼命案。跟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地火明疑:少女撿骨師系列(1)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地火明疑:少女撿骨師系列(1)
西方鑑識科學 x 東方民俗信仰!
繼承家中撿骨(二次葬)事業的美少女,
即將解開各種離奇難解的事件──
★人氣插畫家VOFAN擔綱人設、封面!
★好評推薦
奇幻小說家(喬治馬丁地球人獎首屆得主)/余卓軒
奇幻、驚悚、浪漫、科幻全方位作家/星子
「本故事不會以驚悚嚇人的案件為賣點,更為著重在人情方面,希望能讓推理小說普遍灰暗的風格中映照更多人性曙光。」──新生代小說家/八千子
★本書《地火明疑》獲得108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
【內容簡介】
我和妹妹一槭經營父親留下的禮儀公司,過著生意慘澹的貧窮生活。在這樣的某一天,安排近日開棺撿骨的家屬突然來訪──對方的孫女宣稱,她妹妹無法從爺爺過世的傷痛中走出,一直堅信著爺爺會復活,而且隨著開棺日接近,行為變得越來越詭異。一槭察覺事有蹊蹺,在「復活」背後隱藏的謎團究竟是?
另一方面,附近的巡警翁叔給我看了兩張照片,照片上是焦黑的木板,詭異的是上頭卻留有人形輪廓般的印記。沒過多久,同樣的木板接連被發現,案情逐漸往連續殺人案的可能發展……
作者簡介:
八千子
感謝本作品獲得108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
這本很厚,就算沒有要看也可以用來砸人。
已出版作品:尖端第三屆原創小說大賞逆思流組特別賞《證詞》。
繪者簡介:
VOFAN
台灣的插畫家,喜歡拍照、以及穿著白色細肩帶洋裝的少女。
章節試閱
序章
願我轉生 任何處與時 喜怒聖尊 權巧緣值遇
願我初生 即能言能行 願我具足 宿命智境通
最後一次見到爺爺時,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不用擔心,爺爺會一路陪著妳,看著妳長大的。」
那是有些沙啞的聲音,但是卻十分溫柔。
溫柔到讓我害怕。
害怕一但開口便會失去爺爺,為什麼呢?
即使我能感受到,爺爺的確就在我身邊。
我能看見他的胸膛正規律地起伏著,也能伸手觸摸他因年邁而起皺的肌膚。
活著──爺爺的確活著呀。
因為往生者的心臟不會再跳動,那爺爺的體溫也不可能自我指尖傳來。
感到安心、鬆了口氣。
這讓我能說服自己暫時忘...
願我轉生 任何處與時 喜怒聖尊 權巧緣值遇
願我初生 即能言能行 願我具足 宿命智境通
最後一次見到爺爺時,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不用擔心,爺爺會一路陪著妳,看著妳長大的。」
那是有些沙啞的聲音,但是卻十分溫柔。
溫柔到讓我害怕。
害怕一但開口便會失去爺爺,為什麼呢?
即使我能感受到,爺爺的確就在我身邊。
我能看見他的胸膛正規律地起伏著,也能伸手觸摸他因年邁而起皺的肌膚。
活著──爺爺的確活著呀。
因為往生者的心臟不會再跳動,那爺爺的體溫也不可能自我指尖傳來。
感到安心、鬆了口氣。
這讓我能說服自己暫時忘...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20/10/10
20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