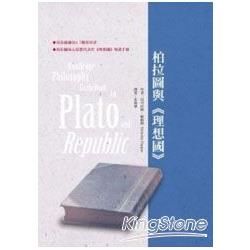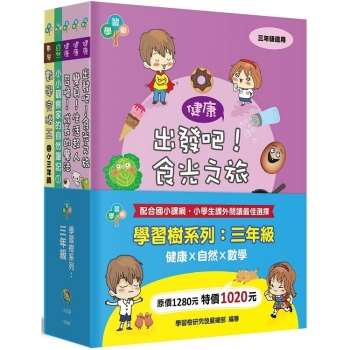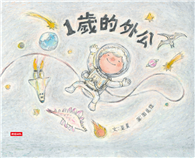再版序
我是十年前開始寫這本導讀的。毫不懷疑,完成一本關於柏拉圖《理想國》的讀物,會花費我大量時間與心血。當這本書印刷出來,我試圖把它用在課堂上時,開始注意到它的缺陷。同時,書評、同事和學生的評論也提出了需要修改之處。很高興有機會對之進行改正,不用再為這些錯誤感到遺憾。
從第一版到第二版的許多改變都是不引人注意的。有時是一個詞的錯誤,有的地方論證需要一句話解釋。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更多的是,文中某處一段話被加上或者刪除。這些改變是為了消除錯誤,並改善書的風格和可讀性。
有時一個新的註解出現不止一次,例如對衛國者的本質所做的一些思考。我強調(以前沒有),柏拉圖將城邦的統治者擬作狗,是為了說明一個事實,民主制製造出來的動物不能恰當地說是自然的還是人工的。一個僅僅建立在習俗或者人工基礎上的城邦必定會毀壞,就像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所說的,因為它的道德前提和人的本質對立。馴養狗向柏拉圖指出了一個跨越自然過程和文化價值裂隙的橋梁,以便社會不被瓦解,而自然法則能夠接受它。
最明顯的改變是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在這幾章提出了一些貫串《理想國》的論題,論述太廣泛以致不能適用。第十章關於柏拉圖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不再包含它在城邦和靈魂之間類比的討論,其包含兩個新的論述,一個是關於柏拉圖的家長式統治,另一個是關於《理想國》的理性擴展定義。後者使得《理想國》的兩個心理學正義的討論比以前更密切關聯。第四卷是一方面,第八、九卷是從另一個方面對靈魂的狀態進行考察,柏拉圖將之也等同於倫理行為和幸福,而其基礎是對靈魂的籌算部分有顯著不同的概念。有時我在第四卷的討論中提到了後面,有時在第八、九卷的討論中又回顧了前面;但是沒有一個處理方式真正關注《理想國》行文中的理性結果。在第十章新增的部分彌補了這個空白。
第十二章關於柏拉圖對詩歌的對待方式同樣也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總結柏拉圖關於美的理論,思考他為何如此高度地頌揚美而鄙視藝術;另外一部分超出了《理想國》,說明亞里斯多德反對柏拉圖而為詩歌辯護。我尤其請讀者注意前者。美是柏拉圖喜愛的一個相的例子。讀者首先遭遇到《理想國》對詩歌以及其他藝術形式的抨擊,這可能對反對它們使我們想到的簡單化的柏拉圖有用,那種簡單化的柏拉圖,使一個清教徒和吹毛求疵的傢伙,同時保留著對美的深切而持續的愛慕。
我很自豪地稱紐約城市大學是我們的學術之家,並樂於感謝它。沒有學院的休假制度支持和研究哲學的同事的思想支持,我就不能完成第二版。Michael Levin 和 David Weissman 教授的批評我已經努力吸收。John Greenwood 和 Claudine Verheggen 教授與我的交談,以非常廣泛的方式激發了我的思想,以致我無法指出我的哪個論點來自他們;他們也將發現他們在本書中的影響。
在城市大學我有太多優秀的哲學學生,在此無法全部列出他們的名字,但直接映入腦海的名字有 Shontanu Basu、Joseph Brown、Amalia Rosenblum、Stephen Sykes,因為我記住了他們在課堂上的論點,我在書的頁邊記下需要改變的觀點。我與 Albert Weeks 的通信探討了大量或大或小的修改,我很高興有此機會感謝他。另外,我必須提及的是,紐約猶太大學的 Ruth Bevan 教授以及她出色的政治科學優等班上的一些學生。在修改第二版的時候,我與這些學生就《理想國》進行了討論,並且極受益於他們的回答。第十章關於柏拉圖的家長制作風那部分,就是來自這次討論。
我讀到對本導讀的每篇書評都教給了我一些東西。不過在對其他人心懷敬意的同時,我想單獨指出 Susan Sauve Meyer 在《心靈》(Mind)中的書評,雖然嚴厲卻不失公允。我已經努力用本版的一些改變來答覆這些批評,也同樣處理了其他讀者的擔憂、疑問和抱怨。我的答覆不甚明顯,不過,此處或彼處的一個說明性段落,一個收回的假設,一個論述的調整,都表明我聽到了批評的聲音,並把它們放在心裡了。
我寫本書主要是因為導讀叢書的編輯 Jonathan Wolff 認為我值得受邀寫關於《理想國》的導讀,並在他不斷的鼓勵下完成了此書。我早就應該感謝 Jonathan 了─要感謝他的地方太多太多。把柏拉圖的《理想國》介紹給讀者,加入這一悠久的傳統,對我來說,是一項難以估量的殊榮。
初版序
為什麼又寫一部對《理想國》介紹的書,或者說,為什麼寫這樣的介紹?柏拉圖不藉助任何幫助就能吸引沒有基礎的讀者。他生動的戲劇化對話,經常敏捷地遊走於世俗現象和形上學意義之間,他態度嚴肅地對待知識、道德、社會和死亡問題─所有這些都以令讀者難忘的輕盈散文寫出─這已使他成為歐洲歷史上最被廣泛閱讀的哲學家之一。
不過柏拉圖的對話風格雖然吸引人,但是,當讀者要想對它覆蓋的領域獲得一個概要的把握,或者對其中某一點的關注細緻程度超出一個對話所允許的範圍,或要分離出討論的諸多前提以發現是哪些在起作用,或要找出對其一個論點柏拉圖不同的論述方式並發現每次重述所得到的結論時,柏拉圖的對話風格都很少給出結果。在柏拉圖冗長的對話中,重要的問題出現而後消失:柏拉圖提出這一點僅僅為了偏離到另外一點去,或僅僅為了使他的論述更為詳盡。最後,起初的那個問題又重新出現了,但是已經被變形和偽裝起來。那些對對話的轉承感到迷惑的讀者,可能希望柏拉圖就對話中的這些論點寫一些論文,雖則平淡乏味,但會更清晰,如果必要,也可更長一些。
我希望本書能夠作這樣一個導讀。我大都緊密地追隨柏拉圖自己對觀點的論述。在每一點上我都先講清楚柏拉圖的立場,然後再來分析、批評或者展開它。(我只是在討論第五至七卷的時候離開了柏拉圖的說明順序,首先概述了政治理論,然後專門討論形上學。)本書大部分(第二部分)是對文本的解釋,並且中間停頓下來作進一步的討論。後面的幾章常常回到前面相關的章節,以便把同一主題的不同處理方式聯結成一個整體。為了同一目的,我標出了在《理想國》中我認為是基礎的前提或假設,並標識上號碼1、2等。這樣做一則是為了我能夠簡便地提到柏拉圖的重要論點,二則也是為了使讀者能夠發現《理想國》起先幾卷的論述步驟,以及它們在後面幾卷中的作用。最後,結尾三章回到一些一般性的問題,它們來自對《理想國》的整體討論。它們過於簡短,但又不得不如此,只有這樣才不至於變成另一本書。但作為對這些問題的初步涉及,它們顯示了如何通覽整個對話。
除了展示出《理想國》的總體架構,我還強調了它與日常觀念關係的複雜性。人們極容易陷入這樣的看法,認為柏拉圖是提倡彼岸理想的理念原型(或模型)的哲學家,因此,在政治學上是個烏托邦主義者,在倫理學上是與其世俗形式完全無關的一種「正義」鼓吹者。但《理想國》的論述不但要使未受過哲學訓練的讀者明白曉暢,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拋開了日常觀念的理論推理視角。這種雙重目標在對話中造成了一個有成效的張力,這一點無論是在第一卷中從一種對正義的行為定義轉向一種內在定義,還是在第四卷中力圖把德性心理學解釋適用於日常變化,或者是在第五卷把哲學家同其他公認的知識愛好者相互區別,都可以顯明地發現。這個張力在《理想國》關於理性的本質矛盾中尤其引人注目(特別是在第九卷);但這也表現在蘇格拉底一再重複的雙重論述策略中,他對一個觀點進行理論確證,同時使非哲學家也能明白。柏拉圖當然達到了否認日常經驗價值的結論,但是如果他不是富有成效地從日常經驗中激發出它們的話,這些結論也不能保留其力量。
在本書的寫作中,我首先受到了 Julia Annas 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導論》和 Nicholas White 的《柏拉圖的〈理想國〉手冊》的指導。了解這些優秀著作的讀者會發現我從中廣泛地汲取了營養。除此之外,Cross 和 Woozley 關於《理想國》的著作,對我觀點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為了保持一種直接的和不勉強的表達方式,我省略了傳統的參考文獻部分,雖然我本來應該聲明,在寫作本書中,我對這些參考文獻在知識上的欠負極大。對這些參考文獻的一種非正式的替代是,我在每章的結尾都給出了一個對本章說明最有影響的書和文章的簡短目錄。讓讀者先看到這些文獻,以超出我所談論的東西,我認為這是最好的地方。本書的文獻目錄同樣也是為了這兩個目的─標出我所倚賴最多的文獻來源,指導讀者自己進一步探索。我相信,此處列出的作者會發現我的處理受到他們的薰陶之處。
所有對《理想國》的引用均出自 Allan Bloom 的譯本(紐約:基礎書籍,1968)。我僅在關於「理性」(reason)和柏拉圖的「相」(Forms)之討論中未採取他的用法,對前者他不常這樣用,對後者他根本未用。
我對兩個機構深表謝忱。我在計畫這本書時還在 Hollins 大學任教,它慷慨地支持我寫作本書的初稿。然後我轉去紐約城市大學,在此處對手稿進行修改;對它在我準備本書時所提供的物質支持表示感謝。
其他應感謝之人也幾乎難以計數。Cyrus Banning 對我的影響無以言喻,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讀《理想國》。Eugen Kullmann、William McCulloh、Martha Nussbaum、Steven Strange、Donald Morrison 給我長期的指導,對此感謝難以言表。我希望以此書讚揚我的老師 Stanley Cavell,因為他,我對什麼是哲學理論,需要怎樣以及不應怎樣獲得了最深的體會。Hollins 大學的同事在我完成這個項目中給予我的建議和對我的幫助超出了他們的想像,由此本書才得以面世。感謝 John Cunningham、Peter Fosl、Allie Frazier 和 Brian Seitz,雖然我離開了 Hollins,他們的指點卻以各種方式留在本書的每一頁上。我對 Michael Pakaluk 也深為感激,他讀了很大篇幅的初稿,不但使我免於許多錯誤,而且對我指出如何論述會更好。還要感謝我在 Hollins 和城市大學的學生們。我僅指出 Jennife Norton 和 Caroline Smith 對本書的貢獻,不過我還可以輕易說出其他很多學生的名字。
我對我的父母有無盡的感謝,把此書獻給他們,他們使我受到教育,在我寫作本書時他們給我以莫大鼓勵。最後,感謝我的妻子 Barbara Friedman。在過去的兩年裡,她在各個方面給予我幫助,閱讀草稿並且和我討論。
譯者序
柏拉圖是西方哲學史的鼻祖,他的思想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孔子在中國思想中的地位。懷特海說過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全部西方哲學傳統都是對柏拉圖的一系列注腳。」這句話可以為上面那句話作注腳。然而,這句話看起來很誇張,實際上並沒有達到人們想的那種程度。柏拉圖的思想實質確實一直滲透到西方思想的血脈中,從未斷絕。即使現代以來解構西方哲學和形上學的努力,又何嘗不是以柏拉圖的思想為對照。相對他以前的哲人,柏拉圖著述頗豐,幾十篇對話著作歷經兩千餘年流傳下來,尤其可以作為柏拉圖思想的代表作,當屬這部《理想國》。雖然一般而言,他的思想被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每個時期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特點,有發展,有變化。但是,一般被標誌為「柏拉圖思想」的,仍然當推他中期思想,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理想國》。和《理想國》同一時期的其他著作都沒有這本書這樣全面地展現其思想。《理想國》集柏拉圖的政治學、倫理學、本體論和認識論於一體,並以他的本體論─相論─作為基本原理,把這幾個方面貫連起來。除了這幾個方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甚至還探討了兒童的教育計畫乃至詩和美學問題,可謂洋洋大觀,美不勝收。
不過,這樣一部著作按照常理推斷也不應該是一目十行的閱讀就可以把美景盡收眼底的。確實,《理想國》不是一部容易讀懂的著作。開頭部分類似朋友的閒聊,人們可以較為輕鬆地跟上,但是它只是一個序幕,漸漸把人誘入最深奧的形上學殿堂。中間極其晦澀的相論和辯證法往往使人百思難解。結尾部分是一個神話故事,它通俗易懂,讀者可輕鬆明白,彷彿穿越了晦暗茂密的叢林,來到草地上安歇。但是人們對叢林裡面的路徑仍然迷惑,雖然穿過了它,仍然驚疑不定。就連人們最津津樂道的《理想國》三個比喻也不能完全地給人們以安慰。這三個比喻─「太陽比喻」、「線段比喻」、「洞穴比喻」,給了讀者理解柏拉圖的相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一條線索,但就連這些試圖解釋相論的比喻自身都是那麼模糊,它們給人的大都是一種詩意的甚至是神祕的暗示,而不是直接的陳述。尼可拉斯.帕帕斯的這本書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穿越這片叢林的路標。
就像帕帕斯在自序中所表明的,他的這部導讀大致根據《理想國》自身的結構和順序進行介紹和解釋,除了對第五至七卷的形上學和認識論單獨提出著重闡釋(第七章)外,皆按照柏拉圖對話的順序進行說明和解釋,有利於剛剛涉足柏拉圖哲學以及要對《理想國》初步涉獵的讀者達到自己的閱讀目標。這個導讀把對話的每個階段都指示了出來,不但對大的轉承關係作了說明,而且對每個階段包括的問題也一一點出加以解釋。至於那些對柏拉圖的敘述中錯綜複雜的問題感到迷茫的讀者,提供了詳盡的指引。
同時,本書對研究柏拉圖的專家也不無裨益。作者在各個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且在每一章的末尾都為欲進一步研究者列出了研讀書目。對那些為柏拉圖思想深深吸引,卻苦於其對話風格的散漫和過於詩意而缺乏現代論文的論證者,這部導讀也可以作為研究方法的示範。就正義這個具體的問題而言,帕帕斯注意到,柏拉圖雖然在引入國家的正義這個題目的時候,貌似把它作為靈魂中正義的「大寫」,為了更清楚地看清靈魂中的正義而提出來的。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城邦中的正義絕不只是具有類比意義。因為,在後面的對話進展中,柏拉圖一直把城邦作為自己的題目。這說明,對靈魂的正義和城邦的正義都是柏拉圖認真考慮的論題。如何理解起初柏拉圖引入城邦的正義和後來實際的討論所造成的印象差異?帕帕斯指出,論述目標的分離實際是《理想國》的特點(第五章)。柏拉圖提出了兩個舉足輕重的題目,任何一個都對人正義的生存非同小可。所以,任何一個題目都不只是作為另一個題目的陪襯而出現。帕帕斯還看到,柏拉圖在尋求理想的正義時,並沒有完全拋開現實中的正義觀念,或者說是日常的正義觀。
擁有理想正義的人,他的靈魂必然是有秩序地運行,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其中欲望部分具有節制的美德,激情部分具有勇敢的美德,而理智部分具有智慧,整體而言協調一致,符合理想的正義。由於遵循傳統的道德觀念而具有日常所謂的正義美德之人,例如克法洛斯,雖然從外在的行為上來看也是正義的,但是他並不真正懂得正義自身,沒有把握關於正義相的知識。所以,嚴格地說,也不能說是正義的。不過,柏拉圖在把哲學理論和日常觀念如此分裂開來之後,隨後又縫合了這個裂隙。因為柏拉圖指出,一個靈魂具有正義的結構之人在俗世最大的報酬就是幸福,正義的靈魂是最幸福的靈魂。而一個實踐日常的正義的人是幸福的。這種幸福不只是精神上的良心安慰,而是事實上的日常幸福。在這兒,柏拉圖努力使他的正義觀念和幸福觀念符合世俗的標準,最大可能地在理想國和現實國度之間架設起可以通達的橋梁。這也是他作為一個嚴肅的哲學家標誌。他不是對現實閉目不看,神遊天外,冥想一種虛無縹緲的烏托邦,而是要對現實問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作為專門的研究文獻,這個導讀也不乏真知灼見。
本書翻譯由於時間倉卒,對原文未及反覆商榷,粗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專家和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