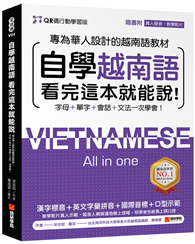我們可以說,心靈和上帝是人的智力範圍內所能知道的最確切、最顯然的事情。我的六篇沉思,千言萬語,沒有其他目的,只是想要說明此一觀點。-笛卡兒笛卡兒於一六四一年完成《沉思錄》一書,其原文書名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揭示了整本書的主旨。所謂First Philosophy即第一哲學,來自於亞里斯多德的用語,為哲學中最關鍵的問題,也就是所有哲學問題的先決條件。書中共包含了六個沉思,從各個角度證明上帝的存在與靈魂的問題。他的語言與論述方式直到今日仍具有廣大的影響力,而此書也成為所有哲學愛好者必讀的經典之作。
本書特色
本書除收入《沉思錄》外,也一併收入《哲學原理》一書,此二者皆為笛卡兒的思想代表作。
作者簡介
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
以「我思,故我在」聞名全世界數百年的法國哲學家,同時兼有數學家、物理學家的身份,其理論奠定了現代哲學的基礎,並開拓所謂的歐陸理性主義,深深影響後世的研究者如史賓諾沙、萊布尼茲。出生於十六世紀一個貴族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學與數學訓練,從普堤耶大學畢業後不久即按照父親的建議,選擇以律師為業。但不久後即至荷蘭從軍,並定居長達二十多年之久,在這其中發表了多本著作。一六五○年受瑞典女王之邀至斯德哥爾摩為其講課,卻不幸染上肺炎而去逝,享年五十五歲。重要著作有《沉思錄》、《笛卡兒談談方法》、《哲學原理》、《幾何原理》等。
譯者簡介
周春塘
美國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歷任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華梵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華梵大學東方思想研究所所長等職。著作包括《撰寫論文的第一本書》、《生活智慧 - 尋找生命中的力量》;譯有《耶穌秘卷》、《笛卡兒與沉思錄》。(以上皆由五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