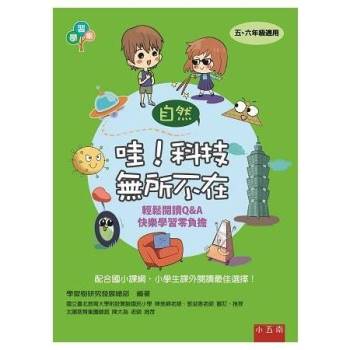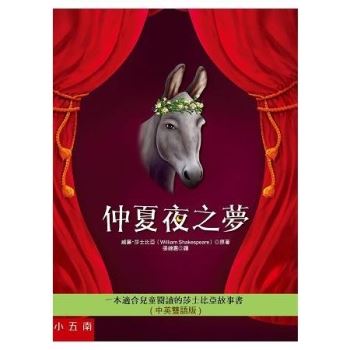本書研究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狀態,以「後現代」命名之。它指的是經歷了各種變化的文化處境,這些變化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影響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遊戲規則。在這裡,我們將通過與敘事危機的比較來定位這些變化。
科學在起源時便與敘事發生衝突。用科學自身的標準衡量,大部分敘事其實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學不想淪落到僅僅陳述實用規律的地步,只要它還尋求真理,它就必須使自己的遊戲規則合法化。於是它製造出關於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論述,這種論述就被叫作哲學。當這種後設論述明確地求助於諸如精神辯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主體或勞動主體的解放、財富的增長等某個大敘事時,我們使用「現代」一詞指稱這種依靠大敘事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學。
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把對後設敘事的不輕易相信看作是「後現代」。後現代知識並不僅僅是權力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增強我們對不可共量的承受力。它的根據不在專家的異質同構中,而在發明家的平行建構中。
李歐塔,「後現代主義之父」的法國思想家
本書為研究後現代社會與後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後現代理論」的領導者。出生於凡爾賽,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學畢業後,1950-1952年於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高中擔任哲學教師。1954年擔任社會主義期刊《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阿爾及利亞分支成員。1960年代回到法國後任教於巴黎大學、南特大學。1964年成為《工權》(Pouvoir ouvrier)的編輯委員,1966年離開。1968年參與法國的「五月風暴」學運。1970年轉至巴黎第八大學,至1987年皆為榮譽教授。接下來20年於世界各地講學,包括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霍普金斯大學、耶魯大學、加拿大的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巴西的聖保羅大學等。1998年4月21日,因癌症病逝於巴黎。
1979年,他接受加拿大魁北克政府大學教育委員會主席之邀,完成了當代文化和知識變化的研究報告書《後現代狀態》。其他著作有:《現象學》(1954)、《論述.圖像》(1971)、《力比多經濟》(1974)、《正義遊戲》(1979)、《衍異:論爭中的言辭》(1983)、《非人:時間漫談》(1988)、《海德格爾與猶太人》(1988)、《壯美分析的課題》(1991)等。
譯者簡介:
車槿山,法國圖盧茲第二大學文學博士,巴黎第八大學完成文學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場域:資訊化社會中的知識
我們的工作假設是:隨著社會進入被稱為後工業的年代以及文化進入被稱為後現代的年代,知識改變了地位【1】。這種過渡至少從五○年代末就開始了,對歐洲來說這標誌著重建的結束。各個國家的過渡有快有慢,各個活動部門的過渡也有快有慢:因此很難寫出完整的編年史,很難畫出總表【2】。一部分描述只可能是臆測的。但我們知道,過分信任未來學是不謹慎的【3】。
與其制定一張不可能完整的圖表,我們不如從一個特徵出發,它能立即決定我們的研究對象。科學知識是一種論述。我們可以說,四十年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4】、溝通問題與控制論(cybernétique)【5】、現代代數與資訊學【6】、電腦與其語言【7】、語言翻譯問題與語言-機器兼容性研究【8】、存儲問題與數據庫【9】、遠端傳訊與「智能」終端的建立【10】,吊詭邏輯(paradoxologie)【11】:以上是明顯的證據,這還不是完整的清單。
這些科技變化對知識產生的影響應是巨大的。受到影響或即將受到影響的是知識的兩個主要功能:研究與認知的傳遞。關於第一個功能,遺傳學提供了外行也能明白的一個例子:它的理論派典(paradigme)來自控制論。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關於第二個功能,我們知道,由於各種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可獲取性處理、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經發生了變化【12】。我們有理由認為,資訊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並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後來音像流通方式(媒體)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13】。
在這種普遍的變化中,知識的性質不會依然如故。知識只有被轉譯為資訊量【14】才能進入新的渠道,成為可操作的。因此我們可以預料,一切被構成的知識,如果不能這樣轉譯,就會遭到遺棄,新的研究方向將服從潛在成果轉變為機器語言所需的可轉譯性條件。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知識的「生產者」和使用者都必須具備把他們試圖發明或試圖學習的東西轉譯到這些語言中去的手段。關於翻譯器的研究已經取得很大進展【15】。隨著資訊科技的霸權,某種邏輯佔了上風,由此生出一整套規範,它們涉及的是那些被人當作「知識」而接受的陳述。
從此我們可以見到明顯的知識外在化,這是相對於「知者」而言的,不論他處在認識過程的哪一點上。以前那種知識的獲取與精神、甚至與個人本身的形成(「教養」(Bildung))密不可分的原則已經過時,而且將更加過時。知識的供應者和使用者與知識的關係,越來越具有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與商品的關係所具有的形式,即價值形式。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值而被消費:它在這兩種情形中都是為了交換。它不再以自身為目的,它喪失其「使用價值」【16】。
我們知道,在最近幾十年中,知識成為首要生產力【17】,這已經顯著地改變了最為發展國家的就業人口構成【18】,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最主要的薄弱環節。在後工業和後現代時期,科學將繼續保持並且可能加強它在民族國家生產能力方面的重要性。由於這種形勢,我們有理由認為,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還會不斷增大【19】。
但這個方面不應該讓人忘記與此互補的另一個方面。在知識對生產力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資訊商品形式下,它在世界權力競爭中已經是、並且將繼續是一筆巨大的爭奪焦點,也許是最重要的爭奪焦點。因為民族國家曾經為了控制領土而開戰,後來又為了控制原料和廉價勞動力而開戰,所以可以想像它們在將來會為了控制資訊而開戰。這樣就為工業和商業戰略,為軍事和政治戰略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20】。
不過,這裡引出的觀點並不像我們剛才說的那麼簡單,因為知識的商品化不可能不觸動現代民族國家在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方面過去及現在仍掌握的特權。知識從屬於社會的「頭腦」或「才智」,即從屬於國家,這種思想將隨著與此相反的另一種原則的鞏固而過時;按照這種相反的原則,只有當社會中流通的資訊十分豐富而且易於解讀時,社會才能生存並進步。一種「溝通透明性」的意識形態與知識的商業化一同出現,對這種意識形態而言,國家開始成為不透明性和「噪音」的製造者。從這個角度看,經濟機構和國家機構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出現新的尖銳問題。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由於那些被統稱為跨國企業的資本流通新形式,經濟機構已經使國家機構的穩定性陷入危險境地。這些資本流通新形式意味著,有關投資的決定至少部分地擺脫了民族國家的控制【21】。隨著資訊技術和遠端傳訊(télématique)技術的發展,這一問題可能會變得更為棘手。例如,假定一個類似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企業得到允許,占用一條地球軌道場來放置通訊衛星和/或資料庫衛星。誰將有權使用它們?誰將規定禁止使用的波道或資料?是國家嗎?或者國家只是許多用戶中的一個?這樣就出現了新的法律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帶來了如下的問題:誰將擁有知識?
因此,知識性質的改變將對執政當局產生一種反作用,迫使當局重新考慮自己在法律上和在事實上與大企業、更一般地說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世界市場的重新開放、非常激烈的經濟競爭的重新開始、美國資本主義排他性霸權的消失、社會主義選項的沒落,中國貿易市場很可能的開放,這一切以及其它許多因素已經在這個七○年代末出現,促使國家認真重新檢視自己從三○年代以來通常所起的作用,即保護與指導,甚至是計畫投資【22】。在這一脈絡中,各種新科技只可能增強檢討的緊迫性,因為它們使那些用於決策的資料(即控制手段)變得更流動,更容易被竊取。
我們可以想像,知識不是根據自身的「養成」價值或政治(行政、外交、軍事)重要性得到傳播,而是被投入與貨幣相同的流通網絡;關於知識的確切劃分不再是「有知識」和「無知識」,而是像貨幣一樣成為「用於支付的知識」和「用於投資的知識」,即一方面是為了維持日常生活(勞動力的恢復,「存活」)而交換的知識,另一方面是為了優化程序產出而的知識信貸。
在這種情況下,透明性和自由主義是相同的。自由主義並不妨礙在金錢的流通中,一些錢用來決策,而另一些錢只適合用來還債。我們同樣可以想像知識的流通使用性質相同的渠道,但其中的一些知識是為「決策者」保留的,而另一些知識則用來償還每人在社會關係方面不斷欠下的債務。
註釋
【1】圖雷納(A. Touraine):《後工業社會》(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德諾埃爾出版社,一九六九年;貝爾(D. Bell):《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紐約,一九七三年;哈桑(I. Hassan):《俄耳甫斯的解體──邁向後現代文學》(The Dismemberment of Orpheus: Toward a Post Modern Literature),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貝納姆(M. Benamou)和卡拉梅洛(Ch. Caramello)編《後現代文化的表現》(Performance in Postmodern Culture),威斯康星,二十世紀研究中心出版社,一九七七年;柯勒(M. K[‥o]hler):《後現代主義──概念史的考察》(Postmondernismus: Ein begriffgeschichtlicher Ueberblick),載《美國研究》(Amerikastudien)第二十二期,一九七七年。
【2】比托爾(M. Butor)發表過與此有關的文學作品,它已成為經典:《運動物體──展現美國的習作》(Mobile. Etude pour une représentation des Etats-Unis),伽利瑪出版社,一九六二年。
【3】福爾斯(J. Fowles)編《未來研究手冊》(Handbook of Futures Research),韋斯特波特(康乃狄克州),格林伍德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4】特魯別茨何依(N. Troubetzkoy):《音位學原理》(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收入《布拉格語言學學派作品集》(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第七卷,布拉格,一九三九年。
【5】維納(N. Wiener):《控制論與社會》(Cyberbetics and Society),波士頓,霍頓.米弗林出版社,一九四九年;阿什貝(W. Ashby):《控制論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Cyberbetics),倫敦,查普曼-霍爾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6】參見諾伊曼(Johannes. von Neumann, 1903-1957)的著作。
【7】貝萊爾(S. Bellert):《控制論系統的形式化》(La Formalisation des systèmes cybernétiques),收入《當代科學中的資訊觀念》(Le Concept d’information dans la science contemporaine),子夜出版社,一九六五年。
【8】穆南(G. Mounin):《翻譯的理論問題》(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伽利瑪出版社;一九六三年。計算機革命始於一九六五年,那時出現了新一代的360 I.B.M.計算機,參見莫克(R. Moch)著《資訊學轉向》(Le Tournant informatique),收入諾拉(P. Nora)和曼克(A. Minc)編《社會的資訊化》(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附錄四《貢獻性文件》(Documents contributifs),法國文獻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阿什貝:《第二代微電子技術》(La Second Génération de la micro-électronique),載《研究》(La Recherche)第二期,一九七○年六月,第一二七頁以下。
【9】戈德費爾南(C. Gaudfernan)和塔伊布(A. Taib):《術語匯編》(Glossaire),收入《社會的資訊化》(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貝卡(R. Beca):《資料庫》(Les Banques de données),收入《社會的資訊化》(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附錄一〈新資訊學和新增長〉(Nouvelle informatique et nouvelle croissance))。
【10】儒瓦耶(L. Joyeux):《資訊學先進技術》(Les Applications Avancées de l’informatique),收入《貢獻性文件》(Documents contributifs)。家庭終端將在一九八四年前商業化,價格約為一千四百美元,參見國際資源發展報告《家庭終端》(The home terminals),康乃狄克州國際資源發展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11】瓦茨拉維克(P. Watzlawick)、赫爾米克-比文(J. Helmiek-Beavin)和傑克遜(D. Jackson):《人類交流語用學──對相互影響的模式、病理及悖論的研究》(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紐約,一九六七年。
【12】經濟及科技系統分析展望小組的特雷佛(J. Treille)宣稱:「我們沒有多談存儲擴散的可能性,尤其是通過半導體和激光(……),不久每人都能在他需要的地方廉價地存儲資訊,而且還將擁有獨立處力的能力」(《傳媒周報》(La Semaine media)第十六期,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根據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查,半數以上的中學生經常使用計算機,八○年代初每個學校都將擁有一台計算機《傳媒周報》(La Semaine media)第十三期,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13】布律內爾(L. Brunel):《機器與人》(Des Machines et des hommes);蒙特婁,魁北克科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米西卡(J. Missika)和沃爾頓(D. Wolton):《思維網絡》(Les réseaux pensants),技術資料書局,一九七八年。魁北克與法國之間的圖像會議正在變成一種習慣:一九七八年十一至十二月,魁北克和蒙特婁為一方,巴黎(北巴黎大學和龐畢度中心)為另一方,召開了第四輪直接圖像會議(由「交響號」衛星傳送)。電子新聞是又一個例子:美國三大新聞網ABC、NBC和CBS在全世界大量增加了製作室,幾乎所有突發事件現在都可以進行電子處理,並通過衛星傳回美國。只有設在莫斯科的辦事處仍用膠片工作,工作人員先把膠片寄到法蘭克福,然後再由衛星傳送。倫敦已經成為大「集散地」(《傳媒周報》(La Semaine media)第二十期,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14】資訊單位是彼持,其定義可參見戈德費爾南和塔佛布的《術語匯編》(Glossaire)。有關此問題的討論可以參見湯姆(R. Thom)的《語義學的影響之一──資訊》(Un protée de la sémantique: l’information),收入《形態發生的數學模式》(Modèles mathématique de la morphogenése),10/18叢書,一九七四年。資訊轉換成數位符碼主要是為了避免歧義,參見瓦茨拉維克等人著《人類交流語用學》(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15】克雷格公司和萊克森公司宣布向市場投放微型翻譯器,它由四個不同語言的組件構成。每個可存一千五百詞。韋德納通訊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一種「多語詞彙處理器」,它可將一個普通翻譯器的能力從每小時六百詞提高到兩千四百詞,它有三個存儲器:雙語詞典、同義詞典和語法索引(《傳媒周報》(La Semaine media)第六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
【16】哈伯馬斯(J. Habemas):《知識與興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法蘭克福,一九六八年。
【17】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1857-1858)中寫道:「在人類作為社會團體存在時,生產和財富的基礎(……)成為智慧,成為對自然的統治」,以至「普遍的社會知識成為直接的生產力」。不過,馬克思承認,知識並不是「在形式中,而是像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一樣」成為生產力,即像機器一樣成為生產力:機器是「大腦的器官,是人類的雙手用客觀化的知識力量鍛造出來的」。參見馬蒂克(P. Mattick)著《馬克思與凱因斯──混合經濟的極限》(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法文版),伽利瑪出版社,一九七二年。有關此問題的討論可以參見李歐塔的《異化在馬克恩主義轉折中的位置》(La place de l’aliénation dans le retournement marxiste),收入《從馬克思和佛洛伊德出發的偏航》(Dérive à partir de Marx et Freud),10/18叢書,一九七三年。
【18】美國各類勞動力的構成在二十年間(1950-1971)的變化如下(《統計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s),一九七一年):
一九五○ 一九七一
工廠、服務業和農業工人 62.5% 51.4%
自由職業與技師 7.5% 14.2%
職員 30% 34%
【19】因為「生產」一個高級技師或一個中級科學家所需時間比開採原材料和轉移貨幣資本所需時間更長。馬蒂克在六○年代末估計,不發達國家的淨投資率為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至五,發達國家為百分之十至十五(《馬克思與凱因斯》(Marx and Keynes),第二八七頁)。
【20】諾拉和曼克編《社會的資訊化》(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特別參見第一章:「挑戰」(Les défis));斯圖爾澤(Y. Stourdz[′e])的《美國與通訊戰爭》(Les Etats-Unis et la guerre des communications),載《世界報》(Le Monde),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至十五日。一九七九年電信器材的世界市場價值是三百億美元,人們估計十年後將達到六百八十億美元(《傳媒周報》(La Semaine media)第十九期,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21】孔布雷(F. de Combret):《工業的重組》(Le redéploiement industriel),載《世界報》(Le Monde),一九七八年四月;勒帕日(H. Lepage):《明天的資本主義》(Demain le capitalisme),巴黎,一九七八年;科塔(A. Cotta):《法國與世界的迫切需要》(La France et l’impératif mondial),法國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22】這裡指的是「削弱行政管理」,達到「最低限度國家」。「福利國家」的沒落是伴隨著一九七四年開始的「危機」發生的。
第一章 場域:資訊化社會中的知識
我們的工作假設是:隨著社會進入被稱為後工業的年代以及文化進入被稱為後現代的年代,知識改變了地位【1】。這種過渡至少從五○年代末就開始了,對歐洲來說這標誌著重建的結束。各個國家的過渡有快有慢,各個活動部門的過渡也有快有慢:因此很難寫出完整的編年史,很難畫出總表【2】。一部分描述只可能是臆測的。但我們知道,過分信任未來學是不謹慎的【3】。
與其制定一張不可能完整的圖表,我們不如從一個特徵出發,它能立即決定我們的研究對象。科學知識是一種論述。我們可以說,四十年來的...
作者序
導論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狀態。我們決定用「後現代」命名這種狀態。這個詞正在美洲大陸的社會學家和批評家的筆下流行,它指的是經歷了各種變化的文化處境,這些變化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影響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遊戲規則了。在這裡,我們將通過它們和與敘事危機的關係來定位這些變化。
科學在起源時便與敘事發生衝突。用科學自身的標準衡量,大部分敘事其實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學不想淪落到僅僅陳述實用規律的地步,只要它還尋求真理,它就必須使自己的遊戲規則合法化。於是它製造出關於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論述,這種論述就被叫作哲學。當這種後設論述明確地求助於諸如精神辯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主體或勞動主體的解放、財富的增長等某個大敘事時,我們使用「現代」一詞指稱這種依靠大敘事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學。例如,如它進入了理性精神間可能形成一致意見的視野中,具有真理價值的陳述在發話者和受話者之間建立共識這一規則便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是啟蒙敘事,在這一敘事中,知識英雄為了一個高尚的倫理-政治目的而工作,即普遍的和平。我們可以通過此一個案看出,用一個包含歷史哲學的後設敘事來使知識合法化,這將使我們對支配社會關係的體制是否具備有效性產生疑問:這些體制也需要使自身合法化。因此正義同真理一樣,也依靠大敘事。
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把對後設敘事的不輕易相信看作是「後現代」。不輕信無疑是科學進步的結果,但這種進步也以不輕信為前提。與以後設敘述進行合法化的配置的衰落相對應的,明顯是形上哲學和依賴於於形上哲學的大學體制所出現的危機。敘述功能失去了自己的功能作用元:偉大的英雄、偉大的風險、偉大的曲折過程以及偉大的目標。它分解為敘述性語言元素的雲團,但其中也有直指性語言元素、規範性語言元素、描寫性語言元素等,每個雲團都帶著自己獨特的語用學價值項。我們大家都生活在許多語用學價值項的交叉路口。我們並不一定構成穩定的語言組合,而且我們構成的語言組合也並不一定具有可溝通的性質。
因此,正在到來的社會基本上不屬於牛頓的人類學(如結構主義或系統理論),它更屬於語言粒子的語用學。語言遊戲有許多不同的種類,這便是元素的異質性。語言遊戲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體制,這便是局部決定論。
然而,決策者嘗試採用一種輸入輸出模式,按照一種包含元素可共量性和全體可決定性的邏輯來管理這些社會性雲團。由於他們,我們的生活註定要獻給力量的增長。不論在社會正義問題上,還是在科學真理問題上,權力的合法化都是優化系統產出,即優化效率。在我們的全部遊戲中實施這一標準將帶來某種或軟或硬的恐怖:你們應該成為有操作性的,也就是可共量的,否則就消失吧。
這種最佳產出邏輯大概在許多方面都不一致,尤其是造成了社會經濟領域的矛盾:它既希望勞動更少(以便降低生產成本),又希望勞動更多(以使減輕社會對非勞動人口的負擔)。但不輕信從此已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我們不能再像馬克思一樣指望由這些矛盾中出現一條拯救之路。
不過後現代狀態與幻滅無關,也與去合法化的盲目實證性無關。在後設敘事之後,合法性可能存在於什麼地方呢?操作性標準是科技性的,它不適宜用來判斷真理和正義。合法性是否像哈伯馬斯(J. Habermas)設想的那樣存在於通過討論而達成的共識中呢?這種共識違背了語言遊戲的異質性。發明總是產生在分歧中。後現代知識並不僅僅是權力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增強我們對不可共量的承受力。它的根據不在專家的異質同構(homologie)中,而在發明家的平行建構(paralogie)中。
這裡展開的問題是:一個社會關係的合法化,一個公正的社會,是否可能依照一種類似科學活動的吊詭(paradoxe)來實現?而這種吊詭又是什麼?
下面的文本是應時之作。它是應魁北克省政府大學委員會主席的要求而提交給該委員會一份有關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的報告。主席還友好地允許這份報告在法國出版:他應受感謝。
所餘要說的是報告撰寫人是哲學家,不是專家。後者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而前者卻不同。一個人是在總結,另一個人是在發問,這是兩種語言遊戲。它們在這裡被混淆了,結果都進行得不好。
哲學家至少可以自我安慰地設想,在他之後,人們會對哲學和倫理-政治學的某些合法化論述作出形式及語用學分析,這種分析也是此報告的基礎。他已經用有點帶有社會學色彩的角度引入此一分析,這使它變得簡短,但也使它獲得定位。
總之,我們將此報告題獻給巴黎第八大學(樊尚大學)哲學綜合科技學院(l’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hilosophie),在這個非常後現代的時刻,這所大學有可能消失,而這所學院則有可能誕生。
導論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狀態。我們決定用「後現代」命名這種狀態。這個詞正在美洲大陸的社會學家和批評家的筆下流行,它指的是經歷了各種變化的文化處境,這些變化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影響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遊戲規則了。在這裡,我們將通過它們和與敘事危機的關係來定位這些變化。
科學在起源時便與敘事發生衝突。用科學自身的標準衡量,大部分敘事其實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學不想淪落到僅僅陳述實用規律的地步,只要它還尋求真理,它就必須使自己的遊戲規則合法化。於是它製造出關於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論述...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場域:資訊化社會中的知識
第二章 問題:合法化
第三章 方法:語言遊戲
第四章 社會關係的性質:現代的另一選項
第五章 社會關係的性質:後現代的視野
第六章 敘述知識的語用學
第七章 科學知識的語用學
第八章 敘述功能與知識合法化
第九章 知識合法化的敘事
第十章 去合法化
第十一章 研究與通過產出能力達到的合法化
第十二章 教學與通過產出能力達到的合法化
第十三章 研究不穩定性的後現代科學
第十四章 以平行建構進行的合法化
導論
第一章 場域:資訊化社會中的知識
第二章 問題:合法化
第三章 方法:語言遊戲
第四章 社會關係的性質:現代的另一選項
第五章 社會關係的性質:後現代的視野
第六章 敘述知識的語用學
第七章 科學知識的語用學
第八章 敘述功能與知識合法化
第九章 知識合法化的敘事
第十章 去合法化
第十一章 研究與通過產出能力達到的合法化
第十二章 教學與通過產出能力達到的合法化
第十三章 研究不穩定性的後現代科學
第十四章 以平行建構進行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