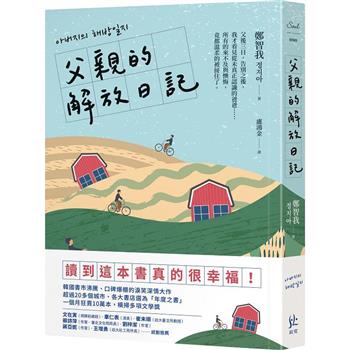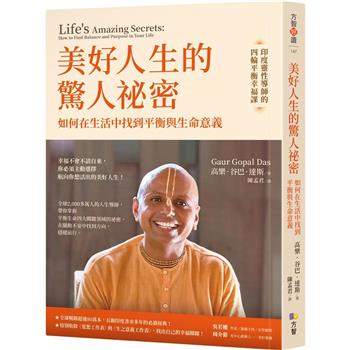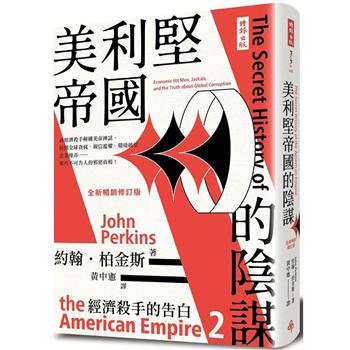中譯修訂版序
本書初版在二○○三年問世,題為「李維羅馬史疏義」。八年來,我對馬基維利有更深入的理解,對翻譯也有更深刻的體會。我領悟到馬基維利是以隨興的筆調闡述他閱讀李維《羅馬史》油然而生的思古幽情,我有信心提高馬基維利的政治哲學思想對於中文讀者的親和力。這一番領悟與信心促使我決定推出修訂版,不只是標題更改,連內文也大刀闊斧修訂。
馬基維利的標題,直譯作「論提圖斯.李維的前十卷」,是馬基維利閱讀李維《羅馬史》開頭十卷的心得,結合他個人在佛羅倫斯的從政經驗和對於義大利當代歷史的觀察,從中歸納出政治哲學的理念。
提到「哲學」難免令人望而生畏,套在馬基維利身上其實不然。傳統所定義的哲學家是以縝密的推理營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藉全面的觀點嘗試為人生或知識的根本問題解惑。以「全面的觀點」探討「根本的問題」,這樣的特性使得哲學家所要解決的疑惑超越具體的經驗、特定的現象與技術的層面,因此在一般人看來往往顯得不切實際或大而無當。此一「哲學家印象」根本不適用於馬基維利,因為他的務實性格處處以具體的經驗和特定的現象為念,念茲在茲的是如何把解惑之道落實在技術的層面。
馬基維利雖然講求實用原則,雖然不曾為自己的政治理念建構一套有系統的理論,卻心繫哲學家的關懷。他的關懷,一言以蔽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處身在政治的洪流,有何安身立命之道?他主張共和體制優於君主統治,以具體的事例闡明「政治權威來自人民的同意」這個原則。他舉證或引述的事例有古代的,也有當代的,李維的《羅馬史》為這些事例提供了一個串連古今歷史、觀照人類政治情境的平台。
李維及其《羅馬史》
李維,全名提圖斯.李維烏斯(Titus Livius,公元前五九到公元後一七),英文省略拉丁文的陽性字尾(-us)成為Livy,故稱「李維」。他是屋大維的外甥孫,卻只比屋大維(公元前六三到公元前十四)年輕四歲。他出生的城市帕塔維翁(現在的帕度亞)是當時義大利半島僅次於羅馬的富庶大城。他十五歲那一年,凱撒被暗殺,羅馬陷入內戰。屋大維統一分裂的羅馬之後,於公元前二七年由元老院授與「奧古斯都」的稱號,大權定於一尊,羅馬的共和體制淪為有名無實,羅馬帝國正式誕生。差不多就在羅馬政體由共和國轉為帝國的那幾年間,李維離開故鄉來到羅馬城,在那裡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完成名山之作《羅馬史》,直到奧古斯都去世才回歸故里。
《羅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直譯「建城以來」,從羅馬建城(傳統上訂為公元前七五三),經共和制取代王制,一路寫到公元前九年,此時帝制肇建已經十八年。李維本人目睹羅馬在屋大維的領導下從內戰的廢墟浴火重生的歲月,又在奧古斯都的身影下從事歷史著述,下筆處處強調羅馬的豐功偉業。在羅馬的歷史學家當中,唯獨李維沒有從政的經驗,因此得以展現獨樹一幟的歷史觀:他從人格和道德的觀點看待歷史的進程,徹底揚棄從政治觀點解讀歷史的傳統。一如維吉爾的《埃涅伊德》,以史詩的體裁描寫羅馬帝國的英雄情操與民族精神,李維以歷史的體裁歌頌歷代羅馬名人的事蹟。這樣一位為羅馬黃金盛世代言的歷史學家,可以恰如其分稱為「史學的維吉爾」,兩人異曲同工在萬象更新的歷史情境中奮勉追尋新時代的英雄典範。對維吉爾和李維來說,那樣的典範就具現在奧古斯都身上。李維在《羅馬史》自序寫道:「即使我的名聲在史家群像中湮沒無聞,擋我光環的名人偉業也可以使我沾光」。他描寫典型在夙昔的古人古事,自己化身為古人心的同時,也在奧古斯都身上看到想像中的楷模。
《羅馬史》總共一四二卷,分十二包(羊皮紙卷的包裝術語,相當於現在套書的分冊)。開頭五卷合為第一包,在公元前二十七年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後續的部分無不是在「應讀者要求」聲中源源問世。一直到古典時期結束,李維的盛名始終不衰。可是在中古時期,他的聲望走下坡,加上這一套書卷帙浩繁,抄寫、閱讀與保存無不是挑戰。可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羅馬史》逐漸散失。到了尚古成風的文藝復興時期,李維再度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素有「文藝復興之父」之美譽的佩脫拉克就是積極搜尋散失抄稿的主要人物。儘管如此,我們現在還能讀到的《羅馬史》只約為原作的四分之一。
在文藝復興火車佩脫拉克(一三○四到一三七四)去世之後九十五年,馬基維利從政治實務的觀點疏陳《羅馬史》的義理,寫出《論李維羅馬史》,這一番評述更是把李維的名望推到另一個高峰。馬基維利本人則承襲李維「史以載道」的觀點而成為古典共和主義的終結者,同時卻憑其現實主義論述而成為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源頭。
馬基維利
一四六九年五月三日,馬基維利出生於佛羅倫斯望族中貧寒的一支。他的父親是律師,他自己在佛羅倫斯大學接受正統的學術訓練,修習科目包括邏輯、數學、音樂、天文學與哲學等人文學科。二十八歲(一四九八)步入政壇,被任命為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國務秘書,積極與聞國防與外交事宜,先後出使法國和德意志,還在佛羅倫斯推動國防改革,以民軍取代雇傭兵。他四十二歲(一五一二)那一年,於一四九四被法國推翻的麥迪奇家族在西班牙扶植下重返佛羅倫斯執政,共和派失勢,馬基維利被麥迪奇家族的羅倫佐解除公職,又因涉及反麥迪奇家族的陰謀而在一年後被捕,獄中慘遭逼供,獲釋後退隱城外祖傳的一塊小地產,著述度日。一五一九年,他和麥迪奇家族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重出政壇。一五二七年,麥迪奇家族遭罷黜,馬基維利嘗試在重新建立的共和政府謀得一官半職,卻因為與舊政權的關係而無法贏得信任。他在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五十八歲)逝世,葬於故鄉的聖十字教堂,與米開朗基羅和伽利略等一代宗師為鄰,墓碑刻了一句拉丁文:“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頌詞無以匹配如此盛名)。
馬基維利雖然也是詩人,又是劇作家,他的墓誌銘所稱的「盛名」其實是指他身為現代政治學的奠基人。他生逢時局板蕩,義大利半島上城邦傾軋無已,又有教皇對於發動戰爭比對於推廣教義更有興趣,權力起伏無常。內亂引來外患,西班牙、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固然垂涎覬覦,甚至連瑞士也想分一杯羹。政治軍事聯盟有如走馬燈,傭兵首領換東家是家常便飯,政權甚至比人生還短命。馬基維利的親身經歷反映那樣的時局,他的從政與歸隱恰是時代變局的縮影。慶幸的是,他失意政壇卻造就學術成功的機緣。
使馬基維利名垂青史的學術著作有四部。歸隱田園之後一年完成的《君王論》(一五一三)是獻給麥迪奇家族,寄望重返政壇卻落了空。失望之餘,他在六年後完成的《論李維羅馬史》(一五一九)寫道:這一次「選擇獻書的對象不是君主之輩,而是具備君主才德的出類拔萃之士;不是可以授我官階、榮譽與財富之輩,而是力不能及卻心有餘之士。」接著《戰爭的藝術》(或譯作《兵法》,一五二○)是他研究歷史上著名戰役的心得,並結合自己擔任軍事指揮觀的第一手經驗。他的最後一部著作《佛羅倫斯史》(一五二五)是一五二一到二五年間,獲麥迪奇家族任命為史官,奉命編修佛羅倫斯共和國歷史的成果。這四部著作使得馬基維利成為文藝復興文明一座醒目的標竿。
正如十六世紀歐洲的知識分子以魔鬼撒旦的俗名「老滑頭」(Old Nick)為他取綽號,他在世就被看作是不道德而且欺詐成性;即使在今天,“Machiavellian”(「馬基維利作風」)這個字的用法仍不脫在政治場域逐權奪位、機心巧詐、寡廉鮮恥之類的意涵。多虧個人的歷史素養與政壇閱歷,他有機會站上「識古鑑今」這個正席捲歐洲文藝復興風潮的浪頭。他在現實世界目睹赤裸裸的官場與政壇現形記,在書壁學海中遙想古道照顏色的夙昔典範。羅馬的榮耀仍有餘暉殘存,能否啟迪深陷於無邊黑暗而前途茫茫的義大利?他在提圖斯.李維的《羅馬史》看出一條「沒有人踩過的新途徑」,他「相信將會對每一個人帶來共同利益」,慧心所得發而為文就是《論李維羅馬史》。一本書為相隔一千五百年的兩個世界提供交流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我們欣然看到廢墟中飛揚著共和主義的神采。
共和主義是以共和國政體治理國家的一套意識形態,政體的首腦則是經由繼承以外的方式產生,通常透過選舉。共和主義的實質內涵因時因地而異,其中一種是文藝復興時期受政府形態與古典作家的啟迪而發展出來,特稱為古典共和主義,第一手資料就是由馬基維利在《論李維羅馬史》所提供。至於現代性,其核心命題為人的主體性。所謂「人的主體性」,借用馬基維利的措詞來表達可以說是發揚政治人的「德性」以克服機運之「無常」,這可能是他透過李維的歷史觀緬懷古代的自由慧心所得最可貴的體悟。大而化之歸納他在書中的論點,可以這麼說:只有在自由的基礎上才可能建立強大的國家。這裡的「自由」指的是公民自治。但是,唯有公民具備德性,國家才能確保自由,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改變機運,主動創造自己的命運。
馬基維利與文藝復興
十二世紀中葉,義大利北部出現嶄新的社會形態和政治組織,和當時蔚成歐洲主流的封建制度大相逕庭。到了一三○○年,義大利中部和北部人口超過二萬八千的城市多達二十三個。這些城市享受到高度的自治,有的甚至轉變成獨立的共和國,政體形態類似上古時代的城邦。佛羅倫斯就是那樣的一個城邦共和國。
馬基維利在佛羅倫斯出生的時候,佩脫拉克已經過世將近一個世紀。下面幾件大事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的文化氛圍。佩脫拉克在一三三七發表《論名人》,書中完全忽略中古時代的聖徒和殉道者,卻從上古時代非基督教的英雄找實例。四年後他在羅馬受封為「桂冠詩人」,隨後在維洛納校勘李維的《羅馬史》。一四五二年,馬奈蒂(Giannozzo Manetti)發表《論人的尊嚴與優越》,表明他相信人具有「無可限量的尊嚴和優越」。接著古騰堡在一四五五以活字版印刷《聖經》。最後,馬基維利出生的那一年,達文西抵達佛羅倫斯,在這個文藝復興之都透過藝術家的眼光多方面落實「人是宇宙的中心」這個抽象的觀念。
文藝復興是一場重生。由佩脫拉克在義大利領軍的這一場運動,以人文主義廣為人知,因為它專注的是人文研究,研究重點在於「人文學科」,而不是物理學、形上學或神學。在馬基維利那個時代,物理學、形上學與神學是唾手可得的文化遺產,但是馬基維利幾乎全面拒絕,獨力抗拒他的時代。雖然重生的觀念本身暗示對於當時通行的方法感到不滿,馬基維利對於他所見到如火如荼的文藝復興尤其不滿。在《論李維羅馬史》的開頭,他抱怨他那個時代的人,購買古代雕像的殘片擺在家中,拿來模仿,以此沾沾自喜,卻不知模仿政治上的「古德」。他感慨古德一去不返,認定有必要復古,因為他們比現代人優越,可是對於在他有生之年,甚至就在他自己的城市佛羅倫斯當著他的眼前所創造出來的藝術精品,他卻看不上眼,反倒呼籲大家師法古人的行為。他也分享了人文主義者推崇羅馬的風氣,竟至於喜歡羅馬甚於喜歡希臘。古德主要在羅馬人身上發現,特別是在羅馬歷史學家李維的《羅馬史》,書中主體就是記載共和時期羅馬人的行為。
「共和」是與君主制相對的政體。《君王論》開宗明義就斷言統治人類的政府不外共和制與君主制這兩種政體。共和國是擁有自由的公民基於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維持其生活方式的政治共同體,此一理念自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以來,始終緊扣歐洲知識份子的想像,源遠流長蔚為烏托邦傳統。馬基維利無法忘情於那樣的想像與那一個傳統,與眾不同的是,他的「理想」既不在虛無飄渺的仙境樂園,也不在與世隔絕的海外荒陬,而是在腳踏實地的塵世社會。令人難以思議的是,一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烏何有」的傳統依然是歐洲政治哲學的主流!
猶如西塞羅(公元前一○六到四三)稱美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人間,馬基維利就是把政治哲學從烏托邦帶到人世間的開宗祖師。烏托邦政治關心的是政府應該如何運作,馬基維利則是第一個關注政府在實際上如阿運作的政治學家。我們常說政治如何如何的現實,現實就是實際,我們不自覺承襲了馬基維利的現實主義觀點。不論喜歡或不喜歡,任誰也無法否認「國家」是父權社會出現以來最巧奪天工的發明,說它是一件既繁複又精細的藝術品並不為過——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明》論「國家即藝術作品」,就是以馬基維利界定那個時期的政治。義大利文藝復興在政治領域的建樹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政體即藝術作品。馬基維利正是政體藝術理論的創始人。
馬基維利的《佛羅倫斯史》又進一步展現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思想。麥迪奇家族拔擢馬基維利,本意是要他為家族歌功頌德,可是馬基維利有更高超的視野。他一改傳統編年史體裁的插曲式敘述,同時徹底揚棄中古時代視歷史發展為體現上帝意志這樣的「天意」史觀,只從形形色色的活動探求人類行為的動機,從中探討歷史發展的軌跡,把自己生於斯又死於斯的城市描寫成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歷史不再是為了實現天意而存在,而是人類有生之年在世間活動的總結,其成其敗與其功其過都可以一覽無遺。人有能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而創造生命的意義,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正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最醒目的成就。這種歷史感滲透到世俗的價值觀,用我們熟悉的措詞來說就是在實踐「人的尊嚴」。
《論李維羅馬史》則讓我們見識到「人的尊嚴」如何落實在政治領域。基督教神學觀在中古時代投下巨大的身影,籠罩整個歐洲文明,馬基維利代表政治領域揮別那個龐然身影的嶄新思維,強調共和主義的理想,特別著重於如何在實務層面促成穩定的政治秩序以避免腐敗,俾使共和體制在動盪之世得以卓然挺立。就人文主義的傳統來說,馬基維利的「佛羅倫斯公民」這個身分意味著他是共和理想的擁護者,不只是反對君主制,而且絕對效忠自由,以務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時代,這樣的信念促使馬基維利在外交和軍事領域獻身母城義無反顧。正因為對人世經驗不抱幻想,他能夠以前無古人的大膽筆法分析權力的本質,這就是馬基維利的現實主義精神——現實的觀點是文藝復興和中古時代分道揚鑣的另一個里程碑。
馬基維利生活在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存活在馬基維利;他這個人與那個時代似乎融合無間。然而,文藝復興不只是舊東西的「重生」,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現代性」的這個新東西的源頭。要不是有馬基維利,文藝復興恐怕不會有那個意思。在文藝復興蔚成風潮的新觀念偏好原則的創新,並且主張在觀念與制度上不斷推陳出新,改變為的是要接受進一步的改變。不論現代為何,總之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持續變為更現代。馬基維利在《君王論》中描繪的新君主固然如此,他在《論李維羅馬史》中陳明的「新模式與新秩序」也一樣。
馬基維利的影響遠遠超乎政治的領域。他讚美古代的功德為的是要有所改善。他的詮釋把古德轉化為功德本身,即馬基維利式功德。這個詮釋還把文藝復興從古代的重生一變而為新時代的黎明,即現代。馬基維利眼中的「現代人」簡直可以說是懦弱之輩,但是他為現代人的衰弱提供進補之道,其藥效將使現代人比古代人更強壯。「現代性」就是現代人是,或可能變得,比古代人更強壯這樣的看法——就是認為現代人能夠從對他們有利而不可逆轉的進步之道獲益。文藝復興蛻變成現代性,馬基維利有功與焉。
![論李維羅馬史[1D34]](https://img.findprice.com.tw/book/97895711633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