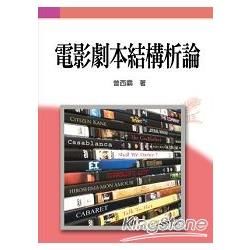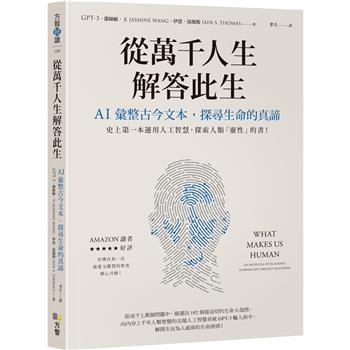本書作者從事編劇教學三十餘年,並擔任編劇的實務工作,且曾翻譯過電影編劇的專書,絕對是國內最具經驗的編劇師資之一。
希區考克曾有「說什麼故事,遠不如怎麼說故事來得重要」之名言;本書作者亦認為“Good Story Well Told”係優良電影必備之條件,且深信「結構」乃電影劇本首要關鍵,因此特地針對電影劇本結構之敘事功能∕形式∕題材的共時性與歷時性∕對立效用∕修辭策略∕改編……等面向進行析論。做為國內第一本面世的電影劇本析論之專書,相信對電影編劇技巧的提升必定有所助益。
作者簡介
曾西霸
1947年出生於台灣南投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曾任:
中國影評人協會秘書長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秘書長
金馬獎、金鐘獎、電影劇本徵選評審委員
「學者電影公司」創辦人
現任: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影劇藝術系專任教師
曾獲:
中興文藝獎之「電影評論獎」
玉山文學獎之「文學貢獻獎」
文化大學∕新竹師院傑出校友獎
代表著作:
《實用電影編劇技巧》(翻譯)
《爐主》(電影劇本)
《走入電影天地》(電影文集)
《電影時代》(電影文集)
《兒童戲劇編寫散論》(創作論述)
《親愛的野狼》(兒童劇本)
《三人行》(劇本選集)
《細說電影》(電影史)
《夢想者一號》(電影劇本)
《電影論集》(電影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