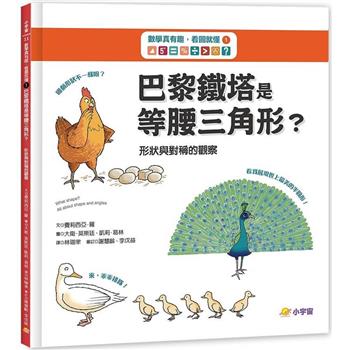第六篇 當代中國哲學
鴉片戰爭以來,清代長期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終於慘遭無法回應西方世界經過現代化歷程後挑戰中國的惡果。歐風美雨的狂風不斷侵襲疲態畢露的中國,導致中國傳統的文化遭受質疑,政治、經濟劇變,傳統價值觀念與社會秩序結構承受動搖和崩解的危機。救亡圖存的辛亥革命不但未能力挽狂瀾,且使政治分裂動盪,舊社會的價值信仰與秩序逐漸剝落,新文化的價值觀與社會秩序未能成熟建構。就國運觀之,外患不息、內憂頻仍、世風不變,浮淺之士盲目崇拜附會西方文化,對中國固有的民族哲學與文化缺乏自覺性的深刻反省和自我理解、肯認而鄙薄有加。因此,當代中國哲學可說是在殷憂啟聖的情境下,莫不在東西文化的衝突激盪下,不但憂國憂民,且更滿懷哲學與文化的深沉意識,困思竭力於對西方哲學文化客觀的理解,有價值批判的吸收,對自家傳統的哲學與文化更企求從根性上覺解、批判的繼承和汲取西學以具創造性之轉化。
歷史的際遇和命運造成一九四九年大陸與臺灣的分裂,儘管如此,兩岸中國哲學的工作者仍本著同樣的憂患意識,對中西文化的結合激盪,中國哲學文化應如何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做了不同思維途徑的努力,也締結多樣而豐富的哲學思想成果,因篇幅所限,本篇分別擇取了五位大陸學者和臺灣學者為代表性的典範,予以一一紹述。在大陸學者方面,梁漱溟是當代中國哲學中首位以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的視域,原創性地撰成名著《東西哲學及其文化》,晚年出版了涉及心理學和哲學的成熟作《人心與人生》,是當代新儒學的起步者。熊十力由唯識論切入儒學,對《周易》及儒家的心性哲學有致廣大、儘精微的原創性詮釋,構作了體大思精的當代新儒家天人之學。馮友蘭不但是首位以英美新實在論的立基點完成一部《中國哲學史》的鉅著,同時也是以新實在論詮解朱熹哲學,建構了熊十力新心學分立而自足的新理學。張岱年是首位引入西方哲學概念範疇的哲學研究法,對中國哲學進行的哲學性問題的概念範疇研究,對當代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有深厚的影響。他對儒家剛健不息、浩然之氣的精神境界,呈現出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並做了精確的闡釋。中國哲學的核心價值在追求人生真善美的崇高意義和價值,宗白華以詩化的人生、舞動的宇宙刻畫出《易》、《老》、《莊》氣韻生動的形上美學,堪謂當代中國美學之啟蒙者。
在臺灣方面,在日據時期,中國哲學未能進入大學中成為一門學科。一九四九年,一些飽學碩彥的中國哲學學者隨國民黨政府來臺,帶來了大學裡中國哲學的學科和課程。回顧這六十年來中國哲學在臺灣的立基和發展概況,可略分為二大重鎮,其一是以方東美為代表的臺大哲學系;其二是早期以臺灣師範大學人文學社,後以臺中東海大學為重鎮的當代新儒家,可以牟宗三、徐復觀及曾來臺講學的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等三位先生為臺港當代新儒家之典範人物;其三係以天主教輔仁大學在臺北復校後,以羅光總主教為代表的儒家與新士林哲學結合的中國哲學研究。本篇以這五位先哲代表為當代中國哲學臺灣方面的研究特色。
第一章 梁漱溟與熊十力
第一節 梁漱溟
一、生平與著作
梁漱溟(西元一八九三∼一九八八年)原名煥鼎,廣西桂林人,早年任教北京大學,後來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張透過鄉村建設來發展教育,革新鄉俗,改良中國社會,他與熊十力被推尊為現代新儒家的開拓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化革命時期分別公開維護孔子,肯定儒家的心性哲學。他是中國現代從事中、西、印哲學與文化之比較研究的開宗者,透過文化視域,不同文化之比較來開發其思想,與熊十力從專業領域研究哲學的進路有所不同。兩人卻有「由佛歸儒」的共同路向,但是他晚年再度皈依佛教,與熊十力引佛入儒歸宿於《易》生生的本體論不同。
梁漱溟自謂共其一生係為兩大問題而致力,先是人生問題,而後是中國哲學與文化問題。他在二十年代所發表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堪謂為代表他早期哲學觀念的主要著作。《人心與人生》完稿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一九八四年出版。這本書是他晚年頗重要的著作,是他數十年來重建儒學之最後的系統表述。全書計二十一章,自謂:「吾書旨在有助於人類之認識自己,同時蓋亦有志介紹古代東方學術於今日之知識界。」書中內容涉及心理學、人與宇宙的本體觀、倫理學及宗教思想等方面。全書歸宗於充盡人心中的理性而開顯宇宙大生命的本性,啟點天人通貫的一本關係說。我們可認定其探索人生的究竟問題才是他一生思想所關切的核心問題所在。
二、中、西、印人生哲學及其文化的比較
梁氏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從人的意欲滿足與否做研究點,提出了人對物、人對人以及人對自身生命等三大人生問題。他認為文化乃是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相應於三大人生問題,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及印度文化分別產生了三種各有特色的「生活樣法」或「文化路向」。三大人生問題中的第一大問題,是人對物的問題,亦即處理物我關係的問題。西方文化意欲向前追求,以征服自然的路向顯發了其文化特色。梁氏視這類文化是「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這種下手的結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這類文化在科學與民主上開出了其特長。他認為西方文化的兩個特長為「一個便是科學的方法,一個便是人的個性伸展,社會發達。前一個是西方學術特別精神,後一個是西方社會的特別精神。」 事實上,他所論述的西方文化係西方近四百年來具現代性的現代化文化,他對西方由希臘哲學之理性、羅馬帝國的法律及希伯來宗教所構成的西方三大精神文化結構,並無深刻的理解。人生第二大問題所處理的是人我關係,其處理方式有別於向外追求、征服的物我關係之處理,而採取向內追求、反求諸己,求得內心的和諧和自足。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生活樣法」就是這種「文化路向」。那就是「對於自己意欲變換調和持中」、「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他並不想奮鬥的改造局面,而是自己意欲的調和罷了。」人生的第三大問題是處理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亦即處理自己的身與心、靈與肉、生與死的關係。印度文化的路向顯出了其特色所在。那就是既不向外追求,也不反求諸己,而是意圖將自己從內在自我及所寄身於外在世界的存在中解脫出來,企盼達到涅槃的至上境界。
總而言之,梁氏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描繪了人類文化的發展圖式:生活樣法決定文化路向,生活樣法又由意欲決定,意欲的滿足與否產生了人生的三大問題。西方、中國及印度三大文化樣式採取了不同的思維方式,衍生了三種不同的「根本精神」。在生活樣態中,西方人較傾向於直覺運用理智的,中國人是理智運用直覺的,印度人是理智運用現量的。因而,三大文化分別採取意欲向前、自為調和持中及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他說:「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國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解脫這個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轉向後,即我們所謂第三條路向。」從佛學觀之,他所謂的「意欲」意指唯識宗所謂的「末那識」。末那識又稱分辨識,理會著眼、耳、鼻、舌、身、意等前六識的活動。對人而言的客觀世界就是這七識的活動所造成的「業」。業的體謂之「思」。整個世界沒有客觀實在性,只不過是人的意識所變現者。基於「唯識無境」,梁氏才說出「只有生活初無宇宙」的世界觀。同時,他借用叔本華的生活意志論,將意志視為一種神祕的生活力,他以求生存的欲求性來使用「意欲」一詞。因此,對他而言,意志的欲求性及意欲要求形成外部世界的傾向,形成人之生活的本然路向,那就是向前奮鬥的意欲。換言之,意欲是末那識,是人的自我意識,人之生活的本來路向係由末那識的執求性導出來的。
在西、中、印三種文化中所呈現的不同思維方式。梁氏的解釋是:西方傾向於理智,中國善於理性,印度人是理智運用現量的。在唯識宗裡,認識的對象稱為「相分」,認識的主體稱為「見分」。「相分」是由「見分」變現出來的。「現量」是「見分」對「相分」所做瞬間即逝的計量。換言之,「現量」是對感官派生的現象之直觀,雖與對象有某種對應關係,卻非對象本質之反映。「現量」之知只照印現象,瞬間即逝。他曾簡單說:「所謂現量就是感覺。」又說:「比量智即今所謂理智。」藉比量所獲致的是知識及抽象推理所得的概念化知識或「共相」。他將近代西方人的科學與民主稱為係直覺運用理性的生活。理智的概念是靜態的、呆板的,然而,中國哲學講的是變化的問題,變化是「活動的渾融的」,認識變化不總靠理智而要靠直覺。因此,中國人的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直覺式生活。
梁氏由人類生活的意欲活動方向,歸結出人生三大問題和人類三種文化形態。其三大文化路向說,針對了三大人生問題。第一大問題是人類得以生存和族類得以繁衍的基本前提,這是各民族都要面對和予以解決的。第二大問題是解決人的孤獨生活困境,旨在建構家庭、民族或國家的共同生活。第三大問題是要解脫人生中生、老、病、死的煩惱和苦痛。從三大文化路向看三大人生問題,乃是一歷時性的過程,也是一共時性的結構。雖然他對中、西、印曲折複雜的三大文化傳統之概括,有片面性及簡單化之嫌,可是他所提出的三大文化路向說,分別有所貢獻於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問題。那就是人類感情和內在生活需要的問題以及生命自身靈與肉、生與死、身與心的緊張矛盾問題。總而言之,他認為人類的發展史可謂為解決這三大問題的文化史。人生的這三大問題在他一生的文化思想中一直繞擊著他。雖然,他後來在《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著作中又提出了些新的圖式,諸如「有對」與「無對」,「從身體出發」或「從心出發」,卻皆未改變上述根本觀點,可以視為對之修改、補充和發展。他本人也自謂:「見解大致如前未變,說法稍有不同。」 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所長期醞釀的文化心理學中,已提出意涵殊異於理智的「理性」概念。
他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中國文化要義》中,首先對「理性」做了較完整的界定,且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做了內在分析。他在晚年的鉅著《人心與人生》一書中則闡發了他自成一家之言的文化心理學。他在該書的緒論中,明確的說:「說人,必於心見之;說心,必於人見之。人與心,心與人,總若離開不得。世之求認識人類者,其必當於此有所識取也。」 該書接續他一向關注和討論的三大人生問題之探討,從人類生活言人心,再從人心論究人生問題。他將前者視為心理學之研究,後者則屬人生哲學、倫理學或道德論所研究的課題。他採實然的觀點以究明人心的諸般內涵及作用,從而追究在應然的價值理想上,人生所當勉勵實踐的基礎和方向。他將人心之所涵視為一事實,人生之所當向視為一理想。理想落腳在事實上,將人生與人心相連互動,藉以昌明清明善良的人性為最高目的。
三、 從人心與人生解說「心」與「身」的概念涵義及其相互關係
梁漱溟早年雖沉浸過佛學,然而佛家的根本精神不但不契合於儒化的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也不符應時代思想與倫理建構的需求。為了符應拯救中國的悲心宏願,他決定採取一種較積極活潑的入世思想。他接受了《易經》生生之德的本體宇宙觀。他在一九二○年春,讀到《明儒學案》中泰州王門崇尚自然的思想,頗為之心動,遂「決然放棄出家之念」。此後,他信奉儒家尊德樂生的思想,開始強調自然、生命、意欲與本能等思想。他的本體論乃由唯識宗的唯心論轉於逐漸吸收儒家、陰陽家、中醫、西方的心理學、叔本華、柏克森、進化論、馬克斯思想,而醞釀成《人心與人生》的心物合一論雛形。他在該書中多處論述了身心的關係。
他在第二章〈略談人心〉一開頭就指出:「說人心,應當是總括著人類生命之全部能力活動而說。」他從人心之機體的內外兩方面言人類生命全部活動。從對外方面言,人在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有所感受和施為的能力。這一部分主要是依據大腦皮質高級神經活動,通過感覺器官系統來實現。人的生命,一切所遇皆自外來,對外應付主要靠大腦。從對內方面而言,個體生命具有賴以維持其機體不息活動的能力,大腦居最高調節中樞的地位。蓋大腦和諸內臟之間息息相聯通,以構成一完整的活體。至於何謂心?梁氏認為人心恆在發展且變化多端,殊難全部了解。然而,吾人仍可由現實生活上起作用的人心來把握其共同一貫之處。他所謂把握的人心特徵,係由心物互動處著眼,所謂:「心非一物也,其義則主宰之意也。主為主動;宰謂宰制。對物而言,則曰宰制:從自體言之,則曰主動;其實一義也。……心物其一而已矣,無可分立者。」 然而,他認為這種分析法只是一種方便。較好的說法是「自覺能動性」,至於這一概念的內涵分析,梁氏透過「主動性」、「計畫性」和「靈活性」三點來說明。其中,他認為主動性可涵括靈活性、計畫性,因而自覺能動性可簡化稱為「主動性」。
在解釋「身」、「腦」興「心」的相互關係上,梁氏渾括的說:「心以身為其物質基礎,重點突出的說,心的物質基礎又特寄乎頭腦。」「腦」雖為身體組織的一部分,「腦」與「身」原係一體。人身內外活動能相互協調聯繫近於高度渾整統一,端賴人腦的統合機能,身腦分說只是一方便性的權說。除了從身腦關係了解「身」以外,梁氏還界定了「身」概念所涵括的內容,他說:「身,指機體、機能、體質、氣質和習慣。」其中體質影響氣質、性情,而呈個別差異的表現,梁氏藉此解釋人與人之間不同的個性。換言之,「個性」係指人所秉賦的氣質有所偏而不同之謂。他承襲了宋明儒者氣質之性的影響,認為氣質凝固而有偏,障蔽了宇宙生侖本原的透顯。相對於氣質是天生的,人的生活習慣是人與環境的交往互動中所凝歛出來的,亦即是說習慣是後天養成的,與自然環境和社會風俗有密切關係。儘管氣質興習慣的形成因不同,梁氏認為兩者皆具有強大的慣性,恆掩蔽著人的主動自覺性,亦即人心的自覺性。由人心所顯露的自覺能動性,彰顯於生產和工具的製作,這是人類基本的性格。在不同時地生活的人群所感染陶鑄而形成的性格,與其體質、心智、性情仍多少有所不同,梁氏稱之為第二性格。他認為人格的這一部分透過修養和教化是可以改變的。至於論身心關係,梁氏說;「心身是矛盾統一之兩面。」身體的諸般生理需要形鑄成諸般人欲,這種來自宇宙大生命而發於個別人身的自然勢力,是「自發性發展」,有別於人心的「主動性自覺」。身心的矛盾在於身是受環境和欲望所制約而有所局限,亦即不自由的。因此,身主於受(陰),具被動的衝動性,是外在傾向的
活動,較屬膚淺的人生意義。人心主於施(陽),具主動靈活性,不願受制和局限。梁氏說:「身心的位置關係正要這樣來理會:身外而心內,心深而身淺,心位於上端,身位於下端。」身心之間的局限和自由、被動與主動、衝動與合理化,呈現了矛盾爭執的緊張性。然而身心相需相連,「心」要透過「身」而顯發作用。換言之,人腦為人心作資具而開豁出道路來。「身」容得「心」則「心」才能更方便地發揮透露出內蘊於人心的生命本性。從身心的統一性而言,心與身雖性向互異,卻一體相聯通。至於人心的內涵與特徵,梁氏別開生面的指出了理智與理性。
四、理智的特徵
梁氏認為生物的進化係按推進生活方法進行的。在空間上,植物固定一所以求生,動物則四處移動以攝食。求生動物中之節足動物依從本能生活,其生活方式由本能預設了先天安排而被制約。脊椎動物(人)趨於理智而生活。他說:「為了說明人心,必須談理智(intellect)與本能(instinct)的問題。」他認為
理智與本能為心學上的兩名詞,分別指出性質及作用方式上相異的生命活動。本能出自天然,以動物式本能為準。理智出乎意識主導人類生活。就身與腦的觀點而言,本能活動全繫於生理機能,十分靠身體;理智活動與大腦的關係較緊密而較遠於身體。
梁氏將動物的本能式生活與人類的理智生活做比較,舉出了三點不同:第一,本能式的生活所需工具即寓於身體的天然機能,人類的理智生活則可離開身體另外創作工具以為憑藉。第二,動物式的本能生活,一生下來(或於短期內)即完具生活能力,然畢生受本能所決定。人類初生時的生活本能遠不如動物,但是其生活能力隨著後天學習而遠超乎動物。第三,動物式的本能生活未脫離自然狀態,人類則不僅依恃身體的成熟,且依靠後天的學習以增進社會生活能力。他說:「一言總括:人類的生活能力、生活方式,必依重後天養成和取得,是即其依重理智之明徵。」透過理智對生活知識及技能的後天學習,人類生活可超越動物式的本能制約而獲得生命之自由。至於兩者間的相同處,則不論理智或本能,都是為解決現實生活需求而存在。所謂現實的生活需求,不外是個體生存及種族繁衍兩大問題。
就身、腦的活動而言,理智是較親近於大腦的心思作用,較不依賴身體感官對具體事物的本能反應。他說:動物是要動的,原無取乎靜也;然靜即從動中發展出來。本能急切於知後之行,即偏乎動;理智著重乎行前之知,即偏乎靜矣。理智發達云者,非有他也,即是減弱身體感官對於具體事物近乎行前之知,即偏乎靜矣。理智發達云者‧非有他也,即是減弱身體感官對於具體事物近似機械的反應作用,而擴大大腦心思作用;其性質為行動之前的猶豫審量。猶豫之中自有某種程度之冷靜在。……設若其靜也不離乎生活上一
種方法手段則亦變形之動耳。
理智是在經驗世界生活,採取行動之前,對情境中所面對的客觀事物進行理解。所謂「猶豫審量」即是「擴大大腦心思作用」。因此理智是為了正確無誤的理解客觀問題及採取有效解決問題之手段所進行的冷靜思考,梁氏以唯識宗的「比量智」來喻釋具分析推理功能的理智,且以「共相」示喻理智從事客觀認識作用時
所獲致的概念化知識。梁氏謂:「理智靜以觀物,其所得者可云『物理』。」因此,理智是從事主客對立的知識認知活動,就這一層而言涵具知解理性義。他進一步解釋說:「理解力即意識所有的概括能力,源於自覺,一切關係意義皆有待前後左右貫通(聯想)以識取,是抽象的(共相)。」當理智獲致正確的概念知識後,再運用於生活情境中,對所擬解決的問題予以分別、計算而取最有利於人的解決手段。就有效運用知識以解決現實生活運動而言,梁氏所謂的「理智」又兼具工具理性運作之意涵。他以理智的發展為西方意識向前的文化特色。他且以佛家語的「我執」與「意執」來予以註解:「蓋生命寄於向前活動,向前活動基於二執故也。(我執之末那識與意執之意識)。」換言之,理性雖趨於靜以觀物,側重在概念化知識之形成,且也顯示出主動性、靈活性和計畫性諸特徵。然而,就現實生活界而言,其核心動力隱於意識背後的深處。支配意識活動的原動力在意欲向前的衝動,理智的認知和分別計算之能力被利用於現實意欲對外活動的工具。對梁氏而言,自覺蘊於自己的自我理解,非對外營求,意識則是由感覺、知覺、思維、判斷所連貫而成的對外活動。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中國哲學史綱的圖書 |
 |
中國哲學史綱 作者:曾春海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8-27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95 |
📌哲學79折起 |
$ 792 |
歷史、哲學、宗教 |
$ 818 |
高等教育 |
$ 818 |
高等教育 |
$ 836 |
哲學概論 |
$ 83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哲學史綱
華人世界中儘管身處異國,擁有不同的國籍,卻有一共同的文化身分,也就是在心靈深處積澱了不同質量的中國文化元素。在器物、制度、理念的文化三大結構中,無疑的,涉及一民族核心價值的哲學性理念是最具普遍性及長久性的。
本書以史綱方式撰寫、以精實的內容從中國哲學方法、精神特質開始,談論先秦哲學、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佛學、宋元明理學,一直到當代哲學。內容緊湊,將豐富的材料擇其精要來呈現。
一本完整的中國哲學史,對構成一民族文化心靈的源流脈絡及其文化認同力是最具自我理解力的。本書可說是華人世界紹述中國哲學內涵及史脉,視域開闊,內容豐富多樣且深刻的一本好書。
本書特色:唯一從傳統走入當代的哲學史
包含二十幾年來最新的哲學研究、出土文獻和研究成果
中國哲學史多年來以勞思光的中國哲學史(共四冊)為主,歷三十多年之久,然而近二十年來,先秦出土文獻的大量出現及密集研究所獲成果,以及中西哲學之交流對話,使當代中國哲學之發展脈落及精神風貌也成為學界關注之焦點,這是書裡所欠缺的。
作者簡介: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及系主任、輔仁大學哲學系及東吳大學兼任教授
學歷:輔仁大學哲學博士(1977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政治大學及輔仁大學專任教授
著作:《易經哲學原理》、《兩漢魏晉哲學史》、《先秦哲學史》、《朱熹哲學論叢》、《中國哲學概論》(主編)、《儒家的淑世哲學》、《易經哲學的宇宙與人生》、《朱熹易學析論》、《王船山周易闡微》、《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陸象山》、《儒家哲學論集》、《中國哲學精神發展史》(合著)
章節試閱
第六篇 當代中國哲學
鴉片戰爭以來,清代長期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終於慘遭無法回應西方世界經過現代化歷程後挑戰中國的惡果。歐風美雨的狂風不斷侵襲疲態畢露的中國,導致中國傳統的文化遭受質疑,政治、經濟劇變,傳統價值觀念與社會秩序結構承受動搖和崩解的危機。救亡圖存的辛亥革命不但未能力挽狂瀾,且使政治分裂動盪,舊社會的價值信仰與秩序逐漸剝落,新文化的價值觀與社會秩序未能成熟建構。就國運觀之,外患不息、內憂頻仍、世風不變,浮淺之士盲目崇拜附會西方文化,對中國固有的民族哲學與文化缺乏自覺性的深刻反省和自我理解...
鴉片戰爭以來,清代長期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終於慘遭無法回應西方世界經過現代化歷程後挑戰中國的惡果。歐風美雨的狂風不斷侵襲疲態畢露的中國,導致中國傳統的文化遭受質疑,政治、經濟劇變,傳統價值觀念與社會秩序結構承受動搖和崩解的危機。救亡圖存的辛亥革命不但未能力挽狂瀾,且使政治分裂動盪,舊社會的價值信仰與秩序逐漸剝落,新文化的價值觀與社會秩序未能成熟建構。就國運觀之,外患不息、內憂頻仍、世風不變,浮淺之士盲目崇拜附會西方文化,對中國固有的民族哲學與文化缺乏自覺性的深刻反省和自我理解...
»看全部
目錄
序
自序
第一篇 先秦哲學
第一章 先秦儒家學派 19
第一節 春秋時代的儒家核心思想 20
第二節 孔子至孟子期間之儒學—以近世出土文獻為依據 35
第三節 戰國中期的孟子學派 53
第四節 戰國晚期的荀子學派與《易傳》 66
第二章 先秦道家學派 93
第一節 老子的形上學與處世智慧 95
第二節 郭店及上海博物館出土簡文之道家思想 108
第三節 莊子的形上學 117
第四節 《管子》與《黃帝四經》的天道與治道 129
第三章 墨家學派 133
第一節 墨子及《墨子》一書 134
第二節 兼愛之德的涵義 136
第三節 貴義之德的涵義 138
第四節 墨...
自序
第一篇 先秦哲學
第一章 先秦儒家學派 19
第一節 春秋時代的儒家核心思想 20
第二節 孔子至孟子期間之儒學—以近世出土文獻為依據 35
第三節 戰國中期的孟子學派 53
第四節 戰國晚期的荀子學派與《易傳》 66
第二章 先秦道家學派 93
第一節 老子的形上學與處世智慧 95
第二節 郭店及上海博物館出土簡文之道家思想 108
第三節 莊子的形上學 117
第四節 《管子》與《黃帝四經》的天道與治道 129
第三章 墨家學派 133
第一節 墨子及《墨子》一書 134
第二節 兼愛之德的涵義 136
第三節 貴義之德的涵義 138
第四節 墨...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曾春海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8-27 ISBN/ISSN:978957116768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868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