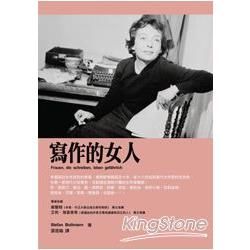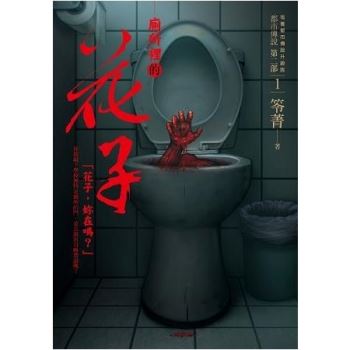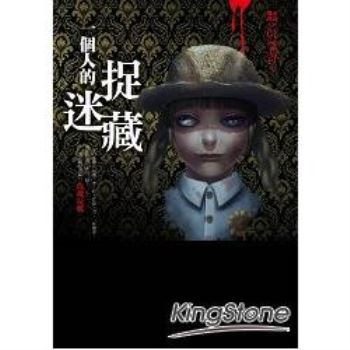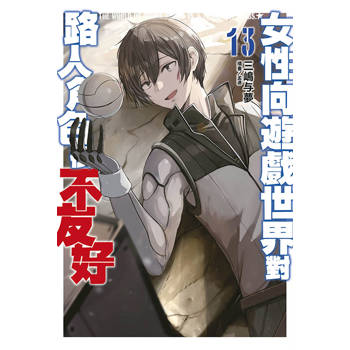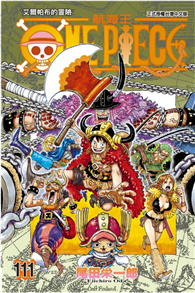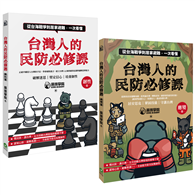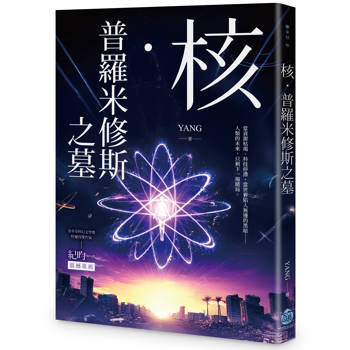本書特色:
本書探討女性寫作的樂趣,橫跨歐美兩百五十年,從十八世紀到當代女作家的生命史,也是一部現代小說簡史,勾勒這些勇敢大膽的女作家輪廓:珍•奧斯汀、喬治•桑、吳爾芙、西蒙•波娃、普拉絲、波特小姐、克莉絲蒂、莒哈絲、莎岡、萊辛、摩里森、尤瑟納……。
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恰巧所有最聰穎、最具創造力、最有天分的女人都對自己的生活感到絕望,覺得無法再繼續承受?顯然地,保有愛情並同時進行藝術創作能讓男人感到快樂,卻足以摧毀女人。箇中原因非常簡單,卻也實在讓人難以忍受,男人之所以能夠兼顧兩者,是因為有女人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讓他們專心寫作(或進行其他創作),那麼,又有誰來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呢?男人非常樂於將女人看做創作的謬斯,那麼,女人的謬斯又是誰呢?他在哪裡?女人必須自己成為自己的謬斯。
作者斯提凡‧博爾曼在本書探討女性寫作的樂趣,女性若想將寫作當作自存在的困頓中解放出來的途徑(當然只能在幻想中實現),她們必須毫不動搖地相信自己,必須冥頑不靈,必須懷抱極大的耐心;閱讀這些女性書寫者的生平紀事,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家庭和社會通常都帶給她們難以克服的阻撓,許多女性在究竟該屈從抑或追求精神獨立的裂口中崩潰,有些女性則擺脫了這樣的壓力,為了不受侵擾,作家喬治•桑(George Sand)甚至以男性化名寫作。
寫作的女人生活充滿危險,尤其,她們的生命通常都非常短暫,就算活得長,有時卻在孤獨、貧窮中度過,最後更經常完全被人遺忘。生命是危險的,生命的終點總是死亡,寫作是危險的,寫作的終點是作品,女性作家用生命換來的作品能夠幫助我們度過剩餘的歲月。
作者簡介:
Stefan Bollmann (斯提凡.博爾曼)
生於1958年,大學時研習德國文學、戲劇、歷史、哲學,並以托馬斯.曼為論文主題獲得博士學位。目前定居慕尼黑,擔任教師與作家,出版著作等身,2005年,在伊莉莎白.山德曼出版社旗下出版暢銷書《閱讀的女人危險》(中文版,左岸文化,2006)。
譯者簡介:
張蓓瑜
學歷:輔仁大學德國語文所
明斯特大學德國語文學博士班
譯作:《女人與珍珠》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我們這些才華洋溢的女人最終總以愛情的失敗者收場。──阿爾韋西娜.斯托爾尼,阿根廷女詩人
◆如果死亡找上某個人、逼迫他,這個人必定是個男人;但是,如果有人自我了斷,這個人必定是個女人。──安妮.塞克斯頓,美國女詩人
◆女人是不寫作的,若她們寫作,就會去自殺。──貝莉.蘿西,烏拉圭詩人
◆本書是女作家的生平故事集錦,也是一本多面向、多層次的豐富之書,它不僅是一部從十八世紀到當代的女性生命史、女性主義理論的演進史,同時更是一部現代小說的簡史。……它羅列了許許多多精彩女人的故事,就像是一幅仕女圖繪的長卷,她們不見得優雅美麗,但卻個個活潑大膽、浪漫不羈,充滿了自己獨特又鮮明的個性。──郝譽翔
推薦人:
郝譽翔(作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教授)專文推薦
艾柯.海登萊希(德國自由作家及電視讀書節目主持人)專文導讀
名人推薦:◆我們這些才華洋溢的女人最終總以愛情的失敗者收場。──阿爾韋西娜.斯托爾尼,阿根廷女詩人
◆如果死亡找上某個人、逼迫他,這個人必定是個男人;但是,如果有人自我了斷,這個人必定是個女人。──安妮.塞克斯頓,美國女詩人
◆女人是不寫作的,若她們寫作,就會去自殺。──貝莉.蘿西,烏拉圭詩人
◆本書是女作家的生平故事集錦,也是一本多面向、多層次的豐富之書,它不僅是一部從十八世紀到當代的女性生命史、女性主義理論的演進史,同時更是一部現代小說的簡史。……它羅列了許許多多精彩女人的故事,就像是一幅仕...
目錄
中文版序:郝譽翔
複數的生活
導 讀:艾柯.海登萊希
書寫的女人生活危險
第一章 珍.奧斯汀、維吉尼亞.吳爾芙和她們的姊妹們
與天使作戰
第二章 愛情地圖
女性作家的先行者
第三章 男人的屋子、女人的房間
感覺的對立世界
第四章 從阿姆河到崑特布恩宮
發現童年之旅
第五章 書寫以生活,生活以書寫
邊緣路
第六章 寫作以反抗
論勇氣
第七章 從巴黎到紐約
虛構人生
第八章 愛與藝術無國界
世界文學中的女性之聲
中文版序:郝譽翔
複數的生活
導 讀:艾柯.海登萊希
書寫的女人生活危險
第一章 珍.奧斯汀、維吉尼亞.吳爾芙和她們的姊妹們
與天使作戰
第二章 愛情地圖
女性作家的先行者
第三章 男人的屋子、女人的房間
感覺的對立世界
第四章 從阿姆河到崑特布恩宮
發現童年之旅
第五章 書寫以生活,生活以書寫
邊緣路
第六章 寫作以反抗
論勇氣
第七章 從巴黎到紐約
虛構人生
第八章 愛與藝術無國界
世界文學中的女性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