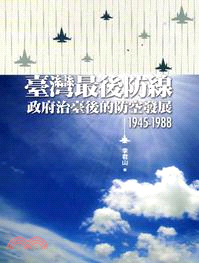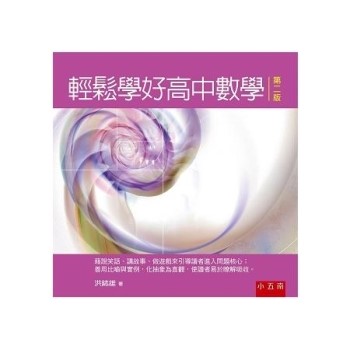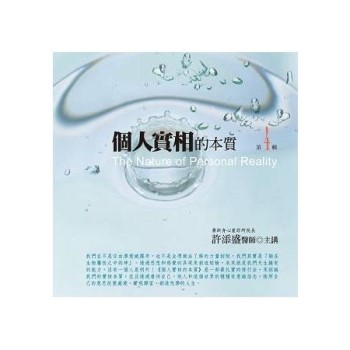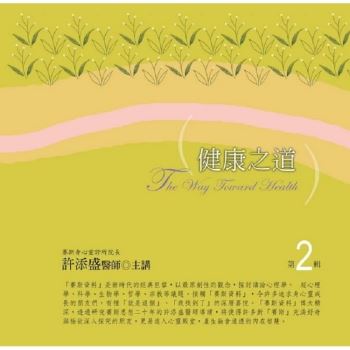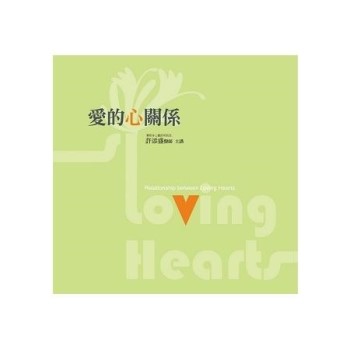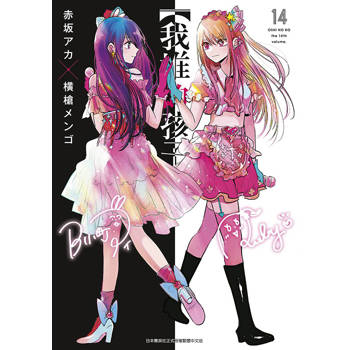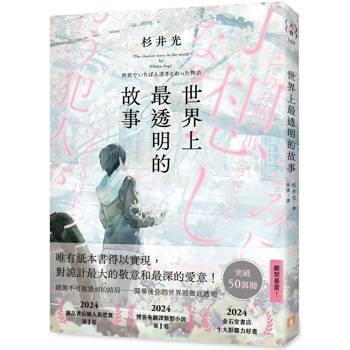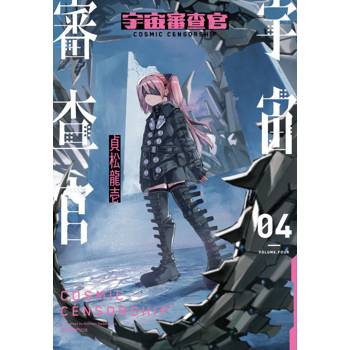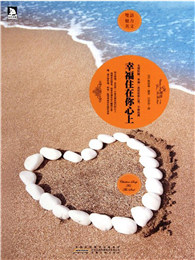書摘/試閱前 言
(一)冷戰史與生活史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在其名著《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開宗明義就將20世紀定義為大災難(Catastrophe)和總體戰(Total War)的年代。這說明了最近的100年間,「總體戰」實際已成為一世界性的現象,無關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無關國勢強弱、甚至民主獨裁,所有國家的戰爭論述,不約而同都朝向這個概念發展。其影響已不限軍事、政治,包括民生、社會思潮,也受牽連所及。所以霍氏又感歎:
這個世紀教導我們,而且仍在教導,就是人類可以學著在最殘酷、和理論上無法忍受的條件下活了下來。......在二十世紀的歷程中,戰爭是越來越以損害各國的經濟和基礎建設,以及它們的平民百姓為目標。自從一次大戰以來,所有交戰國家裡面,除了美國,喪生於戰火下的平民人數,早已遠比軍事傷亡來得慘重。
這段話中,實際也點出了總體戰的重要特色,包括軍事技術上的革命,如戰略轟炸與防空、空中戰鬥與偵察、戰爭工具的機械化、後勤行為轉而依賴內燃機,乃至化學戰的擴散和恐懼等,不僅徹底改變了20世紀的戰爭面貌,也將交戰前線與平民百姓,一併捲入各種災難當中。
惟總體戰的時代意義,除了現實環境上武器的進步外,更為重要者,是「民族戰爭」(Volkskrieg)的共同想像。其論者慣將戰爭行為分成「政府戰」(Kabinettskrieg)和「全體戰」(Totale Krieg)兩個層次,強調差別就在「人民」(民眾、全民、民族)的參與程度。 蓋自拿破崙戰爭(1804-1815)以來,國家之軍隊為人民所支持、軍事之勝利為人民所期待、戰爭之目標為人民所認同,「民族戰爭」已屬傾全國之力以支持的總體戰爭。爾後更將工業革命和意識形態、政治與種族狂熱、侵略與自衛想像等等,結合成一個殘酷的整體,驅使著各工業化社會,徹底動員人力,並自行化身為巨大的兵工廠,終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迸發成一段長期且嚴酷的毀滅過程。
此一毀滅過程中,最能凸顯「前線」和「後方」之零距離、或作戰和非作戰人員之無差別者,自數「空權」與「防空」的發展。所謂「防空」,依其手段及目的,略有「積極防空」和「消極防空」之別。積極防空或可另稱「空防」,較屬「軍防」之概念,即以空防軍力攻擊、驅阻乃至殲滅入侵之敵,使己方損害減至最低。消極防空則「民防」成份居多,係指以各項預防性措施,如疏散、偽裝、掩蔽、救護等,減低因敵空襲所加諸的損害。 後文為討論上的便利,將逕以空防(=軍防)與防空(=民防)兩詞,做簡易的分類。
1949年中央政府遷設臺灣以來,對於總體戰(現稱「全民國防」)和防空工作的提倡,始終不遺餘力。也因此,「逃警報」和「防空演習」就變成那一代、甚至是兩代人的共同記憶。1951年,「渡海三家」中的溥儒(心畬,1896-1963)寄居臺北市臨沂街,鄰人斥資2,000元新建防空洞一所,好意邀溥,遇事即請前來避難。溥乃戲作小品「逃警報之標準姿式」(見【圖表0.1】),畫中小兒一手摀耳聽飛機方向,一手挾著棉被,大步快跑,頗寫出當年戰時風情。
而1944年出生的作家李渝,當溥儒揮毫時,還只是臺灣省立臺北女師附小的小學生。回憶起1950年代初,從韓戰到第一次臺海危機的「戰後少年」歲月,往往課上到一半,空襲警報響了,曾躲過無數警報的老師們,就會鎮定地領導大家,進行各種掩藏動作,如俯身貼去牆邊、躲去桌子底下等:「雖然這只是常有的演習,在拉長的嚎嘯聲中,慌張和恐懼上升,仍舊每次都是心含在口中的」。
於是冷戰史與生活史,在防空的動員和經驗中,得到了接榫。戰後的40年,當局不斷運用防空工作,來型塑「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的冷戰氛圍。這類倡導或鼓吹,潛移默化後,卻變成了庶民生活中,另類的物件及意象(見【圖表0.2】)。至今猶存的例子,就是「防空色」,轉化為諸多文本中,意味無窮的綠制服。
(二)臺灣之兵要地理
1950年3月,甫由中國國民黨總裁「復行視事」,重返中華民國總統職位的蔣中正(1887-1975),為著臺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1908-1997)得自香港的一份剪報情資〈論臺灣攻略戰〉,驚訝不置。當時韓戰尚未爆發,中共「武力解放」臺灣的口號震天價響,情資所述竟至鉅細靡遺。蔣手令交付參謀總長周至柔(1898-1986),速與國防部第二、三廳研議,「於十天內報核。原文何日發表,先呈閱」。
6月8 日,由當時主管情報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蔣經國(1910-1988)和周至柔聯銜,解釋該文係稍早於香港中共外圍刊物《週末報》上連載,已印有單行本,改稱《攻臺必勝論》,作者託名「黎志潔」,並檢呈原書一冊。 接著周呈遞研究意見,承認該書「可見匪方『知彼』之深、用心之積極」,「其對臺灣兵要地理之研究頗深切,對我軍兵力之估計,亦相當精確」;結論是證明「此實由於匪諜運用之成功,故我方對於保防工作,實不容忽視」云。
周的報告,無異是為黎書的「信史」價值背書,也道出當年臺灣防衛的艱困程度。60餘年後,吾人檢視存檔原冊,饒富趣味之處,實在它是用敵人的眼睛,評估臺灣的戰略地位、兵要地理。儘管難以避免「為匪宣傳」之弊,但比較本土的一般軍訓教材,卻具有相當的對照作用。
書中〈從經濟與地理上,看臺灣必不能守〉標題下,強調臺灣是一座孤島,在軍事作用上,利於成為攻勢戰略的前進據點,而不利於守勢防禦的基地。也就是說:當假想以太平洋為戰爭場域,臺灣只要擁有廣大的後方,則將屬一處理想的攻勢據點,地理位置值得重視。不過一旦守勢防禦,臺島的戰略地理與重要性,恰巧相反。畢竟地理環境上,長不過400公里、寬不過150公里,竟有海拔4,000公尺的高峰;島小、峰高、河流淺急、坡度極大,使臺灣基本缺乏自給自足的條件,「拋開了大陸,他是戰略上的死點,無法堅守、不可能堅守的」。
其次,臺灣的地形,利於攻而不利於守。海岸線的遼長,駕乎中國任何省份之上;且除了東部若干地區外,攻者都可以選擇登陸,守者無法處處設防。島內交通雖稱便利,使「蔣匪」容易集中兵力,組成火網;但鐵、公路離海岸太近,如果解放軍分頭登陸,個別切斷,則守軍將被孤立於幾個包圍圈而聚殲之:「事實上,我們相信臺灣攻略戰展開之時,也必然同時在幾個地點發動,決不允許蔣匪殘餘,集中一點以頑抗的」。
(三)海島環境的先天限制
接著,《攻臺必勝論》具體討論了登陸的地點和時機,提及臺灣海峽的海流,分為北上的暖流(今稱「黑潮」)和南下的寒流(今之「親潮」),在新竹一帶匯合。春季以前,據臺灣氣象局的統計,西部沿海東北季風,每秒總在3.5公尺左右;使得每年冬季到次年春末,即11月至3月間,洋流是由北向南;非至3月以後,才能逐漸轉向。所以3、4月間,自福建航向臺灣的機帆船,往往去程要比回程,時間節省達3分之1。
至於登陸的地點,列舉了淡水、新屋、舊港(新竹)、梧棲、鹿港、新港、東石、安平、高雄、東港、東城(疑為「臺東」之誤)等11處海灘。強調在臺北方面,福建的馬尾至淡水,僅有128浬;如以福建平潭島為基地,至淡水則不過100浬左右。時速10浬以上的機動船艦,9小時即可到達。在臺南方面,廈門至安平僅有147浬、至高雄160浬。甚至鵝鑾鼻、貓鼻頭等地,有廣大的淺灘,且為縱貫山脈的尾閭,易於登陸、組織、掌握制高點,也是搶攻的上選。
綜上所論,該書指出:「如果以福建沿海為出發基地,進擊臺灣,三、四月間是最有利的時期。因為這一時期,是自閩赴臺,航行上的最有利時期」。針對蔣中正復行視事,則喊話稱:解放軍登陸攻臺,不會晚於1950年的春、夏之交:
蔣介石的復辟,其壽命是不會超過袁世凱多少的。按:袁世凱稱帝,凡八十三日而覆滅。中秋前後,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一方公里的臺灣土地上,將遍插五星紅旗,是可以預料的。
《攻臺必勝論》有如末日預言般的鐵口直斷,加上當時蔣中正、周至柔等人的反應,一方面印證1950年上半,中共攻臺傳聞的風聲鶴唳;另一方面,書中對於臺灣兵要地理的解釋,也有助凸顯環境條件上,本島防空工作的根本困難。即使稍後韓戰爆發,美國軍援到來,空軍總司令部在向蔣中正遞交的《防空作戰》報告書,所言各項弱點,實際仍與《攻臺必勝論》的評估差距不遠:
本省受地理因素影響,防空缺乏縱深,預警時間短促,而形成空防之弱點。我空軍基地多在西岸,預警系統無法延展;加以飛機航速日增,防空作戰可利用之時限,益形短促。欲求有效之防空作戰,既不能以空間爭取時間,則端賴以時間爭取空間,而期於敵機未達目標投彈線之前,予以擊滅,以確保本島空防之安全。
故而結論上,強調「戰於境外」、確保制空制海權,是屬唯一的自衛之道。
(四)文獻評述與研究方法
以上所述,重點在舖陳臺灣空防和防空的一般狀況,以為本書主題──1945至1988年,政府治臺後的防空發展,作一註腳。全書主旨乃欲探討蔣中正與蔣經國主政時期,當局在防空工作上的幾個主要面向。若由下而上,從基層到高層,概略包括:(一)基層編組和防空演練;(二)防空電信與通報體系;(三)中央部會之疏散辦公;以及(四)層峰戰時大本營之設置等。此為目前學界尚未觸及的嶄新主題,亦屬1950年代兩岸冷戰史和生活史的一個失落環節,相信應有其研究的價值。
過去有關臺灣「空防」和「防空」的文獻資料,已出版者相當有限。空防事涉軍事,多數係在空軍發展的主題下,加以容納。防空工作則較著重群眾動員,其描述蓋皆包含在「民防」相關的介紹中。然不管防空或民防的專書,早年若非軍訓用書,以提示訓練、防護之技能為主;就是類如政治讀物,強調的是「生聚教訓」「居安思危」等總體戰教義。再加上具體的規章、組織,泰半涉及業務機密,在公開發行的出版品中,更不宜周詳說明;以致各種文獻,可利用之價值往往偏低;即使汰蕪存菁,也多斷簡殘編,終究難窺堂奧。
其中民防類的書籍,出版時間較早者,如吳經侯《民防要務彙編》和「臺北市民防指揮部」《家戶民防訓練手冊》, 由於「去古未遠」,許多法規、組織,反而記載較詳;儘管內容多為原則性、概括性的說明,至少讀者能從其中,了解若干沿革和發展。稍後發行者, 或許撰寫人已非真正主事者,內容反而偏重「政令宣導」或「激勵民心」之類作用。其間差別,是否反映著「防空」在臺灣的意義,已由早期「技能演練」的考量,轉移為後來「政治宣傳」的工具性格,實亦值得吾人玩味。
防空之效能,端賴電信通報;最有效的辦法,厥為人口、物資疏散。電信史方面,有王庭樑《戰時電信》、徐耀南等《臺北電信史略》, 介紹戰時一般電信之佈署維修原則,以及臺北縣市的電信發展。至於防空疏散,則有陳胤宏《遠離臺北:臺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運用國史館庋藏的歷次《行政院會議紀錄》,與本主題關聯性頗高。
由於既有的文獻,幫助有限,因此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係依賴國家檔案管理局所架設NEAR(Navigating Elecronic Agencles’ Records,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搜尋系統,先取得政府各機關庋藏的檔案卷名、卷號;再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之相關規定,向各該管機關提出申請。
章節內容方面,除「前言」「結論」外,分為6章,概依時序,從基層到高層,分別探討1945至1953年,政府所進行的各項官民防空避難計劃(第一章);1954至1958年兩次臺海危機期間,部會疏散的努力、與「陽明營房」的起建(第二章);省政府民防措施的迭變、及1954年以後「疏遷」中興新村的爭議(第三章);1961至1965年,反攻大陸之「國光計劃」高潮,和蔣中正普設行館(賓館),作為戰時大本營之關聯性(第四章);配合著各項疏散計畫,在防空通信方面的建設與變革(第五章);以及防空演習、城市疏散等庶民生活史相關的各種發展(第六章)等。
所以本書主線,係嘗試由「冷戰史」與「生活史」的背景出發,就當局各項防空、疏散措施,一以貫之。史料方面,則借重總統府、省政府現存檔案、行政院會議紀錄,搭配臺北國史館與檔案管理局已公開之館藏。圖表也盡量以原件呈現。最後結論則將試由公共行政和群眾動員的角度,探討政府防空規劃的意義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