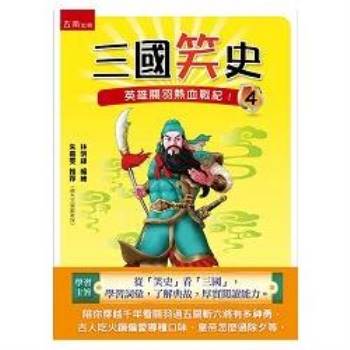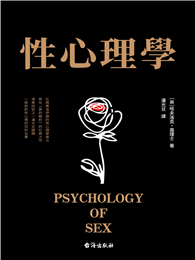序言
大約在一九八五年前後,我買到美國唐德剛著的《胡適雜憶》和他譯著的《胡適口述自傳》兩書很感興趣。尤其是《胡適雜憶》一書,文筆生動,頗見才華,不少人都說簡直把胡適寫活了,事實上我也這麼覺得。
後來又聽說,一九八七年建國以來出版的第一本《胡適傳》寫得很好。但是我跑了多家書店都買不到,很感失望。
說也湊巧,編著《胡適傳》的白吉庵先生最近搬進我們社會科學院宿舍大樓的西樓,我住北樓,相距很近,承他枉過,相談甚歡。白先生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專家,掌握資料很多,令人欽佩。他說應人民出版社之約,將舊著《胡適傳》改寫、擴充為三十多萬字。辱蒙不棄,他要我寫一篇序言,我愧不敢當,又固辭不獲,只好勉強寫一點自己的感想。
胡適先生一九一七年從美國留學回來,任北京大學教授,一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又出國。我於一九二八年考進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三○年進入本科史學系。這年冬天,胡先生重回北大,任文學院長,並在中文系和史學系開課。我就選修過他在史學系所開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這門「叫座」的課程。
胡先生個子不高,戴眼鏡,穿皮鞋,身著長衫,西裝褲,乾淨整齊,風度極為瀟灑。他上課總是在當時叫馬神廟(也稱景山東街,今改名為沙灘後街)的北大二院的小禮堂,座無虛席,加上旁聽的同學,整個禮堂被擠得滿滿。他講起課來鏗鏘有力,抑揚頓挫,莊諧並陳,從沒有「這個」、「那麼」一類的浮辭口語,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能引人入勝,聽進耳裡,印在心中,珠璣連篇,才氣橫溢,真是令人信服。他所印發的講義雖然只是一個提綱,但是內容豐富,條理清楚,每個章節,還附有詳細的參考書目和文獻,不但與講授配合,而且還可據以進行深入研究。那時北大著名教授很多。惟有胡先生的講課使同學們最感興趣。
胡先生還是一個大學者。他好學深思,鍥而不捨,又勤於撰述,著作等身,先後出版的專書就有三十餘種,像《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古思想史長編》、《白話文學史》、《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胡適留學日記》等著作也有十幾種。還有生前沒有發表,等到逝世後才由後人影印出版的《胡適手稿》也達十集三十冊三十五卷五千餘頁。
胡先生家學淵源,早年在私塾讀書,受到績溪「三胡」和他父親的影響,對中國舊學具有一定的基礎知識。後來留學美國,多年住在國外,與西方學者接觸,又學到一些近現代的治學方法。他是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學生,深信杜威的實驗主義。他在《我的歧路》一文說「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說,再細心求證。」他又繼承清代乾嘉考據學的治學精神。他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說,「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只是兩點:(1)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所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就這樣,他經過中西學術的總結,提出了一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問題。
研究學問,首先詳細占有資料,從大量資料的綜合研究中,先形成一個初步的看法,然後就提出大膽的假設,為了證實這個假設,再細心去求得證據。這種治學的態度,還是有其可取的地方。
胡先生早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及對《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三俠五義》、《兒女英雄傳》等十幾部古典小說的考證,就是採用的這種方法。確實有許多開拓創新的地方。
到了晚年,他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始,為了探索「全趙戴三家水經注案」,費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用了他後半生的精力,進行《水經注》的研究。最突出的一點,是他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上海或在北京,沒有不想盡種種方法,去搜集各種版本的《水經注》。用他自己的話說,「各地的《水經注》,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費海璣也說「全國的《水經注》,都集中到他寓所,達三大櫃之多」。對這三大櫃的《水經注》,他編有目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大學還舉行過「《水經注》版本展覽」,展出的《水經注》版本有九大類、四十一種。連《水經注》研究專家陳橋驛在評《胡適手稿》都說胡先生「是酈學史上搜羅版本最多的學者」。
胡先生逝世後才出版的《胡適手稿》,其中一至六集十八冊二十二卷,都是關於《水經注》研究的文章。楊聯升為手稿寫的序文說,「胡先生從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起重審此案,前後近二十年,他的用力之勤,令人驚歎,收穫的豐富,連胡先生自己都沒有預想到。」陳橋驛也一再稱讚手稿,說「手稿無疑是我國學術界的一部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巨著」。又說「手稿當然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這中間首先是手稿發表了胡適的大量學術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中有許多是十分卓著的,它們無疑是極有價值的學術財富。」
胡先生在北京大學,曾任教授、主任、院長和校長,在中央研究院曾任史語所的名譽研究員,研究院的評議員、院士,後來還任院長。我是北京大學預科本科六年畢業,又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七年。在北京大學時,他是我的老師,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他又是我們的領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抗戰結束,我復職回到南京。記得有一年在史語所,傅斯年先生請客,除了胡先生之外,同席還有陳垣先生和袁同禮先生,當傅先生介紹我給胡先生,胡先生說「我在美國,常引用你的文章」。我說「你桃李滿天下,我是你的學生,你不記得我了。」看得出來,他當時聽了很高興。
胡先生不想做官,但要談政治,早年編輯《努力週報》、《現代評論》和《獨立評論》,晚年去臺灣還要支持《自由中國》。不過他過於保守,遇事總是要改良妥協,堅持資產階級的立場,結果就走得很遠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白吉庵先生專門研究中華民國史,今出版《胡適傳》一書,材料充實,觀點明確,既肯定胡先生的貢獻,也指出他的不足的地方,實事求是,是一本很好的著作。故願為此序,權當推薦介紹。
胡厚宣
199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