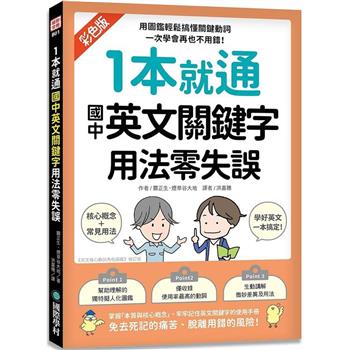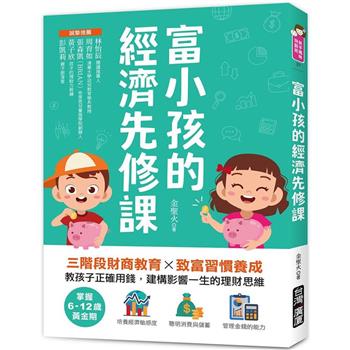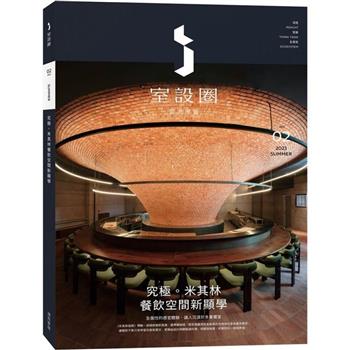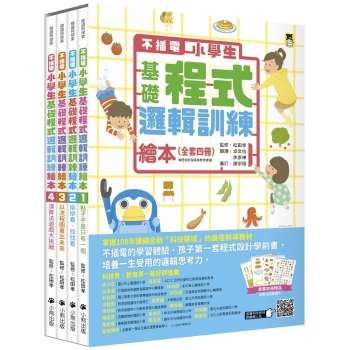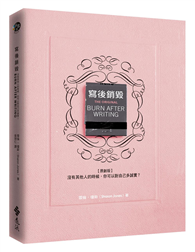一章 《樂記》外考證
─比對志書、體例及引文
「文獻材料的真偽鑑定」指的是對文獻史料的產生時代、產生地點、著作者、及文獻史料原形的確定。如果研究古籍文獻不辨其時空背景,粱啟超於《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已指出,於史蹟方面,將造成歷史演化系統之紊亂,及社會背景混淆,並易顛倒事實是非,從而影響於道德及政治。而於思想方面,將同樣造成時代思想紊亂及學術源流混淆,因而易使學者枉費精神而得致錯誤之果。
在傳統的學術領域中,這類工作大多歸於辨偽之學。歷朝有許多學者皆談到辨偽的方法,而總其要,可以明代胡應麟《四部正譌》所提出檢核偽書之八法為代表:
1.覈之七略以觀其源
2.覈之群志以觀其緒
3.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4.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
5.覈之文以觀其體
6.覈之事以觀其時
7.覈之撰者以觀其託
8.覈之傳者以觀其人
其中前二條指出辨偽之法,首先可以透過比對史志或收錄文獻名目來進行。
第一節 史志或收錄文獻名目之考察
對鑑別先秦文獻來說,可資比對之史志及目錄,即為《別錄》、《七略》、及《漢書‧藝文志》。《別錄》為劉向所作,其於西漢成帝時,奉詔校對並編輯西漢前之文獻典籍,蓋經秦皇焚書及漢初鼓勵獻書,有關先秦典籍之情形不明,於是劉向乃將所收納的書,認為可信為先秦著作的,條列篇章名目,並做簡單的摘要,進呈給漢成帝,後集而寫成《別錄》。西漢末葉時,劉向子劉歆繼承父業,將其父所遺漏或失誤的部分做了增補修訂,並對先秦文獻建構起清楚的分類,另外寫成《七略》一書。到了東漢初,班固以《七略》為本,保留其文獻分類及篇目條列,但刪去各類之摘要,另稍增補一些西漢時之著名著作,寫成《漢書‧藝文志》。
由於《別錄》、《七略》、《漢書‧藝文志》乃是經三位大學者所考訂過的目錄,同時兩漢時代又距先秦不遠,三人於考訂時佔有許多優勢,因此歷朝歷代的學者咸以為這三本書是鑑定先秦文獻最根本的依據,若一文獻三書皆沒有收錄,該文獻則為後代偽造。
然而,現代著名的目錄學大家余嘉錫於《古書通例》中指出欲辨古籍真偽,即使依照史志及目錄所載來鑑別,仍然可發現有遺漏及未收入者。就《漢書‧藝文志》來說,有明見於《漢書》的本紀列傳,確為劉、班時書,而《漢書‧藝文志》卻未收者數種。如〈楚元王傳〉記載「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但是〈藝文志〉卻沒收。另如〈禮樂志〉中記載「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此乃班固自言叔孫通曾寫禮儀之書,但因藏於宮中,屬於國家法典,因此不像其他著作一樣被收錄進史志中。《後漢書‧曹褒傳》言:「班固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是班固得書而不錄入史志之證言。
此外,余嘉錫還指出,
前漢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漢書》亦遂不補也。《七略》之作,由於奉詔校書,故當時人著作,成書較後者,皆不收入,班固直錄《七略》新入者僅三家,劉向、楊雄,以大儒負盛名,杜林《蒼頡訓纂》,因其為小學書,家絃戶誦,故破例收入,其餘皆不甚留意。〈王莽傳〉之《樂經》,〈律歷志〉之《三統歷》,並不見錄,他可知矣……〈藝文志〉於漢時書,不盡著於錄,證之本書,章章可考。其他古書,真出於西漢以前而不見於志者,皆可以三例推之。
除了余嘉錫所舉之例外,南宋學者王應麟作《考證》時已增入不著錄之書27部,民國學者章炳麟、顧實等亦曾舉出其他遺漏。由上,如胡應麟所立之綱而在傳統中被深信不疑之法,經余嘉錫等治學大家所檢核後,依其經驗而補註曰:「據史志目錄以分真偽之法,不盡可憑也」。
從上述比對史志之辨偽法則及治學大家之經驗談,來對《樂記》之成文年代及著作者做考證,並檢視前輩學者們所提出之說法,可以發現,這樣的做法其實所得有限,並不能對《樂記》年代作者進行有效鑑定。
前輩學者們所提出的說法,大抵分為幾種:有認為是戰國初年之公孫尼子所作,有認為是西漢河間獻王劉德所作,亦有認為是兩漢間的許多儒生所共作。不論是那一種說法,考之文獻,可見皆是從以下三段材料為本所做的推斷。
第一段乃是《漢書‧藝文志》中,班固據《七略》所記載者: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第二段乃是東漢末葉古文經大家鄭玄對《樂記》及《別錄》所做的考證:
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
第三段則是《隋書‧音樂志》中單獨出現的一句話,記錄沈約答梁武帝問樂:
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樂記取公孫尼子。
從第一段材料中,可知班固所見之《樂記》收錄有兩個版本,一是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與毛生等所編或作,而由王禹所傳之《樂記二十四卷》,一是漢成帝時劉向所收之《樂記二十三篇》。今天所見的《樂記》,則出於武帝與成帝間之漢宣帝時,戴聖所編輯之《小戴禮記》四十九卷中之第十九卷,內文或可更細分為十一個小篇章。由於《漢書‧藝文志》本身並沒有將這三者間的關係異同交待清楚,因此學者們的分歧意見,即在於判斷《禮記》之《樂記十一章》與《樂記二十三篇》及《樂記二十四卷》之間的關係。
有學者認為,如果可確定《樂記十一章》真為劉向所收錄,則可斷言《樂記》應是先秦文獻。可是,既然劉向之《別錄》及劉歆之《七略》已亡佚,無法比對《漢書‧藝文志》所載是否屬實,並查看《樂記十一章》是否即是劉向《樂記二十三篇》中之十一篇,因此,寧可持懷疑的態度而不予採信《樂記》被劉向所收。反之,在《漢書‧藝文志》中有稍為明確的說詞:「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然不無輕信之嫌,但仍比前者可信,因而主張《樂記》及河間獻王劉德所作,非先秦文獻。
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樂記十一章》即是劉向《樂記二十三篇》中之十一篇,其所依據者,即為第二段材料中所示鄭玄的考證。鄭玄似乎有看過劉向《別錄》,並比對過《樂記十一章》與《樂記二十三篇》中的篇章名目是相符合的。其後唐代的孔穎達在編撰《禮記正義》及張守節在寫《史記正義》時,皆引用了鄭玄的說詞,而持相同的觀點。後世學者即相信鄭玄之說,認為《樂記》為先秦文獻。
第三段材料則提出新的說法。《隋書》的主編是唐太宗時代的名臣魏徵,其所記南朝沈約回答梁武帝的話中,指出劉德之《樂記二十四卷》及劉向之《樂記二十三篇》到了晉代時皆已亡佚,《禮記》第十九篇之《樂記》與兩者的關聯異同實不可考,但《樂記》卻可知乃是摘取自先秦時人公孫尼子的著作。至於為何可知,沈約並無多作說明,魏徵亦無多加考證。學者們只是如同相信《漢書‧藝文志》河間獻王「以作《樂記》」的肯定語氣一般,相信了《隋書》中魏徵與沈約的說詞。
另外,清代馬國翰編輯《玉函山房輯佚》時,曾收納《公孫尼子》十五條佚文,其中一條來自唐玄宗時代的徐堅《初學記》引《公孫尼子》「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另一條來自唐德宗時代的馬總《意林》引《公孫尼子》「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這兩條確實可見於《樂記》之中,然徐堅與馬總是否見過《公孫尼子》全文,或只是曾從《樂記》中抄錄該兩條,而依《隋書》所記,將之歸於公孫尼子,則不得而知,但憑學者自由採信。
由於上述學者的判斷,皆出於「相信」,而非明確的文獻辨證,因此,另有學者認為無論是出於劉德或公孫尼子之說皆不可信。這些學者另考慮到《樂記》的十一章中有許多文詞是與《荀子‧樂論》、《呂氏春秋》、《淮南子》等等秦漢之際之古文獻相同或相似,因此主張《樂記》乃是西漢的儒者所共同編寫的文章,後來收入《禮記》中,而非先秦時所作。
綜觀上面的幾種說法,可以得到如下的評斷:首先,史志中的文獻內容,本身即無法清楚的提供必要的資訊,以供判斷《樂記》的成文年代,或與《別錄》、《七略》間之關係。第二,學者們所各自採用的說詞來源,不論信與不信,皆有所弊。一方面,班固所言劉德作《樂記》、鄭玄所言劉向收《樂記》、魏徵與沈約所言《樂記》取公孫尼子,皆只為一人一家之言,在史料上並無法找到直接佐證,如果相信的話,有點單薄,失之輕信。另方面,班固、鄭玄、魏徵等,皆為當世之大家學者,而其所言又不必相互矛盾,《樂記》可以為公孫尼子於先秦時所作,收於劉向《別錄》,而記載於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為劉向《樂記二十三篇》中之一部分,如果不信,則又過於懷疑,失之於武斷。因此,從這些評斷中可知,《樂記》不論是否見於《別錄》、《七略》及《漢書‧藝文志》,並不足以稱說其是或非為先秦時之書,除非有新史料出土或新的辨偽校勘法,否則分歧意見似難有一定論。
第二節 文字體例及引文之考察
透過考察一篇文獻之文字體例,及其他文獻中對該文獻之引用文句,如同比對史志目錄一般,亦往往可以幫助「文獻材料的真偽鑑定」,辨別該文獻史料的產生時代、產生地點、著作者、及文獻史料原形。是故在辨偽法則中,亦包含了文字體例之檢核,如胡應麟《四部正譌》中所述之第三、四、五、六條:「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
如此之辨偽法則,其實已和訓詁學有所重疊。訓詁學乃是研究文字音義之學問。歷史學者甲凱於《史學通論》中嘗解釋「語文方面,凡字音、音形、字義、文章,每一個時代皆有其特點。如果能在古文字學方面下功夫,必可由此辨古書的真偽」。最著名之例,即為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教授(Prof.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所著之《左傳真偽考》,其中援引中國文字古音古義之考據,以證《左傳》產生的年代,胡適曾為其作序並盛讚之。
除了辨偽學與訓詁學外,校勘學也同樣把焦點放在如何考察文字體例及引用文句上。現代著名的校勘學大家張舜徽於《中國古籍校讀指導》中解釋,
古書傳世既久,自然免不了存在許多錯誤。特別是雕版印刷術沒有盛行以前,書係手寫,更容易以譌傳譌,舉凡字體的缺謬,語句的脫落,乃至衍文增句,無所不有。假若不能找到比較好的本子和比較早的本子去校對,便很難考見古書原來的面目;更無由進一步探索其中的內容了。所以校書工作是讀書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如此,文獻在傳抄過程中,多一字或少一字,即會影響內容義理之領會,及時空背景之掌握。張舜徽以《漢書‧藝文志》為例,其中記載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發現《古文尚書》,後來「安國獻之」,孔子的後人孔安國將該書獻給漢武帝。然對照《史記‧孔子世家》,其中記載「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似乎孔安國在漢武帝中期時即已謝世。如此漢武帝末時,安國已卒而何能獻書?《史記》與《漢書》必有一誤,《古文尚書》的發現年代、進獻年代,及孔安國的生卒都成疑問。其實,這個問題已由清初學者閻若璩及朱彝尊考證後,依荀悅之《漢紀》所載,校訂為「安國家獻之」,《漢書‧藝文志》中脫一「家」字。
張舜徽另以《後漢書‧鄭玄傳》為例,其中記載鄭玄「不為父母昆弟所容」,而此似乎與鄭玄做為一代古文經學家之持穩德行有違,袁宏《後漢紀》中即盛讚鄭玄德行:「鄭玄造次顛沛,非禮勿動」。對於鄭玄人格德行之懷疑,直到清乾隆六十年,阮元在山東學政任內,到鄭玄故鄉拜謁時,偶得一石碑,與《後漢書‧鄭玄傳》相校對下,始發現「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其實應為「為父母昆弟所容」,《後漢書》中多了一個「不」字。而此一字之衍文,使鄭玄受誣逾千年矣。
以文字體例及引文之校對,來辨別原文獻之內容正誤及釐清其著作年代,一般來說是很可行的,以這樣的方法來檢核《樂記》,確實也將有一些重大的新發現。所謂新發現者,乃因為在1993年時曾於湖北出土了一批竹簡,稱為《郭店楚簡》,其中簡文,有可與《樂記》相校核比對處,其中亦是以一字之差,而使《樂記》與《郭店楚簡》兩者之獨特性彰明不少。由於這是新出土的文獻史料,因此以往研究《樂記》的學者,尚未注意到此「一字之差」的重要性,亦沒有機會對此做精細的研究。關於此點,以下(第二章)論及《樂記》內容思想時將有詳細分析。
至於以往學者對《樂記》所進行的文字體例及引文之校對,則有一些評斷值得提出。以文字體例與引文來校讀古文獻,特別是先秦文獻,需要注意到一些限制,這些限制,其實乃源於先秦文獻之獨特寫作方式與背景。
首先,張心澂《偽書通考‧總論》指出,印刷術發明前,特別是先秦時代,學者寫作的環境是很辛苦的,有獨特的限制:「古人寫字用簡冊刀錐,及進而用竹帛毛筆漆書,均不若今之紙墨之便,更不如印刷術發明後流傳之廣」,因此,古人記述言論,即有一種與現代人不一樣的習性─古人不自著書,而由門人學生記之,或古人著書不以為是自己的思想,而視作是公天下的言論。
在政治界或學術界重要之人,其口說及行事,往往由其門人或後人記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是也……章學誠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文史通義‧言公上)。故在孔子以前本無自行著書之事,即偶有所言,或係受前人之語,或係一己之思想,筆之於簡冊,亦以備遺忘,無所謂書之體例。其簡冊傳於他人或後人,即以其所言者應用。嗣後復展轉相傳,連經傳者自己之思想偶筆之於簡冊者,亦一併相傳。書為應用而設,不為傳名而設,故簡冊流傳,其著者姓名,即不自著於冊,亦往往湮沒弗彰。
《論語》、《管子》、《莊子》皆是其例,非由孔子、管仲、莊子自己書寫,而是由其門人記錄其言行,有時並加入各自的闡發應用之說,而成其篇。基於這樣的認識,於是余嘉錫對於以校勘文字而辨偽,在《古書通例》中有補充說明:
考之本書以驗其記載之合否。然古書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後師,或記敘成於眾手,或編次於諸侯之客,或定著於寫書之官。逸事遺聞,殘篇斷簡,並登諸油素,積成卷帙。故學案與語錄同編,說解與經言並載。又箋注標識,混入正文,批答評論,咸從附錄……是則即本書記載以分真偽之法,容有未盡也。
以往有學者批評《樂記》的十一章中,有些是觀點論述,有些是對話語錄,似乎在體例上不一致,而內容有時精簡,有時又針對不同的小議題(如禮樂功能)詳加闡述,似乎筆法也不一。特別是發現有些段落,也曾類似的出現於其他古文獻中,如戰國時的《荀子‧樂論》、戰國與秦代之際的《呂氏春秋》、及漢初的《淮南子》等,因此主張《樂記》乃是在漢代時不同人對古文獻的抄錄匯編,非先秦之作。
然而,由上述張心澂與余嘉錫的校勘經驗觀之,這些對《樂記》文字體例的批評,或許是對古文的書寫環境限制與習性不了解或誤解。蓋《樂記》者,可為先秦學者記錄其師尊所教導之言,因而論述與語錄同編或不足為怪矣。另外《樂記》中論述有詳細與提綱之別,或為將師者的「經言」與學者對「經言」的「說解」並載的情形,或是代師記述的傳言者將自己的箋注標識,混入正文的情形。因此,文體風格之不一致,並不足以推斷《樂記》非為先秦之作,甚至如此不一致的文體,似更符合先秦時人的著作習性。以《樂記》而言,依文字體例來校定成文年代,似不是一個有效的可行之法。
在引文的考察方面,本來,若是文獻在引用時有註明出處,那麼引文則有辨別著作年代之用。如甲凱《史學通論》中解釋:
如甲書稱引乙書或乙書的作者,史學家便可以推定乙書一定在甲書以前……此極明顯之事實,為考史的簡單辦法。可惜舊日文人著書稱引前著,往往不標明著述的年代,令後人難明,即使是博雅如顧亭林,他所作《日知錄》亦有此病,為此增加考證的困難。
然而,引文需說明出處乃是今人的習性,越是遠古之人,基於前述的寫作環境限制與習性,在文獻稱引上亦有異於現代人的作法。張舜徽《中國古籍校讀指導》中解釋,
古人引書,不一定完全符合於原文,做到一字不差。特別是在引用之際,有節略其辭的,也有引用書意的。這在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已經說的很清楚。至於倉卒引用的時候,將原來文字弄錯或將內容顛倒了的,更不可勝數。
這種習性,即呼應前述章學誠所說「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的觀念,亦符合張心澂所解釋,古人著書記述乃是為了「備遺忘」,而可供人「以其所言者應用」,即利用同樣或類似的詞句再自行增刪改寫,以表己意。事實上,這種著書的體例,古稱「述」或「編述」,以別於使用全新文詞來論說新觀點之「作」或「著作」。
以往學者對《樂記》的批評中,有以不同引文間多或少幾個字為由,而判斷《樂記》非先秦之著述者。如徐復觀於《中國藝術精神》中,比較《玉函山房輯佚》所收納《公孫尼子》與《樂記》相關的二條佚文,指出來自徐堅《初學記》引《公孫尼子》「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之文,比《樂記》在句子開頭少了一個「故」字。而另一條來自馬總《意林》引《公孫尼子》「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之文,比《樂記》除了在開頭少一發語詞「夫」字,及句中少了連詞「之」字外,主要在「軍旅」下少了「鈇鉞」兩字。徐復觀因而以為,《公孫尼子》如果確有其文,且成文於戰國時期,「《樂記》中引用此文,卻無端多出鈇鉞二字,這在引書的例子裡也是很少見的」,隨之認為《初學記》與《意林》應係轉引自《樂記》,而《樂記》成文於漢初,其中有許多抄錄《荀子‧樂論》的片段。
類似的例子,亦可見於以《史記‧樂書》與《樂記》的相比較上,由於《史記‧樂書》開頭多了對秦漢樂歌創作的綜述,結尾亦多了對舜與紂樂的批評、晉平公聽師曠鼓琴、及太史公評論等段,有學者即以為《樂記》乃成於《史記‧樂書》後,摘錄《史記‧樂書》片段而成。亦有學者以同樣理由,卻持相反意見。
然而,如果明瞭了前所述及的古人引文習性,以之來檢討諸如上述以引文來斷定《樂記》年代的作法,可知這些斷定皆屬無效。引文中所少之字,或為轉述者為圖便利所省,或為脫字。而引文中所多之字,或為傳述者理解並記憶原文時,自然產生的不影響原意的用語更動。更有甚者,引文有所更動,乃因使用該引文之古人所為,是一種「編述」文體,而非「著作」。於是,從引文間的字詞與字數比較,想得出關於文獻著作年代、釐清何者為轉鈔者、何者為原文獻,至少以《樂記》而論,是不能的了。
有鑑於這些情況,余嘉錫《古書通例》亦做了補充小結:
考之群書之所引用,以證今本是否原書。然古書皆不免闕佚。蓋傳寫之際,鈔胥畏其繁難,則意為刪併,校刻之時,手民恣其顢頇,則妄為刊落……是則援群書所引用,以分真偽之法,尚非其至也。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做一個小歸結。考察史志目錄、文字體例、及引文之法,對《樂記》而言,皆不是鑑別著作時空背景之有效良法。而在辨偽、校勘及訓詁中,另有以思想來辨證之法。考察文獻思想,將不只是有鑑定文獻真偽、著作時空之功,同時亦有考證文獻內容,釐清思想脈絡之效。於此,將使文獻校讀從「外考證」進入「內考證」。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中國舞蹈哲學史:樂記篇與中國舞蹈理論之濫觴(初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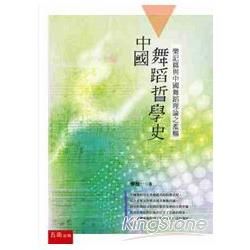 |
中國舞蹈哲學史:樂記篇與中國舞蹈理論之濫觴(初版) 作者:廖抱一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0-0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25 |
社會人文 |
$ 225 |
表演藝術 |
$ 232 |
中文書 |
$ 233 |
高等教育 |
$ 238 |
舞蹈 |
$ 238 |
藝術學群 |
$ 23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舞蹈哲學史:樂記篇與中國舞蹈理論之濫觴(初版)
中國舞蹈哲學最早的論述可見於《樂記》中,其中論及舞蹈的本質、元素、結構、功能及分析法等。在歷史上中國舞蹈與儒、道、佛家哲學有著密切的關係,舞動肢體間所表現的優雅藝術動作,將之賦予靈魂及老莊學說,更進一步確立了「意象」為舞蹈的核心元素。
以《樂記》為中國舞蹈理論核心起始,從而檢視舞蹈內涵與歷史文化之間的關聯。
本書特色:
中國舞蹈旨在透過優美的肢體表現,結合意象及哲理表達其藝術內涵。最早的舞蹈可追朔於敬畏鬼神的宗教祭儀,此時的舞蹈對於後世打下了怎樣的奠基,使得肢體藝術得到了更多元而豐富的發展。
作者簡介:
廖抱一
學歷:英國倫敦城市大學拉邦舞蹈中心博士
經歷:曾任民生報藝文版記者、紙風車劇團企劃
現職: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學系助理教授
章節試閱
一章 《樂記》外考證
─比對志書、體例及引文
「文獻材料的真偽鑑定」指的是對文獻史料的產生時代、產生地點、著作者、及文獻史料原形的確定。如果研究古籍文獻不辨其時空背景,粱啟超於《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已指出,於史蹟方面,將造成歷史演化系統之紊亂,及社會背景混淆,並易顛倒事實是非,從而影響於道德及政治。而於思想方面,將同樣造成時代思想紊亂及學術源流混淆,因而易使學者枉費精神而得致錯誤之果。
在傳統的學術領域中,這類工作大多歸於辨偽之學。歷朝有許多學者皆談到辨偽的方法,而總其要,可以明代胡應麟《四部正...
─比對志書、體例及引文
「文獻材料的真偽鑑定」指的是對文獻史料的產生時代、產生地點、著作者、及文獻史料原形的確定。如果研究古籍文獻不辨其時空背景,粱啟超於《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已指出,於史蹟方面,將造成歷史演化系統之紊亂,及社會背景混淆,並易顛倒事實是非,從而影響於道德及政治。而於思想方面,將同樣造成時代思想紊亂及學術源流混淆,因而易使學者枉費精神而得致錯誤之果。
在傳統的學術領域中,這類工作大多歸於辨偽之學。歷朝有許多學者皆談到辨偽的方法,而總其要,可以明代胡應麟《四部正...
»看全部
目錄
序
自序 3
導言 9
第一章 《樂記》外考證─比對志書、體例及引文 13
第一節 史志或收錄文獻名目之考察 15
第二節 文字體例及引文之考察 22
第二章 《樂記》內考證─思想脈絡之考察 31
第一節 考鏡思想源流的方法 32
第二節 先秦著書習性之考察 42
第三節 時代背景之脈絡 46
第四節 文脈與段落之比較 58
第三章 《樂記》年代之推論 75
第一節 「情」之命題及義涵演變 77
第二節 「性」之命題及義涵演變 95
第三節 《樂記》的思惟比對與年代斷定 117
第四章 《樂記》中所現之舞蹈哲...
自序 3
導言 9
第一章 《樂記》外考證─比對志書、體例及引文 13
第一節 史志或收錄文獻名目之考察 15
第二節 文字體例及引文之考察 22
第二章 《樂記》內考證─思想脈絡之考察 31
第一節 考鏡思想源流的方法 32
第二節 先秦著書習性之考察 42
第三節 時代背景之脈絡 46
第四節 文脈與段落之比較 58
第三章 《樂記》年代之推論 75
第一節 「情」之命題及義涵演變 77
第二節 「性」之命題及義涵演變 95
第三節 《樂記》的思惟比對與年代斷定 117
第四章 《樂記》中所現之舞蹈哲...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廖抱一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0-04 ISBN/ISSN:978957117249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68頁
- 類別: 中文書> 教育> 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