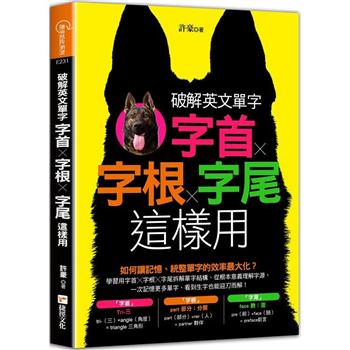第一章 概 論
我在東京曾講演過一次國學,在北京也講演過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國學很不容易講,有的也實在不能講,必須自己用心去讀去看。即如歷史,本是不能講的,古人已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現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鑑》等書似乎稍簡要一點,但還是不能講;如果只像說大書那般鋪排些事實,或講些事實夾些論斷,也沒甚意義。所以這些書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講國學,只能指示些門徑和矯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國學概論」分做兩部研究:一、國學之本體。二、治國學之方法。
一、國學之本體
(一)經史非神話
在古代書籍中,原有些記載是神話;如《山海經》、《淮南子》中所載的,我們看了,覺得是怪誕極了。但此類神話,在王充《論衡》裡,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沒有存在的餘地了。而且正經正史中本沒有那些話,如「盤古開天闢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載。又如「女媧煉石補天」,「后羿射日」那種神話,正史裡也沒有。經史所載,雖在極小部分中還含神祕的意味,大體並沒神怪離奇的論調。並且,這極小部分神祕記載,也許使我們能作合理的解釋:
《詩經》記后稷的誕生,頗似可怪。因據《爾雅》所釋「履帝武敏」,說是他的母親,足蹈了上帝的足跡得孕的。但經毛公注釋,訓「帝」為皇帝,就等於平常的事實了。
《史記‧高帝本紀》,說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澤,見神龍附其母之身,遂生高祖。這不知是太公捏造這話來騙人,還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見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託。記得湖北曾有一件姦殺案—一個奸夫和奸婦密議,得一巧法,在雷雨當中,奸夫裝成雷公怪形,從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殺。高祖的來歷,也許是如此。他母親與人私通,奸夫飾做龍怪的樣子,太公自然不敢進去了。
從前有人常疑古代聖帝賢王都屬假託;即如〈堯典〉所說「欽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的話,有人很懷疑,以為那個時候的社會,哪得有像這樣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敘太古的事,不能詳敘事實,往往只用幾句極混統的話做「考語」,這種考語,原最容易言過其實。譬如今人作行述,遇著沒有事蹟可記的人,每只用幾句極好的考語;〈堯典〉中所載,也不過是一種「考語」,事實雖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貢〉記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說:「後世鑿小小的運河,尚須數十年或數百年才告成功,他治這麼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貢〉只是一種奇蹟。我卻以為大禹治水,他不過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親身去,就遊歷一周也不能,何況鑿成!在那時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了。〈禹貢〉記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過依報告錄出,並不必由大禹親自調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馴者,可見他所記述的很確實;我們再翻看經史中,卻也沒載盤古、三皇的事;所以經史並非神話。
其他經史以外的書,若《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確有可礙者在。但《竹書紀年》,今存者為明代偽託本,可存而不論;《穆天子傳》也不在正經正史之列,不能以此混彼。後世人往往以古書稍有疑點,遂全目以偽,這是錯了!
(二)經典諸子非宗教
經典諸子中有說及道德的,有說及哲學的,卻沒曾說及宗教。近代人因為佛經及耶穌教的《聖經》都是宗教,就把國學裡的「經」也混為一解,實是大誤。「佛經」、「聖經」那個「經」字,是後人翻譯時隨意引用,並不和「經」字原意相符。經字原意只是一經一緯的經,即是一根線,所謂經書,只是一種線裝書罷了。明代有線裝書的名目,即別於那種一頁一頁散著的八股文墨卷;因為墨卷沒有保存的價值,就讓它們散葉,別的要保存的,就用線穿起。古代記事書於簡,不及百名者書於方;事多一簡不能盡,遂連數簡以記之;這連各簡的線,就是「經」。可見「經」不過是當代記述較多而常要翻閱的幾部書罷了,非但沒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漢時訓「經」為「常道」,也非本意。後世疑經是經天緯地之經,其實只言經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經天的意義了。
中國自古即薄於宗教思想,此因中國人都重視政治;周代諸學者已好談政治,差不多在任何書上都見他們政治的主張。這也是環境的關係;中國土地遼廣,統治的方法,急待研究,比不得歐西地小國多,沒感著困難。印度土地也大,但內部實分著許多小邦,所以他們的宗教易於發達。中國人多以全力著眼政治,所以對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對宗教,他說:「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對於宗教,也反對;他雖於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們體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訴我們是沒有神的。《禮記》一書很考究祭祀;這書卻又出自漢代,未必是可靠的。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確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沒有與祭的身分。須知宗教是須普及於一般人的,耶穌教的上帝,是給一般人膜拜的;中國古時所謂天,所謂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講天、鬼,陰陽家說陰陽生剋,確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謂天,陰陽家所謂「龍」、「虎」,卻也和宗教相去很遠。
就上討論,我們可以斷定經典諸子非宗教。
(三)歷史非小說傳奇
後世的歷史,因為辭采不豐美,描寫不入神,大家以為是記實的;對於古史,若《史記》、《漢書》,以其敘述和描寫的關係,引起許多人的懷疑:
〈刺客列傳〉記荊軻刺秦王事,〈項羽本紀〉記項羽垓下之敗,真是活龍活現;大家看了,以為事實上未必如此;太史公並未眼見,也不過如《水滸傳》裡說武松、宋江,信手寫去罷了。實則太史公作史,擇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齊的事,曾經孔子講及,所以他替二人作傳;那許由、務光之流,就缺而不錄了。項羽、荊軻的事蹟,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雖沒親見,但傳說很多,他就可憑著那傳說寫出來了。《史記》中詳記武事,原不止項羽一人;但若夏侯嬰、周勃、灌嬰等傳,對於他們的戰功,只書得某城,斬首若干級,升什麼官,竟像記一筆帳似的;這也因沒有特別的傳說,只將報告記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偽述,那麼〈刺客列傳〉除荊軻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專諸還有些敘述,豫讓、聶政等竟完全略過,這是什麼道理呢?《水滸傳》有一百零八個好漢,所以施耐庵不能個個描摹;〈刺客列傳〉只五個人,難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寫嗎?這都因荊軻行刺的情形有傳說可憑,別人沒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為四個老人哪裡能夠使高祖這樣聽從,《史記》所載未必是實。但須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為多數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傳中歸功於甲,在乙傳中又歸功於乙。漢惠免廢,「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說,並無可疑。
史書原多可疑的地方,但並非像小說那樣的虛構。如劉知幾《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為不確,因為更始起自草澤時,已有英雄氣概,何至為眾所擁立時,竟羞懼不敢仰視而以指刮席呢?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誣衊更始的話。又如史書寫王莽,竟寫得同騃子一般,這樣愚騃的人怎能篡漢?這也是漢室中興,對於王莽,當然特別貶斥。這種以成敗論人的習氣,史家在所不免,但並非像小說的虛構。
攷《漢書‧藝文志》已列小說於百家之一,但那只是縣志之類,如所謂〈周考〉、〈周紀〉者,最早是見於《莊子》,有「飾小說以干縣令」一語;這所謂小說,卻是指那時的小政客,不能游說六國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說幾句本地方的話。這都和後世小說不同。劉宋時有《世說新語》一書,所記多為有風趣的魏、晉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時日多顛倒處,事實並非虛構。唐人始多筆記小說,且有因愛憎而特加揄揚或貶抑者,去事實稍遠;《新唐書》因《舊唐書》所記事實不詳備,多採此等筆記。但司馬溫公作《通鑑》,對於此等事實,必由各方面搜羅證據,見有可疑者即刪去,可見作史是極慎重將事的。最和現代小說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遺事》;彼記宋徽宗遊李師師家,寫得非常生動,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約《水滸傳》即脫胎於此書。古書中全屬虛構者也非沒有,但多專說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輯《太平廣記》之類;這與《聊齋誌異》相當,非《水滸傳》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採取。所以正史中,雖有些敘事很生動的地方,但決與小說傳奇不同。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國學概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8 |
文學 |
$ 225 |
小說/文學 |
$ 232 |
中文書 |
$ 233 |
高等教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國學概論
本書為章太炎先生民國十一年四~六月間在上海市講授國學的集結,全書將國學有系統的分成經學、哲學、文學三種派別論述,深入淺出、條理清晰,可作為中國經學、哲學、文學的簡史,是中文系學子和喜好中國經典學術者不可或缺的書籍。
書末另附有〈白話與文言之關係〉、〈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論讀經有害而無弊〉、〈再釋讀經之異議〉四篇講稿,可供讀者參照。
大師最精彩的國學必修課
本書為章太炎先生民國十一年四~六月間在上海市講授國學的集結,藉著演講,有系統地將國學分成經學、哲學、文學進行闡述,其中含有不少真知灼見,從本書可有系統的認識中國經學、哲學、文學的發展,亦可窺見章太炎深厚的國學底子。
作者簡介:
章太炎(1869~1936)
原名學乘,字枚叔;因仰慕顧炎武的為人處事,曾改名為絳;後又更名為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政論家、學者。章太炎精研國學,尤其擅長於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對中國古籍研讀至深,有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創見。胡適稱:「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梁啟超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魯迅則稱:「章太炎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有學問的革命家』。」其著作甚多,包括《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國故論衡》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概 論
我在東京曾講演過一次國學,在北京也講演過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國學很不容易講,有的也實在不能講,必須自己用心去讀去看。即如歷史,本是不能講的,古人已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現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鑑》等書似乎稍簡要一點,但還是不能講;如果只像說大書那般鋪排些事實,或講些事實夾些論斷,也沒甚意義。所以這些書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講國學,只能指示些門徑和矯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國學概論」分做兩部研究:一、國學之本體。二、治國學之方法。
一、國學之本體
...
我在東京曾講演過一次國學,在北京也講演過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國學很不容易講,有的也實在不能講,必須自己用心去讀去看。即如歷史,本是不能講的,古人已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現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鑑》等書似乎稍簡要一點,但還是不能講;如果只像說大書那般鋪排些事實,或講些事實夾些論斷,也沒甚意義。所以這些書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講國學,只能指示些門徑和矯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國學概論」分做兩部研究:一、國學之本體。二、治國學之方法。
一、國學之本體
...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概論
一、國學之本體
二、治國學之方法
第二章 國學的派別──經學之派別
一、今古文家之分
二、南北學之分
三、漢宋學之分
第三章 國學的派別──哲學之派別
一、先秦諸子之哲理
二、魏晉隋唐間之玄學與佛法
三、兩宋理學
四、明代王學
五、各時代哲學之比較
第四章 國學之派別──文學之派別
一、散文之體制
二、散文之流變
三、有韻文(詩)之體制
第五章 國學之進步
一、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
二、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
三、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
附 錄
一...
一、國學之本體
二、治國學之方法
第二章 國學的派別──經學之派別
一、今古文家之分
二、南北學之分
三、漢宋學之分
第三章 國學的派別──哲學之派別
一、先秦諸子之哲理
二、魏晉隋唐間之玄學與佛法
三、兩宋理學
四、明代王學
五、各時代哲學之比較
第四章 國學之派別──文學之派別
一、散文之體制
二、散文之流變
三、有韻文(詩)之體制
第五章 國學之進步
一、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
二、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
三、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
附 錄
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25 ISBN/ISSN:97895711747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