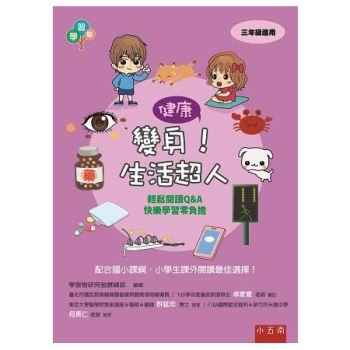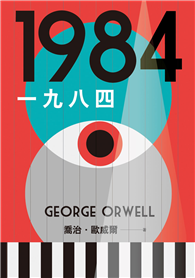十九世紀以來,全球性民主化潮流有三波,從1974年葡萄牙政變開始以迄目前,即屬第三波的範疇。
此一波民主革命帶動三十多個國家進行政治變革,從威權轉型到民主,這可能是本世紀晚期最重要的政治趨勢。
國際政治學巨擘杭廷頓教授深入淺出地分析了這些民主轉型的原因、性質、方式及其直接影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對中華民國台灣有很高的評價,因為只有中華民國在民主化進程中,還能夠維持經濟發展與安定。
因此「台灣經驗」有其優越的地方,可資其他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大陸)政經改革參考。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第三波:20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的圖書 |
 |
第三波:20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作者:塞繆爾.杭廷頓 / 譯者:劉軍寧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2-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315 |
政治概論 |
$ 315 |
社會人文 |
$ 332 |
中文書 |
$ 333 |
高等教育 |
$ 333 |
政治/法律/軍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目錄
第一章 內容
第一節 第三波的開始
第二節 民主的含義
第三節 歷史上的民主化浪潮
第四節 民主化的問題
第二章 原因
第一節 波浪式運動探因
第二節 民主化波浪探因
第三節 第三波探因
第四節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和政績的困局
第五節 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
第六節 宗教變遷
第七節 外來勢力的新政策
第八節 示範效應或滾雪球
第九節 從肇因到肇端
第三章 方式--民主化的過程
第一節 威權政權
第二節 轉型過程
第三節 變革
第四節 置換
第五節 移轉
第四章 進行--民主化的特徵
第一節 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徵
第二節 妥協、參與與適度交易
第三節 選舉結果:預料之外,還是情理之中
第四節 低度的暴力
第五章 持久
第一節 鞏固權力及其問題
第二節 用刑者的難題:法辦與懲治,還是寬恕與遺忘
第三節 執政官式的難題:三心兩意而又強大的軍方
第四節 情境問題、幻滅與威權懷舊
第五節 民主政治文化的培養
第六節 民主政治行為的制度化
第七節 有利於新民主國家鞏固的條件
第六章 走向
第一節 第三波肇因:持續、削弱還是有所變化?
第二節 第三波回潮?
第三節 進一步的民主化:障礙與機會
第四節 經濟發展與政治領導
序
序言
本書探討的是二十世紀後期一項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全球政治發展:即大約有三十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轉型到民主政治體制。這本書致力於說明發生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年間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影響。
本書橫跨理論和歷史兩個領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論著作,也不是一部史書。它位於兩者之間;它基本上是一部說明性的專著。一項好的理論不僅精確、嚴謹、優美,而又能凸顯出若干概念變項間的關係。然而沒有一項理論能夠全面地解釋一個單一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相形之下,一項說明則難免龐雜、膚淺、拖泥帶水,而且思想上不令人滿意。一部說明性的專著,其成功的秘訣不在於嚴謹,而在於全面。
一部好的歷史書則按照編年史的方式來描述、並令人信服地分析一連串事件,同時指出為什麼一起事件導致另一起事件。本研究也不作那樣的工作。它不去詳細刻劃在七○年代和八○年代間民主化的一般過程,也不去描述個別國家的民主化情況,而是試圖解釋並分析一群特定的國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的轉型情況。用社會科學的術語說,本研究既非是通則性,也非是細則性的。理論家和史學家都很可能因此發現本書不令人滿意,因為它沒有提供前者所青睞的概括,也沒有提供後者所偏愛的深刻。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完全不同於我的前幾部著作。在其他那些著作中,我試圖發展出一套關於關鍵變項間關係的概括和理論,諸如政治權力與軍隊職業制、政治參與與政治制度化、政治理想與政治行為,這些關於它們之間關係的命題通常是作為超越時間界限的真理而提出來的。不過,在本書中,我的概括僅限於發生在七○年代和八○年代間的一組不連續的事件。的確,本書的一個重點是要說明第三波民主化與前兩波民主化的差異。
在撰寫本書時,我禁不住地想要提出一些超越時間界限的深刻真理,諸如,「置換過程比變革過程更充滿暴力」。可是當時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已,我的證據只來自於我所研究的有限的歷史事件,而且我在撰寫的是一部解釋性的、而非理論性的著作。所以我必須徹底放棄沒有時間界限的現在時態,而用過去時態來描述:「置換過程在當時比變革過程更充滿暴力」。
除在極少數的幾個例外情況下,我都是這樣做的。在某些場合,命題的普遍性似乎如此明晰,以至我擋不住地要用更沒有時間界限的語彙來陳述。此外,幾乎沒有一項命題能夠適用於第三波的所有情況。因此,讀者們會發現,像「趨向於」、「通常」、「幾乎總是」這樣的字眼和其他一些同類的修飾詞經常出現在通篇的正文之中。根據我最後採行的表達方式,上面所例舉的命題應該讀成,「當時,置換過程通常比變革過程更充滿暴力」。
本書寫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間,當時我所關心的那些事件還在發展中。因此,本書碰到了同時發生性 (contemporaneity) 帶來的所有問題,故本書必須被當作對這些政權轉型的一個初步性的評估和說明。本書引證了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其他學者的著作,他們就特定的專題撰寫了詳細的專論。本書也多方面地依賴對於這些事件的新聞報導。只有在第三波民主化告一段落時,才有可能對這一現象作更全面和更令人滿意的解釋。
我以前對政治變遷的研究,即《變遷中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把重點放在政治穩定的問題上。我寫的那本書是因為我認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要發展一項通則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能否實現穩定的原因、方式和條件。現在,本書的重點是放在民主化上。我撰寫本書是因為我相信民主政治本身是好東西,而且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所主張的那樣,它對個人的自由、國內的穩定、國際的和平和美國均有正面的影響。
正如同在《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一書中一樣,我試圖使我的分析盡可能地獨立於我的價值觀;至少在本書百分之九十五的篇幅上是如此。不過,對我來說,偶爾明確地表達我的分析對那些希望在其社會中實現民主化的人士所具有的意義也是十分有用的。因此,在本書中有五處,我放棄了社會科學家的角色,而擔當了政治顧問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條「民主人士指南」。如果這使我像一個胸懷大志的民主的馬基維利,那也無所謂啦。
促成我撰寫這部書的直接因素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被邀請去俄克拉荷馬大學擔任羅斯鮑姆講座 (Julian J. Rothbaum Lectures)。在這些講座中,我提出了本書的主要論題,當然那時還沒有經驗證據來支持這些論題。本書的大部分手稿寫成於一九八九年底和一九九○年,而且我並未試圖在我的分析中納入發生在一九九○年之後的任何一件事件。
我非常感謝艾伯特國會研究中心 (Carl Alber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與俄克拉荷馬大學研究中心及其主任彼得斯博士 (Dr. Ronald Peters),邀請我前去擔任這些講座。我的妻子南施和我想要在此說明,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在俄克拉荷馬大學受到彼得斯博士和兩位羅斯鮑姆 (Julian & Irene Rothbaum) 和揚克夫斯基 (Joel Jankowsky) 以及眾議院議長艾伯特夫婦對我們倆始終如一禮遇和款待。
儘管講座邀請促成了我撰寫本書,但是書中的素材卻在我心中醞釀了一段時間。在手稿中有好幾處我是取自於以前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會有更多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嗎?〉(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cy)(《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Summer 1984」,第191-218頁)和〈民主的適切含義〉(The Modest Meaning of Democracy) 載於《美洲的民主:停止擺盪》(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Robert A. Pastor編,紐約,一九八九年,11-28頁)。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年間,奧林以民主與發展研究員身份 (John M. Olin Fellowship i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使我得以花更多的時間如努力來研究本書的主題。
還有許多人直接間接地對這部手稿貢獻良多。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我一直在哈佛大學基礎課程中教授現代民主,這門課的重點是民主轉型問題。學生和助教們都會發現,本書中的許多內容取材自這門課;我對這個主題上的一些想法由於他們的評論和批評而得到了很大的改進。
基拉蕊 (Mary Kiraly)、李永洙 (Young Jo Lee)、馬基奧羅 (Kevin Marchioro) 和波森 (Adam Posen) 在研究書中的素材和整理我在這一課題上的檔案資料時提供了絕對必要的幫助。辛巴羅 (Jeffrey Cimbalo) 不僅完成了這些任務,而且還在這部手稿的最後準備階段特別特別認真地校閱了正文和注釋。布萊克特 (Juliet Blackett) 和英格爾哈特 (Amy Englehardt) 把他們非常卓越的文書處理技巧運用於這份手稿上,有效、迅速而且準確地打印出了許多草稿,以及不斷地進行修訂。
我的幾位同事,雪哈比 (Houchang Chehabi)、考爾 (Edwin Corr)、多明格斯 (Jorge Dominguez)、哈格比安 (Frances Hagopian)、諾林格 (Eric Nordlinger) 和史密斯 (Tony Smith),閱讀了我的這部手稿的部分或全部。剛才提到的這幾個人提供了富有思想的、而且很有批判性和建設性的書面評論。哈佛大學比較政治討論組的幾位成員也透過活潑的討論對我的手稿的前半部提出了很多意見。
我非常感激上述人士對我的著作抱有興趣,也感激他們對改進本書的品質所作的實質貢獻。不過,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中的論點、論據和錯誤均由我來負責。
塞繆爾.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劍橋 麻薩諸塞州 一九九一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