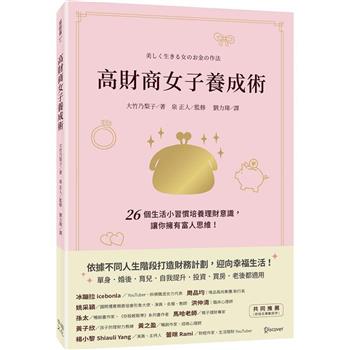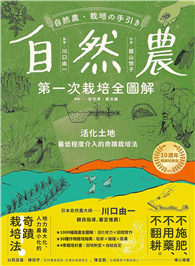第一章 從社會工作歷史人物學習典範
前言
一部社會工作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歐美社會福利史,或福利國家發展史的縮影。如果沒有社會福利的發展,幾乎可以斷定不會有今日社會工作的出現。誠如美國社會福歷史學者川特諾(Trattner, 1999: 1)所言:「任何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信條與方案反映了該社會的系統功能運作的價值。如同其他社會制度的出現一般,社會福利體系不可能憑空冒出,必然從習俗、法規與過去的實踐中找到其血脈。」另一位社會福利史學者賴比(Leiby, 1978: 6)也說:「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與發展必然回應了某種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環境,且被此環境所形塑。」一般論者都會說:「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是為了回應社會問題。」(Karger & Stoesz, 2006),更精準地說是:「回應十九世紀工業化下的都市生活問題」(Leiby, 1978: 2)。亦即,貧窮、失業與勞工集中到城市之後衍生的居住問題。
然而,不同的學者對史料的運用與分析會因觀點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以繆瑞(Charles Murray)的《根基鬆動》(Losing Ground)(1984)為例,他分析一對未婚但懷孕了的年輕夫婦哈洛德與斐莉絲(Harold and Phyllis)的生活經驗,驟下結論認為,由於1970年代的美國擁有慷慨的社會福利方案,例如:有依賴兒童的家庭補助(AFDC)、公共住宅、醫療補助(Medicaid)、食物券(food stamp)等,導致這對年輕夫妻選擇不結婚、不工作而可以過活。這種情形在1960年代比較不可能發生。故繆瑞的觀察結論是:「慷慨的社會福利方案使人們理性地選擇不結婚與不就業。」(Murray, 1984)
這樣的分析結論得到同是保守主義的學者的贊同。但是,其他學者則批評繆瑞的結論犯了嚴重的歷史方法論謬誤。首先,僅用少數資料就通則化歷史事實,犯了過度概化(overgernalization)的謬誤。其次,誤用資料,因為1960至1970年代增加的社會福利預算是給老人福利用得多,不是上述的那些福利方案。第三,繆瑞將複雜的歷史當成一件事(one thing)來看待,化約了歷史事件,忽略了多種影響貧窮與失業的因素。例如:職業結構轉變、失業率升高等(Popple & Leighninger, 2008)。據此,了解不同的社會福利史觀是重要的,讓讀者清楚從哪個角度觀看歷史事件與人物。
壹、社會福利史觀
對歐洲的社會福利發展的觀察,會因為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英國社會福利史學者佛拉瑟(Fraser, 2009)將不同的史觀整理成八個派別,介紹如下:
一、輝格模式(the Whig Model)
「輝格」(Whigs)的名稱是「Whiggamores」(意為「好鬥的蘇格蘭長老會派教徒」)乙詞的縮寫。1679年,因約克公爵詹姆斯(James II,後來的詹姆斯二世,查理一世的次子)具有天主教背景與親法國理念,就詹姆斯是否有權繼承王位的問題,英格蘭議會展開激烈的爭論。一批議員反對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繼承權,被政敵托利黨(the Tories)譏稱為「輝格」。輝格黨人得利於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詹姆斯二世被驅逐,喪失其作為史上羅馬教皇最後一位加冕的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國王。輝格黨人的基本主張是君主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 monarchism)。其於1715至1760年間長期支配英國政治,史稱輝格霸權(Whig Supremacy)。
輝格黨人起初只是一群鬆散的君主立憲主義者,到了1784年,其領導人法克斯(Charles James Fox)為了對抗對手執政的托利黨年輕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83年以二十四歲青年當上首相)而組成較嚴密的政黨。當時,兩黨的組成份子都是富裕的政治世家,而非公民普選的議員。工業革命後,輝格黨支持新浮現的工業利益階級與富商。而其對手托利黨則繼續支持地主與貴族家族。直到1834年,托利黨才轉型成為今日的英國保守黨(the Conservatives),其主要受到皮爾(Robert Peel)的影響。1834年英國國王威廉四世(King William IV)更換屬於輝格黨的梅爾本(Lord Melbourne)首相,而擬任命屬於老托利(old Tory)的威靈頓公爵(Duke Wellington)續任,威靈頓公爵志不在此,於是推薦皮爾。皮爾發表談我思宣言(Tamworth Manifesto),主張在保守良善之餘,改革陋規(reforming ills while conserving the good)的保守主義哲學。從此,保守黨取代托利黨的稱號。1846年因為自由貿易法案,保守黨一分為二。保護主義派(the protectionist)拒絕稱自己為保守黨人,而自稱是保護主義者(Protectionists),甚至希望恢復托利黨名。1859年,皮爾派(The Peelites)脫離保守黨加入輝格黨與基變派(The Radicals),組成自由黨。而留在保守黨的人馬,繼續使用保守黨名迄今。同時,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輝格黨不只支持議會政治、工會,也支持天主教解放運動、解放奴隸,以及普及的公民投票權。
1859年輝格黨在格拉史東(William Gladstone)帶領下改名自由黨(the Liberal Party),吸納了部分輝格黨人、自由工會支持者,以及保守黨的皮爾派等。當時,其信仰是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主張自由貿易、減少政府介入經濟,史稱葛拉史東派自由主義(Gladstonian Liberalism);同時,自由黨主張社會改革、個人自由、削減皇室權力、降低英國教會干預、擴大公民投票權等。
1880年代後,自由黨注入新的價值,亦即現代的、進步的、新的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也就是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主張個人自由與國家介入保障個人基本福利並不衝突。於是,就出現了二十世紀初到1920年代間的自由主義改革(Liberal Reforms),特別是從1908年阿斯奎斯(Herbert H. Asquith)擔任首相,到1916年喬治(Lloyd George)繼任首相,再到自由黨衰退的1922年間,建立了當今英國福利國家的基礎架構。
1929年以後,自由黨幾乎完全被1900年新成立的工黨(The Labour Party)所取代,落後成為英國第三大黨。1981年與新成立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組成社會民主自由聯盟。1988年兩黨合併成為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迄今,一直是英國的第三大黨。
立基於輝格黨的傳統,輝格史觀就出現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他們相信自己擁有幾近完美的自由憲政理念;也認為歷史的演進是因具有前瞻性的人民施壓與發展而出現;同時,也相信評估過去歷史的進步必須與現代經驗關聯。據此,他們認為歐洲社會政策的發展是一條從知識的黑暗時期進步到啟蒙的路徑。當一個社會更敏感於社會需求時,自由市場經濟就會被限縮,同情與關懷弱勢者與差異者的心態油然而生,進步改革的力量就上臺了。輝格史觀滿足了1948年以降英國福利國家發展的解釋期待,讓英國福利國家的發展找到一條可以往前推演的路徑。也就是英國今天之所以會發展福利國家是因為過去一脈相承的歷史演進。
然而,輝格史觀有其詮釋的風險,因為,觀察家很容易將過去的經驗以現在的概念來理解,陷入一種「現在─過去」的對話(present-past dialogue)陷阱,以今日的道德標準來衡量過去的經驗,而忽略過去的事實。
二、務實模式(the Pragmatic Model)
務實模式的史觀解釋今日的社會政策不是以今非古,而是承認今古之間有其差異。過去雖可能是同一個國家,例如:同是英國,卻是不同的朝代,甚至不一樣的地理範圍與政治制度。不必以今日的經驗來看待過去的事實。從這個角度出發,當代社會政策只不過是工業革命以降,一連串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過程而已。據此,社會政策是為此而產生的(ad hoc)、且非計畫的;是漸進的、非基變的;是不規律的,非直線的。這樣的史觀在意的是社會政策發生的當下歷史與政治脈絡,強調實務而非理論,注意短期決策而非長期政策演進。當然,就沒有提供任何空間給人道主義者或社會改革家來引領社會政策的創新,而是看到政客們如何來宣傳與定義當時的社會問題。當人們被說服當下的社會問題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了,政府必須做出回應,社會政策於焉出現。當然,務實觀點看到的社會問題也不見得是完整的。
三、官僚模式(the Bureaucratic Model)
官僚模式認為不論是人道主義者倡議,或是務實的政治需要,政府都必須靠官僚體系的作為,始能讓社會政策實現。因為人道主義倡議者很快會從政策過程的螢幕中消失;而社會問題不會自動轉換成為社會政策,必須靠一群官僚體制的專家,才能將人道理念與社會問題轉換成為政策。社會政策的實現涉及社會立法與行政過程,因此,了解福利體制的官僚作為是理解社會政策之所以出爐的重要面向。不論是地方層級或是中央層級,政府的文官體制已納入許多不同專業與專家,他們獨立於政治與大眾利益的壓力之外,依其專業判斷,設定目標,推動社會政策,以因應社會變遷,滿足人民所需。據此,欲了解社會福利史,必先了解在行政體系中的官僚作為,了解他們如何發起、完成、執行新的社會政策。這是從歷史學的(historiographical)角度來了解官僚在社會政策制訂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官方檔案就成為研究社會政策很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亦即,官僚制度、官僚活動、官員心智(officer mentality)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的重要參考。問題就是官員心智如何被知悉?很多官僚對社會政策的想法不見得會留下正式紀錄,很多官方檔案未完全記錄下官僚的檯面下活動。
四、意識形態模式(the Ideological Model)
不論是務實觀點或是官僚模式,都低估在社會政策創新中理念(ideas)的重要。沒有社會福利的理念,社會問題如何能自動成為解決的方案?官僚如何能設定政策目標?了解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態度,以及在當代知識脈絡下政策發展的空間,才是了解社會福利史的核心。意識形態觀點將社會政策發展扣緊整個時代普遍的文化氛圍。知識脈絡會正當化社會政策的出現與發展。例如,工業革命之後,追求現代化(modernisation)成為支撐社會福利制度的意識形態基礎;反之,1795年的史賓漢蘭制(Speenhamland System),受挫於放任自由主義(Laissez-faire);而政府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助長二次戰後福利國家的發展。然而,困難在如何能知曉這些理念與價值是真正影響到社會政策的制訂?
五、陰謀論(the Conspiratorial Model)
意識形態的批判者認為意識形態是反映該社會優勢階級的價值。因此,政策必然服膺於當代的意識形態,粉飾優勢階級的利益與合理化其價值。據此觀點,社會政策是為了實現某些社會與政治目的產物。社會福利不是為慈善而存在,是資產階級為了控制社會的陰謀手段。陰謀論為批判論者與結構主義學者所偏好,例如,傅科(Michael Foucault)對中世紀以來歐洲大量興建救濟院、收容所、習藝所等機構的批判,認為那是統治者淨化社會、控制人民行為的手段,讓瘋子安靜、工人工作、學童學習、病人被規制。
六、資本主義模式(the Capitalistic Model)
資本主義模式的史觀認為福利的倫理與資本主義倫理本質上是對立的。社會福利之所以出現是資本家為了鞏固自己在現代化社會中的經濟利益,而必須付出的工業化社會成本;同時,藉此促進社會組織來創造其商業利益。這個觀點認為只要是工業社會必然會走向福利資本主義。這是一種聚合論(convergence theory),假設在進步的工業社會裡,勞工福利的提供是為了穩定勞工家庭;教育的普及是為了供給工業社會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健康照顧的提供是為了儲備健康的勞動力以供應生產所需;社會福利就成為促進國家效能(national efficiency)的必要手段。
七、民主模式(the Democratic Model)
民主模式認為社會福利是反映民主社會選民的需求。工人階級意識形態發展、工會組織制度化使工人更加團結。當工人擁有投票權之後,政府必須針對工人的需求提供相對應的福利。普及的投票權使窮人也可以成為社會政策的行動者,藉由其手中的選票讓自己進入政治舞臺。據此,當工人支持的政黨經由民主選舉獲得執政機會後,更多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福利方案亦隨之推出。循此,假設福利國家的出現必須植基於民主政治與社會自由。
八、混合經濟模式(the Mixed Economy Model)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福利國家的發展反映了國家、志願部門、家庭與市場間的互動過程。任何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都不可能單獨由任何一個機制來提供,而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上,不同的福利提供系統扮演的角色不同。不同時期的社會風險籃子(social risk basket)裝著不同的風險,必須由不同的機制來滿足。而一部社會福利史就是這些福利提供機制間不同組合的過程。某些時候非正式或志願部門扮演主要的福利提供角色;反之,國家或市場扮演較主導的位置。
至此,我們相信沒有任一單一理論或觀點可以解釋歐美國家社會福利的發展。如果單純地以為工業革命就自動地創造出英國的福利國家,也未免簡化了社會福利出現的複雜過程。然而,沒有工業革命,的確很難想像會有現代福利國家的出現。同樣地,基於英國輝格黨以來的自由與進步主張而認定其是創建英國社會政策的主要推手,也是過於一廂情願。輝格黨與後繼的自由黨,不見得意識到推動普及的投票權會使自己的政黨泡沫化,而被工黨取代。同樣地,若相信剛完成德國統一的俾斯麥首相是有意要促成德國社會保險的發展,也是高估了俾斯麥的善意。而同是英國君主立憲下的官僚體制,何以會在不同的時期創造出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確,資本階級為了經濟利益,容忍有限度的社會福利出現,可是卻無法有計畫地限制福利國家的發展。中產階級為了穩定社會而推動社會福利,也無法如預期地引導社會福利的發展方向。同是民主國家,卻發展出極其不同的社會福利體系。
本書不擬確證這些觀點的孰是孰非,也不擬針對特定史觀發展論述,而是努力在複雜的歷史事件中,尋找誰在該時期,針對特定的社會議題提出理念、採取行動,影響該社會議題被轉換成為社會政策。但也不敢相信單憑任何一位先知或英明的社會改革者就可以扭轉乾坤,創造歷史。只是,我們相信沒有這些人物的倡導,某些社會議題必然會被延宕或甚至在滔滔歷史洪流中被淹沒,而遭遺忘。
為了讓這些社會工作的前輩們的身影突顯,不可避免地須要將該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交代清楚,否則會過度突出這些人物的個人特質。不過,我們也相信這些人物若無過人之處,斷難在那個政治尚未充分民主、資訊尚未流通無阻、人權尚未獲得確切的保障,甚至女性的地位仍然偏低的情境下,可以勇敢地挑戰既定的社會規範,對抗不利於弱勢者的社會結構,成就讓後世景仰的功績。
貳、從工業革命到慈善組織會社
研究當代社會工作發展的學者莫不相信專業化在工業化的美國是不可避免的(Wenocur and Reisch, 1989: 24)。而美國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植根於出現在1870年代的城市志願慈善組織。這些組織無疑地是被兩股勢力所推動:女性主義與基督新教教士。他們的動心起念從博愛到社會控制都有(Wenocur and Reisch, 1989: 25)。這也說明了本書所推崇的社會工作前輩為何以女性偏多的原因。然而,美國的城市慈善組織無疑地傳承自英國1869年的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該組織原名「倫敦有組織的慈善救濟與遏阻行乞會社」(The London Society for Organizing Charitable Relief and Repressing Mendicancy)(Lubove, 1965: 2)。光看這名稱就可以看出其夾雜著慈善與社會控制的目的。無疑地,英國的慈善組織會社是為了應付工業革命以來,維多利亞盛世(Victorian plenty)衍生的貧窮問題而生(Woodroofe, 1962: 3)。
一、從工業革命到社會改革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維多利亞盛世足以誇耀世人。從1851年的大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到1873年的經濟蕭條期間,英國的人口從一千八百萬增加到二千二百萬;出口總值從七千一百萬英鎊增加到將近二億英鎊;進出英國港口的船隻從1847年的一千四百萬噸增加到1870年的三千六百萬噸。倫敦於是成為世界財政金融的中心(Woodroofe, 1964)。
工業革命不但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改變有密切相關,而且也和社會與政治上層結構的基本變遷有關。前者指涉地主貴族政治(landed aristocracy)的銷蝕與商業寡頭政治(business oligarchy)的崛起;後者則指涉國家在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性(Bailey & Brake, 1975: 2)。對英國來說,工業革命後,家庭手工匠被現代勞工所取代,工人人數增加。但是,失業的貧民與流浪者也增加。
從1832年的皇家委員會的濟貧法調查報告由自由放任經濟學者西尼爾(Nassau Senior)與效用主義者(Utilitarianism)邊沁(Jeremy Bentham)的前任祕書恰維克(Edwin Chadwick)主持,便已是一葉知秋了,宣告1795年以來實施的史賓漢蘭制(Speenhamland System)的終結。西尼爾認為「津貼制度減除了人們對飢餓的恐懼,然而飢餓使人們保持勤勉」,其說法就像後人質疑「福利國家使我們軟弱」一般(Fraser, 2009: 53)。1834年實施的「新濟貧法」(New Poor Law)並沒有解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工人淪落為貧民的大有人在,新聞媒體不斷地報導貧民救濟的捐款請求,一些新的濟貧機構也陸續設立,特別是1860年代的商業危機,倫敦的教堂、慈善機構忙碌異常。然而,私人的慈善機構也被批評浪費資源。
「新濟貧法」的修正使英國的濟貧工作又回到1601年舊濟貧法時代較嚴苛的濟貧原則。令人驚訝的是,新濟貧法無視英國已經工業化,貧民因失業或景氣不佳所造成的多於早年因個人因素所造成的。為強化新濟貧法的精神,1852年英國又通過「院外救濟規制令」來執行「較少合格原則」(less eligibility)。較少合格原則是依恰維克的邏輯,如果貧民階級的生活高於勞工階級,勞工就會想盡辦法擠進貧民階級;反之,成為貧民之後的處境越嚴峻,貧民就會成為勤勉的勞工(Fraser, 2009)。亦即貧民救濟金必須低於最窮的工人所能賺到的薪資。就是窮人必須生活在工作窮人的生活水準之下(Kirst-Ashman, 2007)。因此,習藝所簡直就像十九世紀法國的巴士底監獄(Bastille)一樣的不人道(Fraser, 2009)。
「新濟貧法」的實施看似使窮人減少,1834年英國有一百二十六萬窮人(8.8%),1890年只剩下八十萬(2.5%)。事實如此嗎?其實貧窮現象是社會建構的,只要合格標準越低,窮人就越少(Rose, 1986)。
雖然,英國於1833年也通過了「工廠法」(the Factory Act),解決了童工、女工的工時問題。但是,失業與貧窮問題仍然存在。只要生意興隆,雇主就會讓工人夜以繼日地工作,生意清淡時,他們毫不遲疑地拋棄工人。如此,工廠門口永遠有一群失業的工人在等著找工作,即使對有工作的工人來說,低廉的薪資仍不足以餬口。廉價的勞力支撐了英國十九世紀空前的經濟繁榮,但也引發了社會改革的浪潮(Rose, 1986)。有工作不等於脫離貧窮,工作貧窮充斥著十九世紀的英國勞動市場。
因此,工人憤怒了,文學家也看不下去。1838年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出版了《孤雛淚》(Oliver Twist),藉由小說主人翁崔斯特(Oliver Twist)這位小男孩的遭遇來來控訴1837年到1838年間習藝所收容的窮人生活,其悲慘情況令人鼻酸(Fraser, 2009)。當英國的地主與新興中產階級正在享受工業革命成果的當下,恩格斯(Engles, 1845)已經出版了德文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書中揭露了工業城市裡工人生活的貧困面。英國人自己也看出了這種貧富強烈的對比,一篇未署名的作品〈慈善與貧民〉(Charity and Pauperism)刊登於1869年出刊的《週末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道出了社會中不快樂的一面(Woodroofe, 1964: 7)。
工業化社會的英國,工人階級深知自助與互助的重要性。否則在放任自由主義思想主導的維多利亞盛世,很難提升自己的地位與生活品質。例如:週日學校(Sunday school)的辦理,工人將子弟送到週日學校就學。工會也辦理成人教育,例如:機械學校(Mechanics’ Institutes)、實用知識擴散會社(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男性勞工工會(the Working Men’s Union)等組織均扮演鼓勵勞工進修的團體。這些工人的自助與互助是為符合當時主導社會的布爾喬亞價值(Bourgeois value)。因此,大大降低了中產階級對工人的恐懼。因為在當時的托利黨人的眼中,工人形象是「衝動、不知反省、暴力的」,「充斥著貪婪、無知、酗酒、恐嚇的罪惡。」由於許多成人教育來自中產階級的贊助,而使工人與中產階級間的距離逐漸縮小;也由於工人的自我教育,使中產階級相信這是有利於讓工人擁有政治與社會權利的方式(Fraser, 2009)。
為了降低貧窮率與預防傳染病進入中產階級所居住的地區,一些通往貧民窟的道路被切斷,使得東倫敦區(East End)成為被廢棄的地段。由於過度擁擠造成房價上漲,再加上泰晤士河造船工業的沒落與1860年代的馬鈴薯饑荒,使得失業工人與窮人逐漸變得好戰。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社會工作名人傳的圖書 |
 |
社會工作名人傳 作者:林萬億、鄭如君 等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3-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260 |
Others |
$ 342 |
社會人文 |
$ 342 |
社會 |
$ 353 |
中文書 |
$ 353 |
社會人物 |
$ 353 |
Others |
$ 361 |
社會工作 |
$ 361 |
社會工作 |
$ 361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社會工作名人傳
蒐集英國、美國社會工作歷史上13位重要的社會工作開拓與社會改革者,他們不遺餘力的奉獻一生在社會工作裡,消耗自己是為了幫助社會弱勢爭取應有的福利。這13位名人實為社會工作者的最佳典範。
典範學習理論是根據班度拉所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從前人的榜樣中找到可學習的態度及行為,並將之視為模仿學習的對象。
本書特色
本書撰述了13位社會工作名人,包括桃樂斯‧狄克思、梭爾‧阿林斯基、約瑟芬‧巴特勒、奧克塔維雅‧希爾、瑪麗‧芮奇孟等等13位名人,以期讀者能藉由他們的事蹟激勵自己,成為一名優秀的社會工作者。
作者簡介:
林萬億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碩士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福利學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所長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長
臺北縣副縣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從社會工作歷史人物學習典範
前言
一部社會工作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歐美社會福利史,或福利國家發展史的縮影。如果沒有社會福利的發展,幾乎可以斷定不會有今日社會工作的出現。誠如美國社會福歷史學者川特諾(Trattner, 1999: 1)所言:「任何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信條與方案反映了該社會的系統功能運作的價值。如同其他社會制度的出現一般,社會福利體系不可能憑空冒出,必然從習俗、法規與過去的實踐中找到其血脈。」另一位社會福利史學者賴比(Leiby, 1978: 6)也說:「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與發展必然回應了某種社會、...
前言
一部社會工作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歐美社會福利史,或福利國家發展史的縮影。如果沒有社會福利的發展,幾乎可以斷定不會有今日社會工作的出現。誠如美國社會福歷史學者川特諾(Trattner, 1999: 1)所言:「任何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信條與方案反映了該社會的系統功能運作的價值。如同其他社會制度的出現一般,社會福利體系不可能憑空冒出,必然從習俗、法規與過去的實踐中找到其血脈。」另一位社會福利史學者賴比(Leiby, 1978: 6)也說:「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與發展必然回應了某種社會、...
»看全部
目錄
序
第一章 從社會工作歷史人物學習典範
前言
壹、社會福利史觀
貳、從工業革命到慈善組織會社
參、從五月花號公約到獨立宣言
肆、從科學慈善到社會工作專業化
伍、社會工作改革的號角響起
結語
第二章 桃樂絲‧狄克思
前言:自由國的理想夢土
壹、童年生活
貳、邂逅社會工作
參、重要事跡與貢獻
肆、生涯的轉折
伍、社會影響
陸、向前輩致敬
第三章 約瑟芬‧巴特勒
前言:大時代
壹、童年生活
貳、邂逅社會工作
參、向前輩致敬
第四章 奧克塔維雅‧希爾 ...
第一章 從社會工作歷史人物學習典範
前言
壹、社會福利史觀
貳、從工業革命到慈善組織會社
參、從五月花號公約到獨立宣言
肆、從科學慈善到社會工作專業化
伍、社會工作改革的號角響起
結語
第二章 桃樂絲‧狄克思
前言:自由國的理想夢土
壹、童年生活
貳、邂逅社會工作
參、重要事跡與貢獻
肆、生涯的轉折
伍、社會影響
陸、向前輩致敬
第三章 約瑟芬‧巴特勒
前言:大時代
壹、童年生活
貳、邂逅社會工作
參、向前輩致敬
第四章 奧克塔維雅‧希爾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萬億、鄭如君 等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3-26 ISBN/ISSN:978957117511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開數:20K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社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