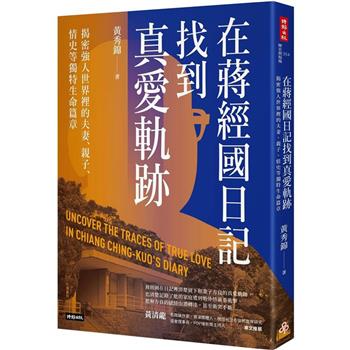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的圖書 |
 |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 作者:王盈勛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4-1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9 |
二手中文書 |
$ 174 |
社會人文 |
$ 198 |
媒體/傳播 |
$ 204 |
中文書 |
$ 205 |
高等教育 |
$ 209 |
大眾傳播 |
$ 209 |
大眾傳播總論 |
$ 209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
內容簡介
傳統領域的經濟分析,過去主要援引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以及新古典主義傳統的產業組織的理論。本書旨在探索,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與理論,如何應用於傳播研究,特別是再傳播史、政策與產業分析等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