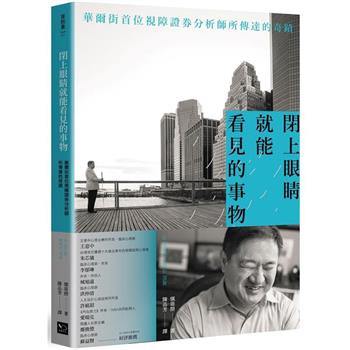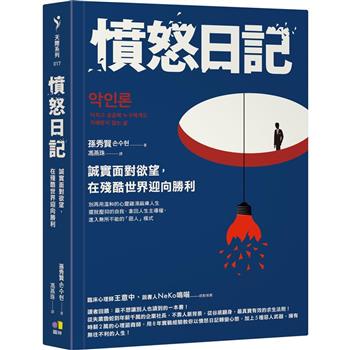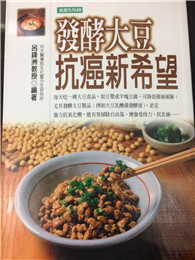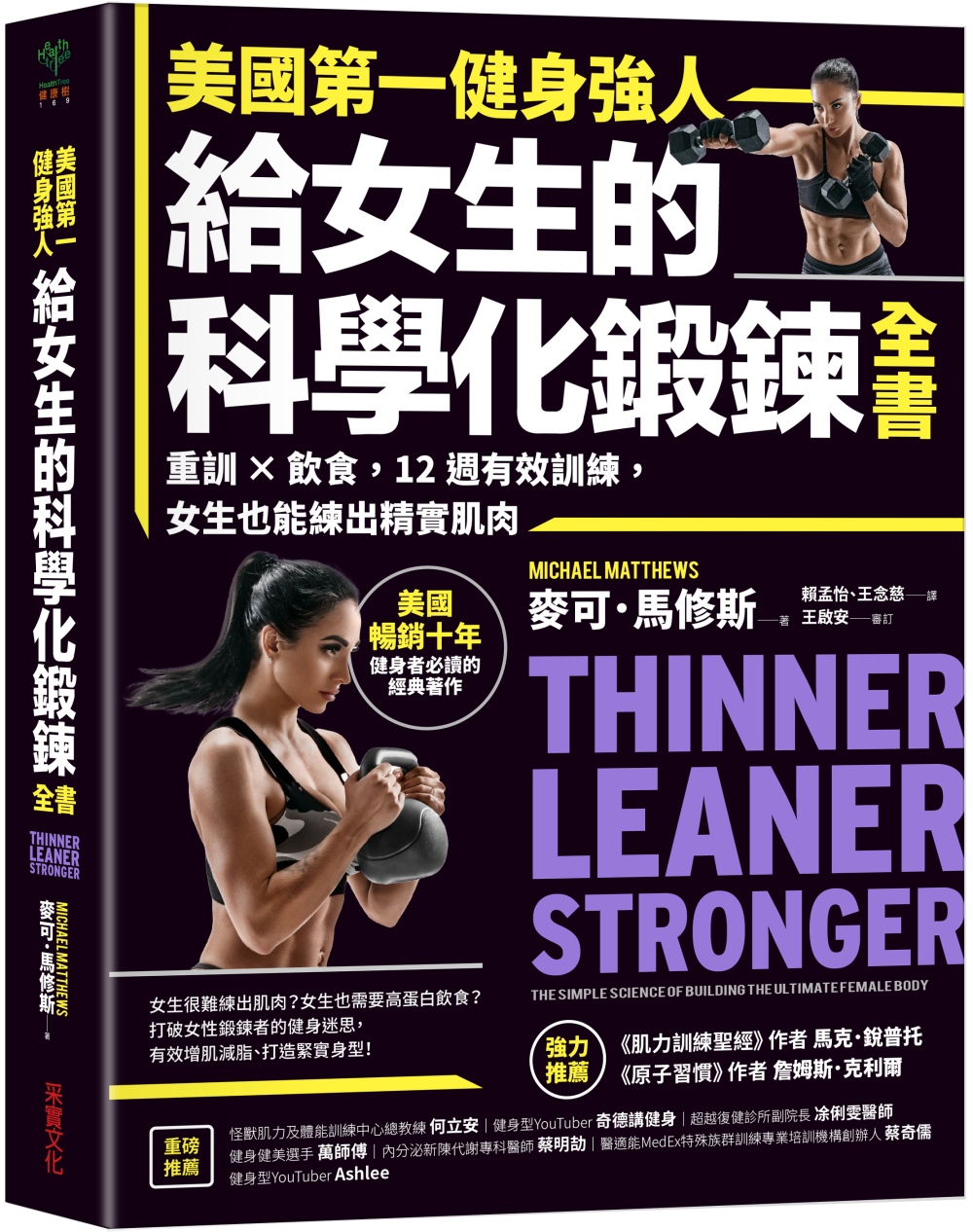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孟軻與《孟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05 |
社會人文 |
$ 405 |
哲學 |
$ 418 |
中文書 |
$ 419 |
高等教育 |
$ 428 |
哲學 |
$ 428 |
儒家思想 |
$ 42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孟軻與《孟子》
內容簡介
以學術性質的研究基礎,做出平實易簡的表達,相較於以往論述《孟子》的方式或有些許不同。第一,陳述「如何理解孟子思想」的建議進路。第二,試圖結合日常生活與某些「道德心理」內容,來嘗試理解孟子的「心性論」。第三,除了對「性善論」做出分析與詮釋,並試圖以平實口吻來強調「性善論」的教育深義。第四,不刻意以孟子的思想為絕對真理,盡可能持平說明孟子思想的合理之處與優劣。第五,簡要談論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並非矛盾,並帶出其中的教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