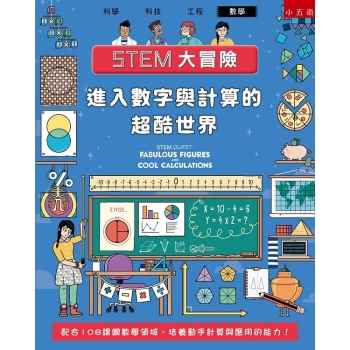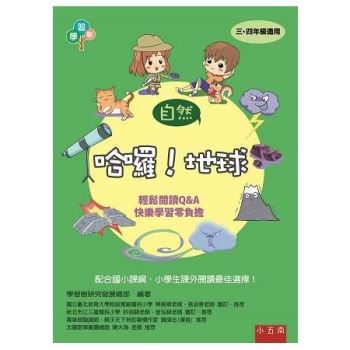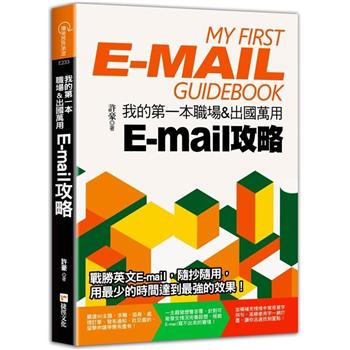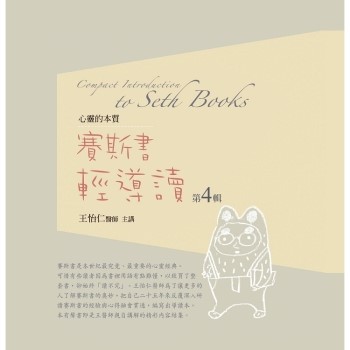屈原,中國文化中一個永遠說不盡的話題。
西元前277年,湖南長沙一帶的汨羅江旁,一位披頭散髮的男子在岸邊徘徊、沉思。他和江邊的漁翁對談,「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翁勸戒他,何必非得把事情看得那麼透徹深刻,何必非得讓自己的言行舉止高潔、何苦與眾不同,以致於為世人不容而被放逐呢?
這人就是屈原,後人提起他時,稱為屈子,認為他和孔子、孟子那些大家一樣,對中國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
屈原帶給人的影響不僅是因為其為愛國思想先驅,其更可稱為浪漫文學始祖,他開創了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體裁──楚辭體,而且代表這一文學體裁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是離騷。此外,他正道直行的信念和精神,早已被自己選擇的最後歸宿證明,在如今,中國法定的傳統節日中,唯有端午節是有明確紀念對象的,就是屈原。儘管學者已經證明,早在屈原生活的時代以前,端午節就是已經存在,但是因為屈原是在五月初五這一天自沉的,所以從此以後,端午節成為人們祭祀、緬懷屈原的節日。
屈原,傳奇的詩人,一生中,經歷過哪些傳奇故事?他對祖國的熱烈到底有什麼動人的傳說?作者在書中做了詳盡的闡述。
本書特色
本書依作者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所做講座的講稿整理潤色而成。
作者簡介:
楊雨,湖南長沙人,文學博士。現任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古代文學專業學科帶頭人。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湖南省首批新世紀121人才工程,湖南省高校青年骨幹教師。中國詞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已出版《我是人間惆悵客——聽楊雨講納蘭》、《宋詞的女性意識》、《傳播學視野下的宋詞生態》、《網路詩歌論》、《莫道不銷魂——楊雨解密李清照》、《俠骨柔情陸放翁——楊雨講述傳奇陸遊》、《唐宋 名士瀟湘情》、《唐宋詞經典——楊雨如是說》等著作,發表論文四十餘篇,主持多項省、部級社科規劃課題,獲多項科研、教學獎勵。自2011年起,在中央電 視台《百家講壇》先後主講「俠骨柔情陸放翁」、「納蘭心事有誰知」、「端午時節話屈原」等系列講座。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狐死首丘——白起破郢,屈子自沉
大約在西元前二七七年的某一天,湖南長沙一帶的汨羅江邊,一位身材瘦長、面容蒼老、臉色灰暗、披頭散髮的男子,在岸邊長時間徘徊、沉思著,看樣子十分落魄潦倒。他有時一邊走一邊高聲吟誦著什麼,有時又停下腳步,朝西北的方向久久地凝望著,花白的長髮被夏天傍晚的風吹得淩亂不堪,他也渾然不覺。眼看著太陽就要西沉,江上瀰漫起薄霧,他似乎還沒有離開的打算。
不遠處有一位打漁的老翁,注意這位男子幾乎整整一天了。漁父收起漁網準備返回,特意繞到男子身邊,上下打量了他好久,忽然眼睛一亮,神色頓時變得恭敬起來,他對著男子深深一拜,拱手問道:「敢問這位先生可是三閭大夫?您怎麼會來到這兒呢?」
男子的沉思被打斷,也拱手回禮道:「在下正是屈平。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沒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我就被流放到了這裡。」
漁父說:「聖人可不應該像您這樣迂腐固執啊!聖人應該能夠適應社會、伸縮自如。既然全天下的人都渾濁,那您為什麼不能混在裡面也一起和稀泥、同流合汙呢?既然別人都昏昏沉沉、大醉不醒,那您為什麼不混在其中連酒帶渣地一起喝他個酩酊大醉呢?先生您為什麼非要把事情看得那麼透徹深刻,為什麼非要讓自己的言行舉止那麼高潔,那麼與眾不同,以至於為世人不容而被放逐呢?」
屈平長歎一聲,回答道:「我聽說,剛洗過頭的人一定要先彈去帽子上的灰塵,再將帽子戴在頭上;剛洗過澡的人一定會先把衣服上的灰塵抖掉,再穿上乾淨的衣服。我怎麼能讓自己乾乾淨淨的身體裹在汙濁不堪的衣服裡面呢?我做不到啊!我寧可投身江水去餵魚,也絕不能讓自己潔淨的身體沾染上世俗的塵埃汙垢!」
漁父聽了,微微一笑,也不再答話,他知道已經不可能再說服屈平。於是,漁父拱手告別,一邊搖著船槳叩著船舷,一邊高聲唱起了楚地流行的歌謠:「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當屈平自認為已經瀕臨絕境、不知該何去何從的時候,漁父的勸告彷彿是為他指出了另外一條出路,他能做得到嗎?
屈平,也就是屈原。「平」是他的名,「原」是字。後人提起他時,總是以字敬稱,稱他為「屈原」,甚至稱他為「屈子」,認為他和孔子、孟子那些大家一樣,對中國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
屈原,出生於湖北的秭歸(今湖北宜昌秭歸縣),根據屈原在他的長篇詩歌〈離騷〉中的自述,他的出生日期非常特別——出生於寅年寅月寅日。「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是歲星也就是木星的別名;貞,是正當的意思;孟,開始;陬則是夏曆正月的意思。因此這兩句詩可以解釋為:歲星恰好在孟春正月晨出東方,庚寅的這一天我降生了。據當代學者推算,屈原應當出生於西元前三四二年夏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也就是楚宣王二十八年己卯。
關於屈原的出生,唯一可以依據的資料就是他自己的這兩句詩,按照不同的計算方法,歷代都有學者對他的出生日期進行推算,結論也有諸多分歧。但有一點目前已經取得了共識:那就是屈原出生於楚宣王後期,主要活動於懷王和頃襄王時期,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屈原具體出生於哪一天雖然還有爭議,但沒有爭議的是,屈原既然自稱「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說明他對自己降生在特別吉祥的日子裡充滿驕傲,也充滿了一種特殊的使命感。因為按照古代的禮法,男子如果生於寅,那就很不一般,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先兆了。
王室後裔
屈原的身分確實不同一般:他是楚國王室的後裔,和楚國的君王本來是同姓的宗親,而且他年紀輕輕就進入了楚國的政壇中心——在他二十出頭、楚懷王當政的時候已經官至左徒。【5】
左徒是一個什麼官呢?當時楚國的官職和中原諸侯國不一樣。楚國的最高官職是令尹,相當於丞相。左徒大約是僅次於令尹的官職,很可能類似於「副相」的職位。
屈原流浪江邊時,漁父稱他為「三閭大夫」,這是因為除了左徒外,屈原還做過「三閭大夫」。這個官職的主要功能,是掌管楚國王室宗族之事,並且還承擔培養王族子弟的教育任務。
既是王室宗親,又是朝廷貴臣的屈原,此時卻也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面臨著艱難而痛苦的抉擇。西元前二七七年,屈原虛歲已經六十六了。歷盡滄桑的他,怎麼會走到如此進退兩難的境地呢?
時間首先要回溯到一年前,也就是西元前二七八年。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讓屈原坎坷的命運雪上加霜。
西元前二七八年,正是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如果將西元前四○三年韓、趙、魏三家瓜分
晉國後接受周天子周威烈王冊命,成為正式的諸侯國,標誌著戰國時代的開始,那麼西元前二七八年,已經是戰國的後期——戰國時期進入到了第一百二十五個年頭,離秦始皇帝統一六國、結束戰國局面的西元前二二一年只有五十七年。
戰國時期的最大特點是戰亂頻繁,同時又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也最為激動人心的時代。七國爭雄、名士縱橫,套用一句廣告詞,這正是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的時代。
到西元前二七八年的時候,七國爭雄的戰國時代行將結束,燕、趙、魏、韓業已衰落,真正的強國實際上只剩下秦、楚、齊三國。這三個諸侯國之中,秦國的軍事力量最為強大,齊國是當仁不讓的文化強國,楚國則是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它幾乎占有整個長江的中下游地區,西起陝西漢中,東到大海,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蘇四省,還有江西的大部分地區,以及陝西、河南、貴州、四川、重慶、廣東、浙江、山東的部分地區,差不多將近今天中國面積的一半了,堪稱地大物博、實力雄厚。
此時的周天子雖然還存在,但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對諸侯國已經完全喪失了控制力,各諸侯國之間的較量早已成為事實上的「國際形勢」變化。三大諸侯國之中,又以秦國和楚國的實力最為強大,甚至當時流傳有「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的說法。
因此,如果說從當時的歷史趨勢來看,中國的統一已經成為必然,而肩負著統一重任、又不乏統一雄心的國家非秦、楚莫屬。俗話說得好,一山容不得二虎,戰國後期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就在兩大強國——秦國和楚國之間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白起破郢
西元前二七八年,對關東六國虎視眈眈的秦國,再次向他最強大的鄰國楚國發起強攻。這次戰役的最高軍事指揮官——秦國的大良造白起率領秦軍大舉南下,進攻楚國。儘管號稱是兩大強國之間的較量,但真正一交手就會發現,楚國在軍事上顯然是外強中乾,秦軍一開始便占據了戰場的主動。秦軍勢如破竹,楚國當時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危若累卵。
其實就在前一年,也就是西元前二七九年,大良造白起就已經率領秦軍連續占領了鄢、鄧兩
座城池(兩地均在今湖北襄陽市境)。鄢、鄧距離郢不過一兩百里路程,可以說是郢都的最後一道屏障。這道屏障的失守,郢都就毫無遮擋地暴露於秦軍的兵鋒之下。
此時的秦國,是當時的第一軍事強國,不僅武器裝備精良,驍勇善戰的士兵橫掃天下,而且賞罰分明,將士無不踴躍衝鋒陷陣,幾乎是所向披靡,「虎狼之國」的威名早已名滿天下。
更重要的是,戰國時期的秦國,一代又一代名將不斷湧現,如:司馬錯、樗里疾,以及白起、蒙驁、王翦、王賁、蒙武……,一時間,將帥之才如群星閃耀。
而率領秦軍進攻楚國的大良造白起,正是秦昭王時期聲威赫赫的一代名將,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白起不但為秦國屢立戰功,他還有一個讓人心驚膽戰的名聲: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如:
秦昭王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斬首二十四萬。
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斬首十三萬。
秦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斬首五萬。
最令人髮指的是秦昭王四十七年,據《史記》記載,長平之戰後,白起坑殺趙國降卒四十五萬人,天下震恐……。
西元前二七八年,正是秦昭王二十九年,這時的白起雖然還不像後來那樣如日中天,但也正是他的聲威逐漸顯赫的時候。可以想像,當白起的大軍兵臨郢都城下的時候,楚國上下是何等驚慌!
郢都,危在旦夕!
楚國,生死攸關!
而有一位楚國人,此時也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候!
這位楚人,正是屈原!
此時的屈原,既不是楚國的王侯將相,也不是朝廷高官,他甚至連楚國的一介平民都算不上,他只是一個被楚王放逐的罪臣,這時正在長江以南流浪。遠離都城、遠離故鄉的他,已經這樣流浪很多年了。
秦楚交戰,白起攻郢勢在必得,即便是早已被排擠在楚國政壇之外的屈原,這一切資訊對他而言也是極其敏感的。他的一生,也因此而走到了痛苦最強烈、思想鬥爭最激烈的時候。
他真希望,現在的他,不是在遠離郢都的地方「閒逛」,眼看著楚國大廈將傾而束手無策;他多麼希望能夠率領楚軍,布陣在白起軍隊的前方,就算是背水一戰,就算是明知敗局已定,也要傾盡全力、傾盡智慧,為楚國做最後的一搏。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不正是屈原的勇氣和膽量嗎?
他不止一次地假想,假定他還在朝廷效力,還能鞍前馬後地為朝廷獻計獻策,而楚王也還像當年一樣對他言聽計從,也許形勢不會像今天這樣:眼睜睜地看著秦國強大,眼睜睜地看著六國衰弱,這其中,包括他的祖國——楚國。
可是,這一切在現在的屈原看來,都只能是假想——儘管當年,他自信完全有可能令楚國政局改觀,重現楚國的輝煌與強大。然而,現在的他,早已喪失了左右楚國政壇的機會。
他,只是一個罪臣。流亡多年,楚王也許早就忘了還有屈原這個人吧?他當年共事的那些同僚、當年教育過的那些王族子弟,也早就忘了還有屈原這個人吧?
但是,他不會忘記,他的一生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忘記楚國,他是用對待愛情、對待愛人般矢志不渝的感情來愛著他的楚國。而且他這個「愛人」——楚國,一度也是那麼愛他、信賴他,儘管後來對他有點反覆無常,到最後甚至還絕情地拋棄了他,但他仍然抱著熱戀時的那份情感,執著地守望著他的「初戀」——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熱戀」。
如今,「愛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從屈原的內心深處而言,他渴望赴湯蹈火地去救她。但他的「愛人」已經不再愛他了,甚至還斷絕了一切能使自己接近她的機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愛人」在生命垂危之際苦苦掙扎,誰能了解他內心如此強烈的痛苦?
屈原,就這樣站在了生命的「懸崖」:進,是萬丈深淵,粉身碎骨;退,他還可以苟活於世,但是那樣的他,剩下的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
白起即將圍攻郢都的消息,將屈原推向了一生矛盾的頂峰,但他的心中還殘留著最後一線希望。
不錯,楚國就像他生生死死唯一眷戀的「愛人」,可是他的「愛人」卻不是僅有他這一位「護花使者」。儘管屈原深信沒有人會比自己對她的愛更強烈、更不顧一切,但為了「愛人」的平安,他還是保留著最後的希望:他的「愛人」身邊圍繞著的那些「護花使者」——那些朝廷重臣,能夠幫助她絕地重生,哪怕只是爭取到一線生機!
屈原,就這樣懷著極度的矛盾和痛苦,佇立在「懸崖」邊上,等待著來自郢都的每一點消息。此時的郢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亂之中,早已看不到了昔日富庶繁華的景象。城裡的老百姓亂成一團,哭的哭,喊的喊,逃的逃,散的散;也有一些死守著多年經營的家,眼巴巴指望楚國的軍隊能夠保護他們的家園。
而老百姓眼巴巴指望的唯一的保護傘——楚國的朝廷,現在也亂成了一鍋粥。
這時的楚王是頃襄王熊橫,生死存亡之際,頃襄王理所當然地寄希望於圍繞在身邊的那些「股肱之臣」。他緊急召集大臣們出謀劃策,希望能夠在最後關頭殺出一條活路來。
可是,平時在他周圍滔滔不絕縱論國際形勢的那些朝廷重臣,那些平日裡侃侃而談好像學富五車的大夫卿相,現在竟然比他還慌亂。這個說:「趕緊向秦國求和吧,我們實在是沒有還手之力了啊!大王您是秦國的女婿,說不定秦王會看在姻親的分上,接受我們的投降,保全郢都啊!」那個說:「別給大王出餿主意了!秦國的狼子野心誰還看不出來?!白起又豈是一個心慈手軟之人?!他們殺起俘虜來可是連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看還是別白費力氣了,不如趁早保護大王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等以後我們休整好了,再把郢都奪回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啊!」
……
這些人在頃襄王耳邊嘰嘰喳喳個不停,你指責我,我嘲笑你,頃襄王頹唐地看著眼前這些晃來晃去的腦袋,看著那些喋喋不休的嘴皮子,心想:這就是我平日裡極度信任的左膀右臂?這就是我平時賞賜無數的股肱大臣?一時間,他失望到了極點,也氣憤到了極點。
正當朝臣們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一向昏聵沒主意的頃襄王,倒好像忽然清醒了。他左右一權衡——戰吧,最近幾場大仗和秦國交手下來都是完敗,朝中幾乎已經沒有可以帶兵打仗的將領了;投降吧,秦王和白起絕對不可能接受;退一萬步講,就算他們答應,投降恐怕也是凶多吉少,父親懷王被秦國拘禁至死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鑒……。想來想去,三十六計還是走為上計!
楚王這一拍板,那些貪生怕死的酒囊飯袋們紛紛高呼「大王英明」,便迅速打點好金銀細軟,帶上寵姬美妾,簇擁著頃襄王和他的後宮妃嬪們,手忙腳亂地連夜逃出了郢都。
當然,君王出逃自然不能說是「逃跑」,他們公之於眾的理由是「遷都」。但無論理由是什麼,總之,事實上,楚王跑了!
楚王棄城而逃的消息不脛而走,國王跑了,留守的楚軍當然不會再為他賣命,老百姓也就失去了最後的庇護。白起攻郢,幾乎沒有遭到什麼有效的抵抗,楚國就這樣丟失了它的都城。
從楚國先祖楚文王熊貲定都郢以來,郢都已歷經二十代君王,又經過楚平王等幾代人的不斷修繕、加固,四百多年的苦心經營,當時已號稱是天下最美麗、最繁華的都城。
白起率秦軍進駐郢都後,將其更名為秦國的南郡,還縱火焚燒了楚先王的陵墓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夷陵區)。僥倖逃脫的郢都百姓一路流亡、哀鴻遍野,一夜之間,繁華都市變成一片廢墟。白起則因為這場大勝而被秦昭王加封為武安君。白起乘勝追擊,又一舉拿下楚國的巫郡和黔中郡,改為秦國治下的黔中郡。
郢都陷落的消息傳來,儘管這個結果應該早在屈原的預料之中,但他還是不敢接受也不忍心接受這樣的結局。他甚至一度希望這個消息只是老百姓因為懼怕秦軍而散布的謠言,或者是秦軍為了動搖民心而散布的流言。正是這殘存的一點希望,讓他流浪的腳步不自覺地迅速邁向郢都的方向。
但是,當他越接近郢都,這最後的一點幻想越趨於破滅。因為不久之後,他就遇到了一批又一批從郢都倉皇逃出來的老百姓,他們一個個衣不蔽體、面色慘痛。
意料之中的結局終於成了無可挽回的現實!屈原淚如雨下,他發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也寫下了著名的詩篇〈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哀郢〉,顧名思義就是哀傷郢都的陷落。其實,讓屈原陷入極度傷心和絕望的,還不僅僅是國都陷落、君王和百姓的流亡,對他而言,可能更痛苦的是,作為楚國人,而且自認為是楚國最堅貞、最勇敢的守護者,眼看著「愛人」遭受慘無人道的蹂躪,自己卻無能為力。他沒有辦法原諒自己,更不應該在「愛人」遭遇滅頂之災後,自己卻還逍遙地苟活於世,就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
在這一刻,屈原下定了決心。
此時的屈原,漂泊到了長沙東北今岳陽地區的汨羅一帶。
第一章
狐死首丘——白起破郢,屈子自沉
大約在西元前二七七年的某一天,湖南長沙一帶的汨羅江邊,一位身材瘦長、面容蒼老、臉色灰暗、披頭散髮的男子,在岸邊長時間徘徊、沉思著,看樣子十分落魄潦倒。他有時一邊走一邊高聲吟誦著什麼,有時又停下腳步,朝西北的方向久久地凝望著,花白的長髮被夏天傍晚的風吹得淩亂不堪,他也渾然不覺。眼看著太陽就要西沉,江上瀰漫起薄霧,他似乎還沒有離開的打算。
不遠處有一位打漁的老翁,注意這位男子幾乎整整一天了。漁父收起漁網準備返回,特意繞到男子身邊,上下打量了他好久,忽然眼睛一...
作者序
自序
屈原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永遠說不盡的話題。
關於屈原及楚辭的評論,鐘嶸在《詩品》中品評五言詩,以追源溯流的方法,從體系上分《國風》、《小雅》、《楚辭》三個源流,而承接「小雅」一脈的只有阮籍一人。按照鐘嶸的評說,李陵是直接《楚辭》的,而班姬、王粲、曹丕又師法李陵,以此勾勒出了五言詩的源流網絡。
李陵的詩因為源出《楚辭》,所以「文多悽愴,怨者之流」,而出於李陵的班姬、王粲、曹丕也分別被鐘嶸評為「怨深文綺」、「發愀愴之詞」、「殊美贍可玩」。由這些師承《楚辭》的詩人的風格逆推上去,《楚辭》的風格大概「怨深文綺」四字可盡,如果再簡單一點,就是「綺怨」兩個字了。
我雖然對於鐘嶸的評判心底下是贊同的,但也總覺得他的結論只能觸及我的思想,卻不能戳中我的情感。對很多問題,往往要情感與思想並舉,才能真正契入到我的內心。以前讀到晉代陸雲說:初讀《楚辭》不甚愛之,但過了幾天再讀,竟讀出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清絕滔滔」之感。從此,《楚辭》在他心裡便有了「文宗」的地位。這與我的閱讀體驗,倒很有幾分相似。
像「清絕滔滔」這樣的話,要說清楚它的意思,注定是不容易的。因為,陸雲不僅點出了「清」的基本元素,而且用「絕」和「滔滔」誇張了清的程度和範圍,這就一下子讓一個元範疇帶上了動態的內涵。但解釋不清,並不妨礙感受的進行。尤其是這個「清」字,簡直是人見人愛的字眼。可是,當得起這個字的人和文,實在是有限。
因為「清」雖是至簡,卻也是至難的事情。
先說詩之「清」。詩常常被視為「清物」。清代的熊士鵬曾說,詩之所以被稱為「清物」,是因為她抗拒「囂而雜」、「昏而濁」、「粗而膚」、「冗而散」,排除了這些雜亂因素,自然就成為純淨之詩境了。宋代的林景熙更認為,天地間只有「正氣不擾」,才能「清氣不渾」。詩歌就應該是這種正氣與清氣化後而成。中國的學者是這樣認為,西方的學者也持相似的觀點。如荷爾德林就認為「作詩乃是最清白無邪的事情」。可見,「清」作為詩歌的一種審美理想,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隔閡,所以懸格甚高。
再說人之「清」。詩歌既然是朗朗乾坤之清氣凝結而成,則「作詩者非鐘夫清氣,弗能為也」。詩歌的這一特質,對詩人之「清」也提出了特別的要求。賀貽孫說「詩家清境最難」,難在何處呢?難就難在詩人之清俊,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清代學者蘇時學就曾說:「世之論詩者,每曰清才多,奇才少,此不然之論也。夫清豈易言哉?孟子論聖人而獨以清許伯夷,則自伯夷之外,其真清者有幾人耶?今言詩之清者,必曰王、孟、韋、柳,然自王、孟、韋、柳之外,其真清者有幾人耶?」
清才之難得,不僅在「清」的懸格高,更在於「清」往往依賴天賦而存。所以清人高延第說,雖然成功的詩歌,並非「清」之一字能窮盡底蘊,但如果沒有氣清,則斷然不能臻於極致之詩境。我很贊同這樣的話。因為詩歌之工可以通過力學而致,而詩人與詩歌的「清」,就不是力學所能至,得乎天的因素顯然是主要的。
我們還是回到屈原的話題。
在我看來,對屈原其人其作的評價雖歷來不一,如司馬遷、劉安與班固對屈原及其楚辭作品的評價就有很大的分歧,但有沒有一種評價能夠立於其中而綰合雙方、消弭矛盾,從而獲得相對一致的意見呢?
這個思考困惑了我很久,但現在我豁然開朗了。這彌合的地方就在一個「清」字了。
屈原在〈漁父〉中曾滿懷激憤地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前者說自己的清白,後者說自己的清醒。在〈惜往日〉一詩中,屈原也反覆陳說自己「心純庬而不泄兮」,而他最痛心的正是「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這個世界失去了「清」,也就失去了光華。屈原一生,都毫不動搖地堅守著這個「清」字,他將生命的歸宿選擇在滔滔的汨羅江裡,也是為了「伏清白以死直兮」。屈原的一生,從生到死,雖然命運多舛,但這個「清」字是寫得正大光明的。
屈原是清白的,當楚國朝廷被群小左右,被利益纏繞,唯有屈原堅守著清白的人格。
屈原是清醒的,當戰國風雲瞬息萬變時,唯有屈原始終堅持著聯齊抗秦的國家策略。
屈原是清傲的,當群凶嚷嚷之時,屈原以孤傲不群,藐視著如螻蟻般的上官之流。
我現在明白,為什麼梁啟超要用「極高寒的理想」與「極熱烈的情感」來概括屈原的為人了。極熱烈的情感源於其天賦的詩人熱情,而極高寒的理想則本於其極窘迫的艱難現實。在我的印象中,屈原彷彿生活在楚國的高空,鳥瞰著世間紛紜的一切,心中洞明,卻無能為力。只有在文學的世界裡,他才能如此不羈地馳騁著想像。
因為「清」,屈原極端地珍惜著自己,不能容忍哪怕是一點點的混濁;因為「清」,屈原的視線時時從紛擾的現實中逸開,在香草美人中尋找自己的生命寄託;因為「清」,屈原為我們留下了洋溢著如此豐盛的思想與人格光輝的詩篇。
在文學批評上極度孤傲的劉勰,為何用「奇文鬱起」這樣的句子來誇讚屈原的偉大?因為「奇文」的背後,支撐著的是屈原岸然不群的傲世人格。陸雲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也不是一個偉大的批評家,但他對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給予的「清絕滔滔」之評,絕對是一個天才式的感悟。嚴羽《滄浪詩話》曾經說學詩的工夫要從上做下,這《楚辭》便是他心目中的「上」,便是他覺得應該朝夕諷詠之「本」。蘇軾說:「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屈原及其作品贏得這樣的讚譽,實在是實至名歸。
我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讀,大體是按照上面的思路進行的。如果從中學關注屈原的作品算起,我已經涵泳其中二十多年了。世事紛紜,滄海桑田,而我對屈原的喜愛從未有過變化。當然,年輪的增長,多少改變著我的思想與情感。我從不奢求無限量地走近屈原,但我的步伐卻一直向著屈原走去。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不願意「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堅守一份心靈的純淨與清澈,該是一件多麼重要而又多麼不易的事情!
「微斯人,吾誰與歸」!屈原生前是寂寞的,但中國文化中的屈原其實從來都不孤獨。
楊雨
二○一三年四月
自序
屈原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永遠說不盡的話題。
關於屈原及楚辭的評論,鐘嶸在《詩品》中品評五言詩,以追源溯流的方法,從體系上分《國風》、《小雅》、《楚辭》三個源流,而承接「小雅」一脈的只有阮籍一人。按照鐘嶸的評說,李陵是直接《楚辭》的,而班姬、王粲、曹丕又師法李陵,以此勾勒出了五言詩的源流網絡。
李陵的詩因為源出《楚辭》,所以「文多悽愴,怨者之流」,而出於李陵的班姬、王粲、曹丕也分別被鐘嶸評為「怨深文綺」、「發愀愴之詞」、「殊美贍可玩」。由這些師承《楚辭》的詩人的風格逆推上去,《楚辭》的風格大概「...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狐死首丘——白起破郢,屈子自沉
第二章 香草美人——文學始祖,浪漫楚騷
第三章 密事載心——秦楚抗衡,屈原變法
第四章 鷙鳥不群——屈原聯齊,六國合縱
第五章 精彩絕豔——《九歌》亮相,屈原成名
第六章 蛾眉遭嫉——攻秦失利,屈原遭讒
第七章 黨人偷樂——張儀使楚,屈原被疏
第八章 靈修數化——懷王絕齊,秦楚交鋒
第九章 驟諫不聽——屈原使齊,張儀欺楚
第十章 美人造怒——懷王善變,屈原被逐
第十一章 上下求索(一)——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第十二章 上下求索(二)——穿越時空,守望故國
第十三章 長夜漫漫——屈原歸朝,懷王客死
第十四章 魂兮歸來——屈原〈招魂〉,生命輓歌
第十五章 光齊日月——屈騷情懷,隔世知音
附錄一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附錄二 劉向《新序‧節士》
後記
主要參考書目
自序
第一章 狐死首丘——白起破郢,屈子自沉
第二章 香草美人——文學始祖,浪漫楚騷
第三章 密事載心——秦楚抗衡,屈原變法
第四章 鷙鳥不群——屈原聯齊,六國合縱
第五章 精彩絕豔——《九歌》亮相,屈原成名
第六章 蛾眉遭嫉——攻秦失利,屈原遭讒
第七章 黨人偷樂——張儀使楚,屈原被疏
第八章 靈修數化——懷王絕齊,秦楚交鋒
第九章 驟諫不聽——屈原使齊,張儀欺楚
第十章 美人造怒——懷王善變,屈原被逐
第十一章 上下求索(一)——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第十二章 上下求索(二)——穿越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