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生平與年代背景
1711年,大衛‧休姆(David Hume)出生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家族世居貝里克郡的寧威爾區(鄰近英格蘭邊界),在地方小有名望,但家境不算特別富裕。根據記錄顯示,家族姓氏原本正確拼寫是Home,蘇格蘭語發音和Hume相同,中文譯音都近似「休姆」([hjum])。但是,當時地方戶政較為鬆散,所以也有部分人家登記為Hoom、Hum,以及許多其他相近寫法的變體字。雖然,早在12世紀,宗親族人就已落戶貝里克郡,但直系祖先則到了15世紀之後,才定居寧威爾區。1713年,休姆兩歲,父親約瑟夫去世,由寡母凱瑟琳獨力撫養他和一兄、一姊。《大衛‧休姆的人生》(The Life of David Hume)傳記作者莫斯納(Ernest Mossner)寫道:
休姆家族在宗教方面,信奉蘇格蘭國教長老教會,在政治方面,則追隨輝格黨,堅定支持1688年光榮革命,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共主聯邦制度,1714年漢諾瓦王朝入主蘇格蘭,並且強烈反對詹姆士黨的各種流派。
(Mossner 1980: 32)
1722年,休姆十一歲,和兄長約翰同時進入愛丁堡大學就讀,這並不代表他特別早慧,因為當時學童多半十一歲上下就進入大學就讀,照現前的學制,約莫就是念中學的年齡。大學核心課程包括:拉丁文、希臘文、邏輯、形上學、自然哲學(亦即物理),另可選修數學和歷史等科目。1726年前後,休姆輟學,這在當時頗為平常,只留下甚少的在校學業記錄。在〈我的人生〉(My Own Life)一文,他只簡略記下「我順利通過教育學普通課程」(1980: 40)。
關於未完成大學學業,他寫道是在家庭經濟壓力下,只好中輟離校投入法律相關職業,並且開始自學法律,這方面的知識,
算是相當紮實……這讓他有機會在1746年受委聘,出任遠征軍的隨行法務參議,再者也讓他在有生之年,陸續撰寫諸多類型的法律文件,以及提供法務專家評論見解。
(Mossner 1980: 55)
雖然,他形容自己「年少篤信教義」,但是在這段年歲前後,他下定決心,和宗教分道揚鑣。箇中緣由或許可從他後來對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說法窺見一班:「我渴望從西塞羅著作,尋找建立美德條目的源泉,而不再取法自幼篤信的宗教讀本《人的完全責任》(Whole Duty of Man)」(1980: 64)。此一階段,堪稱休姆學思能量突飛猛進的時期,到了1729年間,他就已經登上思想洞見初綻的入門峰頂,奠定了日後博大精深哲學體系的基礎。
在大量研讀與反思此一[新材料,藉此可望奠立真理的基礎],終於在我18歲上下的年紀,似乎敞開了思想的新天地,把我轉渡向無可估量的遠方,讓我發諸少年人自然的孺慕之心,毅然決然拋開一切尋歡作樂或其他志業,全心全意貫注其中。法律,我本該認命追尋的志業,似乎只讓我滿心作噁,我無法設想,除了學者和哲學家之外,這世上還有其他我應該去努力追尋的前途。
(Mossner 1980: 65)
1729至34年間,休姆全神貫注探索「思想的新天地」,身心健康大受影響,飽受憂鬱之苦,還染上敗血症之類的生理病症。醫生給他開了偏方,建議每天喝一品特的紅葡萄酒,外加適量運動。後來,休姆自己也歸結,療癒心病的良方就是棄筆從商,暫時擱置嚴肅的學思志業。於是,他前往港滬商城布里斯托,找到一家糖業進口商行,做起營業員的工作。這期間,因為蘇格蘭姓氏「Home」(蘇格蘭發音[hjum])老是被英格蘭人錯念成「霍姆」(英格蘭發音[hom]),讓他不勝其擾,最後索性改寫成「Hume」(蘇格蘭、英格蘭發音同為[hjum]),比較不會被念錯。不過,他這從商之路也沒有維持太久,因為工作的時候,他老愛糾正老闆的文法和書寫風格,有一回,老闆被惹得火冒三丈,當場就把他解僱了。
1734至37年,休姆旅居法國,開始投入寫作《人性論》。其實,他心中理想的居住地點是巴黎,但礙於一年家裡只能給他50英鎊,難以支應當地的生活開銷,退而求其次,只好選擇落腳安茹省的拉弗萊什(La Fleche, Anjou)。除了住宿便宜之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當地有一所相當不錯的耶穌教會學校(Jesuit College),圖書館藏甚為豐富,笛卡兒曾在此就讀。
休姆回到倫敦之後,找了一家出版社,一直待到1739年初。1739年一月,John Noon出版《人性論》第一卷、第二卷;1740年,Thomas Longman出版第三卷。他依循慣例採用匿名出版,只有過世後出版的作品,才正式列印出自己的姓名。他還特別刪除了其中爭議性最大的章節〈論奇蹟〉,希望能夠避開「狂熱之士」的怒焰,以免波及他在書中神學觀點賴以建立的主要理論基礎。
後來,休姆自覺,如此委曲求全並沒有發揮任何效果。他改編了教宗的弔唁,自嘲:「甫從印刷機落地就夭折,還沒來得及讓世人看清楚,甚至在狂熱分子當中也沒能激起一聲半響。」不過,更多證據顯示恰好相反。發行初期,銷量固然不熱絡,但不久之後,充滿敵意的反撲勢力就如野火燎原,猶待啟航的學術生涯岌岌可危,終其一生,飽受各方人馬對其人格攻擊,還有對他論著曲解汙衊。除了極少數圈內行家,包括教會「溫和派」之外,他淪為眾人眼中的「叛教異端休姆」,而不再是「溫良大衛」。
初期批評聲浪一面倒:(1)幾乎完全聚焦第一卷;(2)嚴重誤解該卷旨意;(3)語氣充滿敵意,用詞遣字極盡羞辱。沒有任何公開回應來自有能力理解者,諸如:柏克萊或哈奇森。為了扭轉此一情勢,休姆於是決定出版一份《文摘》(Abstract),摘錄《人性論》第一卷的主要論述,但此舉也沒能發揮預期效果。失望之餘,他轉而嘗試以散文形式改寫,希望能將理念有效傳達給一般大眾。於是在1741年,他完成了《道德與政治散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普遍反應頗佳。不過,甚至時隔二十數載之後的1766年,休姆還是迭有怨言:
反對我的群書和簡冊,擺滿諾大廳堂的地板,我不可能照單全收,沒一本我想投注絲毫心血去回覆,這不是出於鄙視(其中有些作者,我心存敬重),只是渴望安心、平靜。
(Mossner 1980: 286)
第一位出書嚴肅看待休姆哲學體系的是,格拉斯哥大學邏輯講座教授,湯瑪斯‧里德(Thomas Reid),休姆也應徵過此一講座,不過沒能成功。里德的《人類心靈研究,論共通感原則》(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出版於1764年,時隔《人性論》初問世已過了二十又五個年頭。不過,連他似乎也沒能確當把握休姆旨意,沒有看出兩人在許多重要地方,所見並無二致。
休姆在世時,批評他最有名的就是詹姆士‧貝帝(James Beattie),馬修學院(Marischal College)的道德哲學與邏輯教授,該校位於蘇格蘭東北部的亞伯丁(Aberdeen)。1770年,貝帝的《真理本質與不可變性:反詭辯術和懷疑論》(Essay on the Nature and Immutability of Truth: in opposition to Sophistry and Skepticism),甫上市旋即大受歡迎,在1776年,休姆辭世之前,狂銷五版,但時至今日哲學評價不高。而貝帝身後也只留名於休姆的墓誌銘,「那個狂妄愚蠢的傢伙,貝帝」。雖然,休姆從未公開反駁貝帝,但是長年飽受窮追濫打肯定也讓他受夠了,後來還給未來出版的著作寫了前所未聞的書序「廣告」,自我貶斥《人性論》是輕佻草率的不成熟之作。不過,如此評斷目前少有人認同就是。
1745年,休姆申請愛丁堡大學倫理學與精神哲學(Pneumatical Philosophy)講座教授。這英文「Pneumatics」不是現今所指的氣體動力學,而是涵蓋自然神學、證明上帝不朽,以及研究非物質存有,感官無從覺知的「幽微實體」。休姆怨嘆道:「異端邪說、自然神論、懷疑論、無神論,不足為外人道的指控罵名,開始朝我步步進逼;但城內的好夥伴,在當權勢力壓制下,始終緘默無聞」(1980: 156)。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休姆與《人性論》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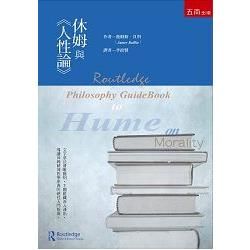 |
休姆與《人性論》 作者:詹姆斯‧貝利 / 譯者:李政賢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00 |
二手中文書 |
$ 405 |
社會人文 |
$ 405 |
社會哲思 |
$ 405 |
哲學 |
$ 418 |
中文書 |
$ 419 |
高等教育 |
$ 428 |
哲學 |
$ 428 |
英美哲學 |
$ 42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休姆與《人性論》
1.重點介紹哲學大師休姆生平與學術發展承先啟後的背景。
2.聚焦導讀《人性論》、《人類理智研究》、《道德原理研究》、〈品味鑒賞標準〉重要篇章,掌握關鍵概念,釐清學術爭議,觸類旁通實踐議題。
大衛‧休姆(David Hume)是哲學史上,以英文著述、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眾所公認,精神哲學領域最重要的曠世經典巨作,媲美牛頓近代自然科學開山之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休姆出身蘇格蘭地方望族之後,兩歲喪父,11歲就讀大學,礙於家境因素輟學。自學有成,22歲開始撰寫《人性論》,自此掀起論戰,梵諦岡查禁所有著作,終其一生備受教會衛道人士打壓,學術生涯坎坷。學思博大精深的休姆,堪稱古今學界的跨界奇葩,精通知識論、倫理學、美學、精神或心靈科學、文學(悲劇理論)、宗教(自殺論、不朽、靈魂等)、法律(正義論、財產權等)、政治、經濟、歷史等等。
作者簡介:
詹姆斯˙貝利(James Baillie)
美國波特蘭大學哲學系教授
專研領域:休姆、人格同一性、宗教哲學、倫理學、近代哲學、分析形上學、精神哲學、語言分析哲學。
譯者簡介:
李政賢
自由譯者。翻譯種類甚多,有教育哲學、教育美學、正向心理學、幸福學、質性研究方法、人文社會科學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生平與年代背景
1711年,大衛‧休姆(David Hume)出生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家族世居貝里克郡的寧威爾區(鄰近英格蘭邊界),在地方小有名望,但家境不算特別富裕。根據記錄顯示,家族姓氏原本正確拼寫是Home,蘇格蘭語發音和Hume相同,中文譯音都近似「休姆」([hjum])。但是,當時地方戶政較為鬆散,所以也有部分人家登記為Hoom、Hum,以及許多其他相近寫法的變體字。雖然,早在12世紀,宗親族人就已落戶貝里克郡,但直系祖先則到了15世紀之後,才定居寧威爾區。1713年,休姆兩歲,父親約瑟夫去世,由寡母凱瑟琳獨...
第一節 生平與年代背景
1711年,大衛‧休姆(David Hume)出生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家族世居貝里克郡的寧威爾區(鄰近英格蘭邊界),在地方小有名望,但家境不算特別富裕。根據記錄顯示,家族姓氏原本正確拼寫是Home,蘇格蘭語發音和Hume相同,中文譯音都近似「休姆」([hjum])。但是,當時地方戶政較為鬆散,所以也有部分人家登記為Hoom、Hum,以及許多其他相近寫法的變體字。雖然,早在12世紀,宗親族人就已落戶貝里克郡,但直系祖先則到了15世紀之後,才定居寧威爾區。1713年,休姆兩歲,父親約瑟夫去世,由寡母凱瑟琳獨...
»看全部
TOP
目錄
致謝辭
休姆作品縮寫對照表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生平與年代背景
第二節 方法與目標
第三節 道德感
第二章 人類理智的背景介紹
第一節 印象和觀念
第二節 因果連結
第三節 否定物質實體和精神實體
第三章 激情
第一節 社會自我
第二節 直接激情
第三節 自豪和卑微
第四節 間接激情的對象與原因
第五節 印象和觀念的雙重連結
第六節 自豪產生通則的配合條件
第七節 同情
第七節 喜愛與憎恨
第八節 同情機轉與比較原則
第四章 動機與意志
第一節 自由與意志
第二節 理性無法直接驅動行為
第三節 激情作為「源生性的存...
休姆作品縮寫對照表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生平與年代背景
第二節 方法與目標
第三節 道德感
第二章 人類理智的背景介紹
第一節 印象和觀念
第二節 因果連結
第三節 否定物質實體和精神實體
第三章 激情
第一節 社會自我
第二節 直接激情
第三節 自豪和卑微
第四節 間接激情的對象與原因
第五節 印象和觀念的雙重連結
第六節 自豪產生通則的配合條件
第七節 同情
第七節 喜愛與憎恨
第八節 同情機轉與比較原則
第四章 動機與意志
第一節 自由與意志
第二節 理性無法直接驅動行為
第三節 激情作為「源生性的存...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詹姆斯‧貝利 譯者: 李政賢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10 ISBN/ISSN:978957118292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西方哲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