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樂之於電影,就像魚之於水,兩者並存才能稱之為完美的作品,電影中的喜怒哀樂,甚至是隱藏的影像符號,靠著配樂的起伏帶領影迷深入電影的奇幻世界。
電影不單單依賴影像說故事,配樂有時說得比視覺符號更多。《影像閱讀時代—音樂‧聆聽的眼睛》分析24部電影配樂,細說音樂的創作內涵及藝術價值,點出音樂如何稱職地發揮說書人、化妝師、旁白者和預言家的功能。透過閱讀這本書,影迷會發現伴隨視覺影像的豐富聽覺世界,將音樂變成「聆聽的眼睛」更深入影像核心,看得更開心!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影像閱讀時代:音樂.聆聽的眼睛(2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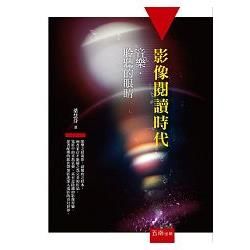 |
影像閱讀時代: 音樂.聆聽的眼睛 (第2版) 作者:桑慧芬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0-0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3 |
電影 |
$ 288 |
藝術設計 |
$ 297 |
中文書 |
$ 298 |
電影 |
$ 304 |
音樂 |
$ 304 |
電影評論 |
$ 304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影像閱讀時代:音樂.聆聽的眼睛(2版)
內容簡介
目錄
再版序
第一章 影像閱讀時代─音樂作為解析符號的工具Ⅰ
音樂與影像互為補述語言
「說書人」
「旁白者」
「化妝師」
「預言家」
結語
第二章 影像閱讀時代—音樂作為解析符號的工具Ⅱ
「標記系列電影」
「協調電影節奏」
「統整時空」
結語
第三章 一個靜默無聲的世界─悲憐上帝的女兒(The Children of Lesser God)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四章 家庭動物園─漢娜姊妹(Hanna and Her Sister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五章 拒絕溶化的心─今生情未了(Un Coeur en Hiver)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六章 預知宿命的悲情民族─流浪者之歌(Dom za vesanje)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七章 走出心靈禁錮的枷鎖─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八章 成敗在天,我們讚美奮鬥─羅倫佐的油(Lorenzo’s Oil)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九章 心靈之鄉的逆旅過客─遊子(Kolya)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章 生命幽谷的天堂微光─月光提琴手(To Fos pou svini)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一章 池塘深底‧愛的教育─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二章 掀動沉澱的記憶─童年再見(Au revoir les enfant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三章 笑淚中競技的無聲樂團─巴爾幹龐克(Super 8 Storie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四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布拉格的春天(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五章 費氏數列‧城市的聲音─午夜之後‧狂戀(Dopo mezzanotte)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六章 當慕賽塔?還是咪咪?─發暈(Moonstruck)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七章 對傳統禮教的無聲控訴─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八章 愛得過火─與敵人共枕(Sleeping with the enemy)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九章 是愛人還是敵手─音樂作為解析符號的工具Ⅲ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章 愛到深處無怨尤─永遠的愛人(Immortal Beloved)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一章 愛與被愛的計謀─春光奏鳴曲(Impromptu)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二章 命運啊,主宰世界的女王─法朵(Amália)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三章 分秒間的生命存在思考─時時刻刻(The Hour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四章 當電影愛上歌劇─戲中戲的趣味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影像閱讀時代─音樂作為解析符號的工具Ⅰ
音樂與影像互為補述語言
「說書人」
「旁白者」
「化妝師」
「預言家」
結語
第二章 影像閱讀時代—音樂作為解析符號的工具Ⅱ
「標記系列電影」
「協調電影節奏」
「統整時空」
結語
第三章 一個靜默無聲的世界─悲憐上帝的女兒(The Children of Lesser God)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四章 家庭動物園─漢娜姊妹(Hanna and Her Sister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五章 拒絕溶化的心─今生情未了(Un Coeur en Hiver)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六章 預知宿命的悲情民族─流浪者之歌(Dom za vesanje)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七章 走出心靈禁錮的枷鎖─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八章 成敗在天,我們讚美奮鬥─羅倫佐的油(Lorenzo’s Oil)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九章 心靈之鄉的逆旅過客─遊子(Kolya)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章 生命幽谷的天堂微光─月光提琴手(To Fos pou svini)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一章 池塘深底‧愛的教育─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二章 掀動沉澱的記憶─童年再見(Au revoir les enfant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三章 笑淚中競技的無聲樂團─巴爾幹龐克(Super 8 Storie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四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布拉格的春天(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五章 費氏數列‧城市的聲音─午夜之後‧狂戀(Dopo mezzanotte)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六章 當慕賽塔?還是咪咪?─發暈(Moonstruck)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七章 對傳統禮教的無聲控訴─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八章 愛得過火─與敵人共枕(Sleeping with the enemy)
延伸導聆
結語
第十九章 是愛人還是敵手─音樂作為解析符號的工具Ⅲ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章 愛到深處無怨尤─永遠的愛人(Immortal Beloved)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一章 愛與被愛的計謀─春光奏鳴曲(Impromptu)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二章 命運啊,主宰世界的女王─法朵(Amália)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三章 分秒間的生命存在思考─時時刻刻(The Hours)
延伸導聆
結語
第二十四章 當電影愛上歌劇─戲中戲的趣味
參考書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