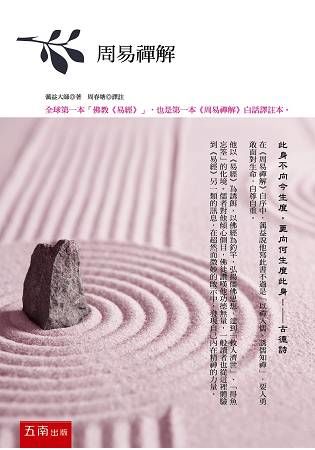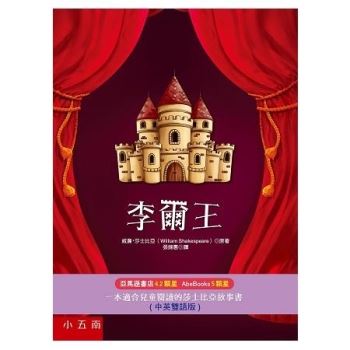佛教要求智慧的超越和身心的解脫,它的外觀雖有形而上的包裝,內部卻是一個嚴謹的經驗論和實踐論。每當人向釋迦牟尼問起抽象的哲理問題時,他總是閉口不言,保持「高貴的緘默」,他的用意,不難想見。
蕅益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也是一位樸實無華而充滿詩趣的高僧。他想從知識中發現智慧,從本性中找回生命,歸還給人們應有的本來面目。所以在「慈航普渡」的佛經和「雲行雨施」的《易經》相互對照下,蕅益大師給了我們一部和傳統截然不同的《易經》,充滿生活、修行的趣味,和自度度人的妙方,堪稱人間佛教最好的教科書。
本書除了收錄《周易禪解》十卷全文外,每卷都包括
1.《易經》原文
2.蕅益大師禪解原文
3.蕅益大師原文的翻譯和詮釋
期使更淺白文字的譯註,能使這部自明代流傳至今的傳世寶典,發揮更深層的影響力。
當佛經遇上《易經》,蕅益大師替入世的《易經》增添了宗教的光芒,替出世的佛教增添了人世間的意義。從宗教的立場說,這是儒學的進步,佛學的讓步;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則是一件不可避免、皆大歡喜的儒佛交融的文化現象。
全球第一本白話文譯註本
全球第一本「佛教《易經》」,也是第一本《周易禪解》譯註版。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古德詩
在《周易禪解》自序中,蕅益說他寫此書不過是「以禪入儒,誘儒知禪」,要人勇敢面對生命,自尊自重。
他以《易經》為誘餌,以佛經為釣竿,弘揚儒佛思想,達到「救人濟世」、「得魚忘筌」的化境。儒者對他傾心側目,佛徒讚嘆他功德無量,一般讀者也從這裡體驗到《易經》另一類的訊息,在超然而微妙的啟示中,發現自己內在精神的力量。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周易禪解(全球第一本白話文譯註本)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711 |
易經 |
$ 810 |
易經 |
$ 810 |
五南文庫 |
$ 837 |
中文書 |
$ 837 |
高等教育 |
$ 855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周易禪解(全球第一本白話文譯註本)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1599-1655),俗姓鍾,名際明,字振之,法名蕅益智旭,自號八不道人,古吳木瀆人(今江蘇吳縣),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十二歲讀儒書,作《滅佛論》數十篇,誓滅佛老。十七歲受蓮池大師和王陽明的影響,不再謗佛,把所著謗佛言論付之一炬。二十歲注《論語》,至「天下歸仁」一句,廢寢忘食者數日,漸悟孔顏心法。二十三歲聽《大佛頂楞嚴經》,被「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那句話打動,次年剃度出家,決心「要復我本來面目」。出家前,先發三願:一、未證無生法忍,不收門徒;二、不登高座;三、寧凍餓死,不誦經禮懺及化緣,以資身口。
蕅益大師註釋佛經甚多,包含《阿彌陀經》、《占察經》、《楞伽經》、《楞嚴經》、《法華經》、《梵網經》、《金剛經》、《心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等二十餘種,儒書則有《四書蕅益解》和《周易禪解》。
大師晚年居靈峰,故又稱靈峰蕅益大師,自稱北天目道人蕅益智旭。
他畢生修行和參悟,確守淨土六字彌陀的話頭,和天台圓教「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信念,給淨土和天台做了極好的表揚,後世尊為淨土八祖,和天台第三十一代祖師。
譯者簡介
周春塘
現職:威爾斯大學英國漢學院董事/教授;《新地雜誌社》副總編輯
學歷:美國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
經歷:美國愛阿華大學講師、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華梵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所長;《文星雜誌》、《慧炬月刊》編輯;香港《大學生活》特約撰稿人
著作:〈敦煌變文研究〉、〈蘇俄文學新論〉、〈緣起性空與人生〉、Lake Como(英文詩集)、《書寫生命中的溫柔──在文字背後看見感動》、《撰寫論文的第一本書》、《波士頓新聞‧易經講座》等中英文著作四十餘篇
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1599-1655),俗姓鍾,名際明,字振之,法名蕅益智旭,自號八不道人,古吳木瀆人(今江蘇吳縣),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十二歲讀儒書,作《滅佛論》數十篇,誓滅佛老。十七歲受蓮池大師和王陽明的影響,不再謗佛,把所著謗佛言論付之一炬。二十歲注《論語》,至「天下歸仁」一句,廢寢忘食者數日,漸悟孔顏心法。二十三歲聽《大佛頂楞嚴經》,被「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那句話打動,次年剃度出家,決心「要復我本來面目」。出家前,先發三願:一、未證無生法忍,不收門徒;二、不登高座;三、寧凍餓死,不誦經禮懺及化緣,以資身口。
蕅益大師註釋佛經甚多,包含《阿彌陀經》、《占察經》、《楞伽經》、《楞嚴經》、《法華經》、《梵網經》、《金剛經》、《心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等二十餘種,儒書則有《四書蕅益解》和《周易禪解》。
大師晚年居靈峰,故又稱靈峰蕅益大師,自稱北天目道人蕅益智旭。
他畢生修行和參悟,確守淨土六字彌陀的話頭,和天台圓教「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信念,給淨土和天台做了極好的表揚,後世尊為淨土八祖,和天台第三十一代祖師。
譯者簡介
周春塘
現職:威爾斯大學英國漢學院董事/教授;《新地雜誌社》副總編輯
學歷:美國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
經歷:美國愛阿華大學講師、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華梵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所長;《文星雜誌》、《慧炬月刊》編輯;香港《大學生活》特約撰稿人
著作:〈敦煌變文研究〉、〈蘇俄文學新論〉、〈緣起性空與人生〉、Lake Como(英文詩集)、《書寫生命中的溫柔──在文字背後看見感動》、《撰寫論文的第一本書》、《波士頓新聞‧易經講座》等中英文著作四十餘篇
目錄
序
卷一(上經之一) 乾 坤
卷二 (上經之二)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三 (上經之三)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卷四 (上經之四)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五 (下經之一)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暌 蹇 解 損 益
卷六 (下經之二)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卷七 (下經之三)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八 繫辭上傳
卷九 繫辭下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卷十 河圖說 洛書說 伏羲八卦次序說 伏羲八卦方位說 六十四卦方位說 文王八卦次序說 文王八卦方位說
卷一(上經之一) 乾 坤
卷二 (上經之二)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三 (上經之三)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卷四 (上經之四)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五 (下經之一)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暌 蹇 解 損 益
卷六 (下經之二)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卷七 (下經之三)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八 繫辭上傳
卷九 繫辭下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卷十 河圖說 洛書說 伏羲八卦次序說 伏羲八卦方位說 六十四卦方位說 文王八卦次序說 文王八卦方位說
序
序
『群龍無首,吉!』
明‧蕅益大師《周易禪解》譯註序
這是一個陰陽失調、上下失序的時代;這是一個青黃不接、黑白不分的時代;這是一個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代;老年人感到無奈,青年人感到彷徨,少年人感到焦躁;我們丟失了過去,隨風飄向茫然的未來,沒有重心,沒有方向,手中捏著一把冷汗:這是噩夢,是幻想?是煉獄,還是解脫?是絕望,還是希望?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想尋找希望,可真不容易。每天層出不窮的恐怖事件,毫無理性的集體屠殺,加上昧著良心的政客和奸商,把國家和民眾的福祉安危,在唯利是圖的前提下變成了當然的犧牲品。
哪裡是我們的希望?哪裡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呀?
有人打開《易經》,尋找答案。有些《易經》達人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有些說:「樂天知命,禍福相倚」,雖然給了我們些許的安慰,抓住了《易經》形而上學的皮毛,卻沒有發揚《易經》解決問題的初衷。這種滿足於形而上的陳述,是中國哲學界向有的現象,不足為怪;但如果問題沒有解決,目的沒有達到,跟阿Q的精神勝利又有什麼不同?佛教要求智慧的超越和身心的解脫,它的外觀雖有形而上的包裝,內部卻是一個嚴謹的經驗論和實踐論。每當人向釋迦牟尼問起哲理的問題時,他總是閉口不言,保持「高貴的緘默」,他的用意,不難想見。
佛陀最微妙的「中觀論」,包括空假中的「三觀」和「破三觀」的中道,是佛陀七百年後印度哲學家龍樹整理出來的思想,也成為後來天台宗教理的骨幹。明代蕅益大師用佛理解讀《易經》,雖也借用這些術語,但一如佛陀,仍然全神卻貫注在實踐——也就是修行——的工夫上。事實上,實事求是也是《易經》一貫的主張,但不到《周易禪解》問世,很少人察覺到罷了。在「慈航普渡」的佛經和「雲行雨施」的《易經》相互對照下,蕅益大師給了我們一部跟傳統截然不同的《易經》,充滿了活生生的趣味,和自度度人的妙方!
人的苦來自「我」,佛經中的「身、口、意」便是「我」的象徵,稱為「三業」。但誰都知道,我的身體、我的言論和我的意念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惡事,因此也有「三善業」和「三惡業」的不同,前者造福人群,值得讚美,後者製造糾紛,需要防範。懂得這個道理,人才會開始警覺,對自己要求多,對人責難少,而人世間的祥和之氣才會隨之而發生。蕅益大師提醒我們說,其實孔子的「仁學」也有同樣的作用;《論語》裡「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的話,便是身口意的管制,提高了個人的價值和力量,成為大同理想的先決條件。蕅益年青時代便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儒生,隨後潛心佛學,奠定了他劃時代的「以禪入儒、誘儒知禪」的《周易禪解》工程。
蕅益大師(1599-1655),俗姓鍾,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二十三歲聽《大佛頂楞嚴經》,「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那句神秘的話打動了他,次年剃度出家,法名智旭。剃度前,他的舅父母不同意,舅母問他,「今天佛教圈裡亂成一團,你幹嘛要做和尚?你是想做善知識吧?」蕅益說,「我佛都不想做,而況其他?」舅父聽了,笑著說,「既然如此,又何必出家呢?」他回答說:「只要復我本來面目!」
用佛經的話說,人的本來面目,就是真如本性,也稱佛性;這是人人能夠成佛的根本道理。然而人的本性不容易看見,因為身口意把它層層污染了。《周易》以乾坤為首,開天闢地後,亂象叢生,最顯著的莫過於人心,人雖有佛性,人的心卻是虛妄和無明的大本營。蕅益用屯卦( )解釋了人心「一念初動」時的利弊。他說,「人的真如如果不依本性的原則行動,讓無明牽著你的鼻子走,並用因明學來推理,製造妄念,顛倒是非,亂象便發生了。」但他繼續說,「如果沒有一念初動的亂象,我們又怎能悟到修德的重要呢?」。屯卦上坎下震,上面是滂沱的大雨,下面是震耳欲聾的雷電,險象重重。在這惡劣的環境中,幸而一念初動,證明我們的身口意沒有昏睡,還有機會開啟智慧的大門,給自己帶來轉機,這便是生命的意義,也是坎險( )的意義。
蕅益對坎的認識,賦予了佛經和《易經》特殊的趣味,也說明了人的覺心充滿了潛在的力量。繼險象環生的屯卦之後,他還指出童蒙無知的蒙卦(上艮下坎),能在危險則中向自己招手喊停,回頭是岸,便是吉利;在風雨飄搖的需卦(上坎下乾)裡,如果有人按兵不動,不是怯懦,因為智慧也需要韜光養晦的機會;在你爭我奪的訟卦(上乾下坎)中,敢向自己興師問罪,坦白「自訟」,才是真正的智慧;在干戈相向的師卦(上坤下坎)裡,如果戰爭不能避免,挺身而出,以毒攻毒,藥到病除,才是真正的勇敢;在人事莫測的比卦(上坎下坤)裡,人吃盡了苦頭,丟盡了朋友,才發現希望原來就在自己的身邊。乾卦「群龍無首」的妙喻,在這裡也產生了奇特的效應。
從屯卦初九的「建侯」,到比卦上六的「比之無首」,是一部人類生存奮鬥的小史,而坎卦從不缺席。依照天台止觀的學說,只要有智慧,加上禪定的工夫,困難沒有不被克服,光明沒有不會朗照;危險和希望總是緊緊相扣在一起。人不怕一念初動,只怕覺悟來遲。人需要的是覺,是解脫,不是語言的麻醉。坎險對人的意義非比尋常。但這些簡單而永恆的真理,如果沒有蕅益大師的提醒,誰注意到呢?
從佛法看《易經》,蕅益也為我們揭開了永恆的面紗。
咸卦( )上兌下艮,恒卦( )上震下巽,他們分別代表感和應,是「天地萬物之情」一感一應、一動一靜的自然現象 ,雖然變化無窮,但連智慧不高的魚和豬都能感受,還不够恒常嗎?咸(感)是動,是無常,但它的卦象是寂然不動的澤( )和山( );恒是靜,是有常,卦象卻是瞬息萬變的雷( )和風( ),是饒有趣味的安排,所以蕅益說:
如果寂然不動的澤和山是「咸」,那麼常就是無常了;如果瞬息萬變的雷和風是「恒」,那麼無常就是有常了。 變化無常的「咸」既然是寂然不動的澤和山,所謂無常,就是有常了;永不改變的「恒」既然是瞬息萬變的雷和風,所謂常,也就是無常了。《涅槃經‧鳥喻品》拿鴛鴦雙宿雙飛的現象,比喻常與無常永不分離,從這裡也可以得到理解!
佛教講究真理,追求寂照(《楞嚴經》用語:真理的體是寂,真理的用是照),在寂照的光芒中我們得到無言的啟示,那才是「看破」和「放下」真正的動力;如果我們能走上覺悟的道路,則更是智慧和禪定的收穫了。這些個人的努力,遠比「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那樣的話有意義多多。
再說,佛經中司空見慣的常與無常,對蕅益本人來說,卻有切膚之痛:他四十三歲寫《周易禪解》,是明崇禎十四年(1641),當他四十七歲完成寫作時,崇禎皇帝已經縊死煤山,大明三百年的江山已經走入歷史,是清順治皇帝入關的第二年(1645)了!短短四年間翻天覆地的變化,滄海桑田的淒涼,個人和時代意識的破滅,鐵石心腸也會墮淚!他才有資格說「這是一個陰陽失調、上下失序的時代;這是一個青黃不接、黑白不分的時代…」!然而他沒有這樣做。在痛定思痛之餘,他親眼看見該變的全變了,不該變的也變了,但出乎意料之外地,他「卻發現有些東西竟然一成不變!」這時他才體會到,「不變」原來就是「至變」,而「至變」原來就是「不變」!他再度想到比翼雙飛的鴛鴦,這個常與無常的象徵,從來便在空中翩翩起舞,一刻都不曾休歇!
這便是真理!這便是生活!在徹底的破滅中,真理會露面;在群龍無首的天地間,吉祥會呈現奪目的光彩!然而沒有智慧,不能看破;沒有禪定,不能放下。對蕅益來說,「悟」是時間的造化,時間淨化了他的生命,讓他在不幸中懂得慈悲的重要,也為他解開了《大佛頂經》「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那句神秘難解的名言。
抽象的思維常有提綱挈領、畫龍點睛的妙用,在宗教和哲學的領域中,尤為恰當。在詮釋《易經》時,蕅益不斷提到的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八個字。那是天台圓教(大乘窮極的實教)的教理,用在「神無方而易無體」的《易經》身上,再合適不過了。從佛學的角度看,隨緣不變,指森羅萬象的大千世界如如不動;不變隨緣,指千波萬浪的因緣在覺性中翻騰,而真如不改。解讀《易‧繫辭》時,蕅益說:
《易經》的道理,一言以蔽之,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這是天地萬物構成的基本原則。書中卦爻陰陽的變化,是天地萬物的縮影。至於天的「易知」、地的「易從」,是品玩天地萬物之後得到的結論。…(《繫辭》)先說怎樣從天地萬物中得到了易書,從易書中完成了易學,又怎樣從易學中印證了易理。
對蕅益來說,所謂易理,是從本體開始推演,得到空假中「三觀」的結論,這就是「不變隨緣」;以中道的本體作為推演的過程,達到「破三觀」的效果,回到真如本性,這就是「隨緣不變」。他的方法,在原則上避免了宿命論和排他性的陷阱,讓人在瞬息間領悟到天下的至理和生命的意義。至於「讓人不在歧路上痛哭,明白成功不是運氣」等等的觀察,把高深化為平易,把日用化為神奇,正是宗教家救人濟世精神的。
在《周易禪解‧序》中蕅益說他寫此書不過是「以禪入儒,誘儒知禪」,重點好像在學術。但他的話只說了一半,而且誤導了讀者三百六十年。他自己很清楚,他的易,是易又不是易,是非易,又是非非易;換句話說,他用《易經》作為誘餌,用佛經作為釣竿,弘揚儒佛思想,執行他宗教家「救人濟世」的任務,達到了「得魚忘筌」的化境:儒者對他傾心側目,佛徒讚歎他的功德無量,聽眾範圍越來越大,而傳播的效果也到達了頂峰。
不過佛經遇上了《易經》,這種今天稱之為「儒佛會通」的行動,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呢?蕅益替入世的《易經》增添了宗教的光芒,替出世的佛教增添了人世間的精神!從宗教的立場說,這是儒學的進步,是佛學的讓步;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卻是一件不可避免的、皆大歡喜的事實。中國自從隋唐以來,佛教便開始了明顯而漫長的漢化過程,其中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天台宗的創建。天台圓教「一行一切行」的包容,和「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教理,開啟了人間佛教的先河。宋代廓庵的《牧牛圖》便是人間佛教勝利的宣言,其中「返本還原」、「入廛垂手」的欣慰,曾一再出現在蕅益大師的詩文中。蕅益在《周易禪解》中更不斷強調說,證得佛果的人,不入涅槃,而願流轉九界,度化眾生,乃是從「凡夫性」進入「聖人性」的證明,是值得讚揚的人間智慧!
當然,有勝利就有挫敗,有解脫就有沉淪,有安樂就有憂患,這正是蕅益所說「二鳥雙遊」的必然性。但蕅益提出個人超越時空的修養,利用定慧的力量,在群龍無首的困境中,發現自己,發揚自覺覺他、救人濟世的菩薩精神,足以造就一個全新的天地:雖然空無一物,群龍無首,依然處之泰然。用蕅益在《繫辭上傳》裡的話說,那就是:「運用乾坤的力量,修持定慧的工夫;運用定慧的力量,發揮心中本然的易理!」
中國人談《易經》,喜歡把它高深化,所謂「探頤索隱,鉤深致遠」,向來是我們讀易的標準模式。蕅益大師也不例外。他借重這個複雜的模式,圓滿達成了他簡單的度化眾生的願望。雖然不少後世學者認為他有比這更廣大、更深遠的計劃。我們不能否認蕅益大師解易時儒佛雙管齊下的努力和他在學術上另闢蹊徑的成就,然而因此便相信他有王弼註《老》、僧肇建立「般若學」一般的雄心,未免強人所難;尤其當他們發現蕅益運用了太多的「比附」,卻沒有完成他的「計劃」,開始對他感到遺憾時,便有欠公允了!
蕅益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更是一位樸實而充滿詩趣的高僧。他想從知識中發現智慧,從本性中找回生命,歸還給人們應有的本來面目。但這不是學問可以做到的事。他把學問比喻為「楊葉空拳」(《四書蕅益解‧序》),並非偶然。楊葉被風一吹,散落滿地,不可收拾;拳頭打開,裡面空無一物:這便是所謂的學問,不是真理!是束縛,不是解脫!他心中「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的自然境界,是王充、僧肇,以及 後來以搬弄學問為榮的學者所望塵莫及的!
作為一個宗教家,他有他憂心如焚的地方,但他的壓力不在學問,而在時間,這個「無在而無所不在」的時間,這個只會在人心中若隱若現、跟人捉迷藏的時間(革卦•象傳),才是他最大的敵人!從《易經》的千言萬語語中,除了吉凶悔吝這些詞彙外,他最看重一句話是:「與時俱進」,不要落後!
人的生命是時間,而悟的關鍵也是時間。
蕅益在乾卦中提出的話:「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雖是通俗至極的老生常談,卻是他給我們讀《易經》時語重心長、至高無上的企盼!
此書寫作期間,榮獲 淨空老法師殷切的鼓勵和題字,萬分感謝!
周春塘 敬序於新店花園新城攬翠樓
『群龍無首,吉!』
明‧蕅益大師《周易禪解》譯註序
這是一個陰陽失調、上下失序的時代;這是一個青黃不接、黑白不分的時代;這是一個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代;老年人感到無奈,青年人感到彷徨,少年人感到焦躁;我們丟失了過去,隨風飄向茫然的未來,沒有重心,沒有方向,手中捏著一把冷汗:這是噩夢,是幻想?是煉獄,還是解脫?是絕望,還是希望?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想尋找希望,可真不容易。每天層出不窮的恐怖事件,毫無理性的集體屠殺,加上昧著良心的政客和奸商,把國家和民眾的福祉安危,在唯利是圖的前提下變成了當然的犧牲品。
哪裡是我們的希望?哪裡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呀?
有人打開《易經》,尋找答案。有些《易經》達人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有些說:「樂天知命,禍福相倚」,雖然給了我們些許的安慰,抓住了《易經》形而上學的皮毛,卻沒有發揚《易經》解決問題的初衷。這種滿足於形而上的陳述,是中國哲學界向有的現象,不足為怪;但如果問題沒有解決,目的沒有達到,跟阿Q的精神勝利又有什麼不同?佛教要求智慧的超越和身心的解脫,它的外觀雖有形而上的包裝,內部卻是一個嚴謹的經驗論和實踐論。每當人向釋迦牟尼問起哲理的問題時,他總是閉口不言,保持「高貴的緘默」,他的用意,不難想見。
佛陀最微妙的「中觀論」,包括空假中的「三觀」和「破三觀」的中道,是佛陀七百年後印度哲學家龍樹整理出來的思想,也成為後來天台宗教理的骨幹。明代蕅益大師用佛理解讀《易經》,雖也借用這些術語,但一如佛陀,仍然全神卻貫注在實踐——也就是修行——的工夫上。事實上,實事求是也是《易經》一貫的主張,但不到《周易禪解》問世,很少人察覺到罷了。在「慈航普渡」的佛經和「雲行雨施」的《易經》相互對照下,蕅益大師給了我們一部跟傳統截然不同的《易經》,充滿了活生生的趣味,和自度度人的妙方!
人的苦來自「我」,佛經中的「身、口、意」便是「我」的象徵,稱為「三業」。但誰都知道,我的身體、我的言論和我的意念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惡事,因此也有「三善業」和「三惡業」的不同,前者造福人群,值得讚美,後者製造糾紛,需要防範。懂得這個道理,人才會開始警覺,對自己要求多,對人責難少,而人世間的祥和之氣才會隨之而發生。蕅益大師提醒我們說,其實孔子的「仁學」也有同樣的作用;《論語》裡「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的話,便是身口意的管制,提高了個人的價值和力量,成為大同理想的先決條件。蕅益年青時代便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儒生,隨後潛心佛學,奠定了他劃時代的「以禪入儒、誘儒知禪」的《周易禪解》工程。
蕅益大師(1599-1655),俗姓鍾,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二十三歲聽《大佛頂楞嚴經》,「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那句神秘的話打動了他,次年剃度出家,法名智旭。剃度前,他的舅父母不同意,舅母問他,「今天佛教圈裡亂成一團,你幹嘛要做和尚?你是想做善知識吧?」蕅益說,「我佛都不想做,而況其他?」舅父聽了,笑著說,「既然如此,又何必出家呢?」他回答說:「只要復我本來面目!」
用佛經的話說,人的本來面目,就是真如本性,也稱佛性;這是人人能夠成佛的根本道理。然而人的本性不容易看見,因為身口意把它層層污染了。《周易》以乾坤為首,開天闢地後,亂象叢生,最顯著的莫過於人心,人雖有佛性,人的心卻是虛妄和無明的大本營。蕅益用屯卦( )解釋了人心「一念初動」時的利弊。他說,「人的真如如果不依本性的原則行動,讓無明牽著你的鼻子走,並用因明學來推理,製造妄念,顛倒是非,亂象便發生了。」但他繼續說,「如果沒有一念初動的亂象,我們又怎能悟到修德的重要呢?」。屯卦上坎下震,上面是滂沱的大雨,下面是震耳欲聾的雷電,險象重重。在這惡劣的環境中,幸而一念初動,證明我們的身口意沒有昏睡,還有機會開啟智慧的大門,給自己帶來轉機,這便是生命的意義,也是坎險( )的意義。
蕅益對坎的認識,賦予了佛經和《易經》特殊的趣味,也說明了人的覺心充滿了潛在的力量。繼險象環生的屯卦之後,他還指出童蒙無知的蒙卦(上艮下坎),能在危險則中向自己招手喊停,回頭是岸,便是吉利;在風雨飄搖的需卦(上坎下乾)裡,如果有人按兵不動,不是怯懦,因為智慧也需要韜光養晦的機會;在你爭我奪的訟卦(上乾下坎)中,敢向自己興師問罪,坦白「自訟」,才是真正的智慧;在干戈相向的師卦(上坤下坎)裡,如果戰爭不能避免,挺身而出,以毒攻毒,藥到病除,才是真正的勇敢;在人事莫測的比卦(上坎下坤)裡,人吃盡了苦頭,丟盡了朋友,才發現希望原來就在自己的身邊。乾卦「群龍無首」的妙喻,在這裡也產生了奇特的效應。
從屯卦初九的「建侯」,到比卦上六的「比之無首」,是一部人類生存奮鬥的小史,而坎卦從不缺席。依照天台止觀的學說,只要有智慧,加上禪定的工夫,困難沒有不被克服,光明沒有不會朗照;危險和希望總是緊緊相扣在一起。人不怕一念初動,只怕覺悟來遲。人需要的是覺,是解脫,不是語言的麻醉。坎險對人的意義非比尋常。但這些簡單而永恆的真理,如果沒有蕅益大師的提醒,誰注意到呢?
從佛法看《易經》,蕅益也為我們揭開了永恆的面紗。
咸卦( )上兌下艮,恒卦( )上震下巽,他們分別代表感和應,是「天地萬物之情」一感一應、一動一靜的自然現象 ,雖然變化無窮,但連智慧不高的魚和豬都能感受,還不够恒常嗎?咸(感)是動,是無常,但它的卦象是寂然不動的澤( )和山( );恒是靜,是有常,卦象卻是瞬息萬變的雷( )和風( ),是饒有趣味的安排,所以蕅益說:
如果寂然不動的澤和山是「咸」,那麼常就是無常了;如果瞬息萬變的雷和風是「恒」,那麼無常就是有常了。 變化無常的「咸」既然是寂然不動的澤和山,所謂無常,就是有常了;永不改變的「恒」既然是瞬息萬變的雷和風,所謂常,也就是無常了。《涅槃經‧鳥喻品》拿鴛鴦雙宿雙飛的現象,比喻常與無常永不分離,從這裡也可以得到理解!
佛教講究真理,追求寂照(《楞嚴經》用語:真理的體是寂,真理的用是照),在寂照的光芒中我們得到無言的啟示,那才是「看破」和「放下」真正的動力;如果我們能走上覺悟的道路,則更是智慧和禪定的收穫了。這些個人的努力,遠比「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那樣的話有意義多多。
再說,佛經中司空見慣的常與無常,對蕅益本人來說,卻有切膚之痛:他四十三歲寫《周易禪解》,是明崇禎十四年(1641),當他四十七歲完成寫作時,崇禎皇帝已經縊死煤山,大明三百年的江山已經走入歷史,是清順治皇帝入關的第二年(1645)了!短短四年間翻天覆地的變化,滄海桑田的淒涼,個人和時代意識的破滅,鐵石心腸也會墮淚!他才有資格說「這是一個陰陽失調、上下失序的時代;這是一個青黃不接、黑白不分的時代…」!然而他沒有這樣做。在痛定思痛之餘,他親眼看見該變的全變了,不該變的也變了,但出乎意料之外地,他「卻發現有些東西竟然一成不變!」這時他才體會到,「不變」原來就是「至變」,而「至變」原來就是「不變」!他再度想到比翼雙飛的鴛鴦,這個常與無常的象徵,從來便在空中翩翩起舞,一刻都不曾休歇!
這便是真理!這便是生活!在徹底的破滅中,真理會露面;在群龍無首的天地間,吉祥會呈現奪目的光彩!然而沒有智慧,不能看破;沒有禪定,不能放下。對蕅益來說,「悟」是時間的造化,時間淨化了他的生命,讓他在不幸中懂得慈悲的重要,也為他解開了《大佛頂經》「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那句神秘難解的名言。
抽象的思維常有提綱挈領、畫龍點睛的妙用,在宗教和哲學的領域中,尤為恰當。在詮釋《易經》時,蕅益不斷提到的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八個字。那是天台圓教(大乘窮極的實教)的教理,用在「神無方而易無體」的《易經》身上,再合適不過了。從佛學的角度看,隨緣不變,指森羅萬象的大千世界如如不動;不變隨緣,指千波萬浪的因緣在覺性中翻騰,而真如不改。解讀《易‧繫辭》時,蕅益說:
《易經》的道理,一言以蔽之,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這是天地萬物構成的基本原則。書中卦爻陰陽的變化,是天地萬物的縮影。至於天的「易知」、地的「易從」,是品玩天地萬物之後得到的結論。…(《繫辭》)先說怎樣從天地萬物中得到了易書,從易書中完成了易學,又怎樣從易學中印證了易理。
對蕅益來說,所謂易理,是從本體開始推演,得到空假中「三觀」的結論,這就是「不變隨緣」;以中道的本體作為推演的過程,達到「破三觀」的效果,回到真如本性,這就是「隨緣不變」。他的方法,在原則上避免了宿命論和排他性的陷阱,讓人在瞬息間領悟到天下的至理和生命的意義。至於「讓人不在歧路上痛哭,明白成功不是運氣」等等的觀察,把高深化為平易,把日用化為神奇,正是宗教家救人濟世精神的。
在《周易禪解‧序》中蕅益說他寫此書不過是「以禪入儒,誘儒知禪」,重點好像在學術。但他的話只說了一半,而且誤導了讀者三百六十年。他自己很清楚,他的易,是易又不是易,是非易,又是非非易;換句話說,他用《易經》作為誘餌,用佛經作為釣竿,弘揚儒佛思想,執行他宗教家「救人濟世」的任務,達到了「得魚忘筌」的化境:儒者對他傾心側目,佛徒讚歎他的功德無量,聽眾範圍越來越大,而傳播的效果也到達了頂峰。
不過佛經遇上了《易經》,這種今天稱之為「儒佛會通」的行動,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呢?蕅益替入世的《易經》增添了宗教的光芒,替出世的佛教增添了人世間的精神!從宗教的立場說,這是儒學的進步,是佛學的讓步;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卻是一件不可避免的、皆大歡喜的事實。中國自從隋唐以來,佛教便開始了明顯而漫長的漢化過程,其中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天台宗的創建。天台圓教「一行一切行」的包容,和「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教理,開啟了人間佛教的先河。宋代廓庵的《牧牛圖》便是人間佛教勝利的宣言,其中「返本還原」、「入廛垂手」的欣慰,曾一再出現在蕅益大師的詩文中。蕅益在《周易禪解》中更不斷強調說,證得佛果的人,不入涅槃,而願流轉九界,度化眾生,乃是從「凡夫性」進入「聖人性」的證明,是值得讚揚的人間智慧!
當然,有勝利就有挫敗,有解脫就有沉淪,有安樂就有憂患,這正是蕅益所說「二鳥雙遊」的必然性。但蕅益提出個人超越時空的修養,利用定慧的力量,在群龍無首的困境中,發現自己,發揚自覺覺他、救人濟世的菩薩精神,足以造就一個全新的天地:雖然空無一物,群龍無首,依然處之泰然。用蕅益在《繫辭上傳》裡的話說,那就是:「運用乾坤的力量,修持定慧的工夫;運用定慧的力量,發揮心中本然的易理!」
中國人談《易經》,喜歡把它高深化,所謂「探頤索隱,鉤深致遠」,向來是我們讀易的標準模式。蕅益大師也不例外。他借重這個複雜的模式,圓滿達成了他簡單的度化眾生的願望。雖然不少後世學者認為他有比這更廣大、更深遠的計劃。我們不能否認蕅益大師解易時儒佛雙管齊下的努力和他在學術上另闢蹊徑的成就,然而因此便相信他有王弼註《老》、僧肇建立「般若學」一般的雄心,未免強人所難;尤其當他們發現蕅益運用了太多的「比附」,卻沒有完成他的「計劃」,開始對他感到遺憾時,便有欠公允了!
蕅益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更是一位樸實而充滿詩趣的高僧。他想從知識中發現智慧,從本性中找回生命,歸還給人們應有的本來面目。但這不是學問可以做到的事。他把學問比喻為「楊葉空拳」(《四書蕅益解‧序》),並非偶然。楊葉被風一吹,散落滿地,不可收拾;拳頭打開,裡面空無一物:這便是所謂的學問,不是真理!是束縛,不是解脫!他心中「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的自然境界,是王充、僧肇,以及 後來以搬弄學問為榮的學者所望塵莫及的!
作為一個宗教家,他有他憂心如焚的地方,但他的壓力不在學問,而在時間,這個「無在而無所不在」的時間,這個只會在人心中若隱若現、跟人捉迷藏的時間(革卦•象傳),才是他最大的敵人!從《易經》的千言萬語語中,除了吉凶悔吝這些詞彙外,他最看重一句話是:「與時俱進」,不要落後!
人的生命是時間,而悟的關鍵也是時間。
蕅益在乾卦中提出的話:「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雖是通俗至極的老生常談,卻是他給我們讀《易經》時語重心長、至高無上的企盼!
此書寫作期間,榮獲 淨空老法師殷切的鼓勵和題字,萬分感謝!
周春塘 敬序於新店花園新城攬翠樓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