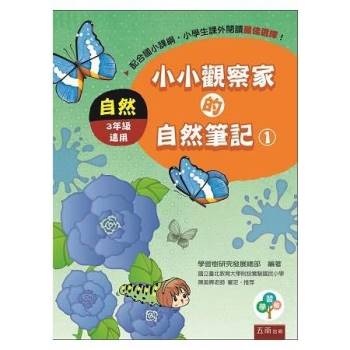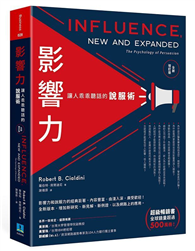在鈴木博士生花妙筆下,把一般人望而卻步的「禪」說解成人人可解的生活體驗。
鈴木大拙為當今的禪學權威,是把禪宗傳到日本之外的世界先鋒。
本書是從享譽世界的禪學大師鈴木大拙所著《禪學論文集》、《禪學研究》中精選而成。在鈴木博士生花妙筆下,把「禪」說解成人人可解的生活體驗。
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無一不含禪機,而禪家所體驗的則是禪悟的喜悅。現代人為了不迷失自己,《禪與生活》一書不容錯過。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禪與生活的圖書 |
 |
禪與生活 作者:鈴木大拙 / 譯者:劉大悲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6-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禪與生活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鈴木大拙(すずき だいせつ、D.T.Suzuki,1870年10月18日-1966年7月12日)
本名貞太郎〔ていたろう〕,別號也風流居士。日本石川縣金澤市人。曾於1963年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1]。有「世界禪者」之譽。著有《般若經の哲學と宗教》、《華嚴の研究》、《禪的研究》、《禪的諸問題》、《禪思想史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佛教與基督教》。
主要思想主張之一為「自己作主」。
譯者簡介
劉大悲(1894年11月-1984年4月)
又名文厚,四川古宋人,森林學家。
巴黎大學理科博士。留法期間獲授大學官獎章與騎士勛章。1933年返回中國,出任國民政府實業部技正,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森林法》,1934年完成。1949年在台灣擔任公職至退休,1977年移民至紐西蘭。1983年8月取道香港回到成都,次年4月逝世,安葬老家四川古宋。
鈴木大拙(すずき だいせつ、D.T.Suzuki,1870年10月18日-1966年7月12日)
本名貞太郎〔ていたろう〕,別號也風流居士。日本石川縣金澤市人。曾於1963年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1]。有「世界禪者」之譽。著有《般若經の哲學と宗教》、《華嚴の研究》、《禪的研究》、《禪的諸問題》、《禪思想史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佛教與基督教》。
主要思想主張之一為「自己作主」。
譯者簡介
劉大悲(1894年11月-1984年4月)
又名文厚,四川古宋人,森林學家。
巴黎大學理科博士。留法期間獲授大學官獎章與騎士勛章。1933年返回中國,出任國民政府實業部技正,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森林法》,1934年完成。1949年在台灣擔任公職至退休,1977年移民至紐西蘭。1983年8月取道香港回到成都,次年4月逝世,安葬老家四川古宋。
目錄
譯者序
禪對西方世界的意義 / William Barrett
第一章 禪的意義
第二章 禪與一般佛教
第三章 禪的歷史
第四章 悟
第五章 禪的實際開導方法
第六章 無理性的理性:公案的運用
第七章 禪的無心說
第八章 自然在禪學中所占的地位
第九章 存在主義、實用主義與禪
名詞索引
鈴木大拙 年表
禪對西方世界的意義 / William Barrett
第一章 禪的意義
第二章 禪與一般佛教
第三章 禪的歷史
第四章 悟
第五章 禪的實際開導方法
第六章 無理性的理性:公案的運用
第七章 禪的無心說
第八章 自然在禪學中所占的地位
第九章 存在主義、實用主義與禪
名詞索引
鈴木大拙 年表
序
譯者序
一
大多數人一聽到「談禪說道」,總以為這是非常抽象的,其實,禪是非常具體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經驗,無一不是禪機,所以禪不能離開生活,離開生活便沒有禪。只要我們看一看禪的起源,便知道上面所說的話不虛了。
相傳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說法,他手中拿著一朵花,面對大眾,一語不發。這時大眾面面相覷,唯有摩訶迦葉發出會心的微笑。於是釋迦牟尼便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禪就在拈花微笑之間誕生了。這段傳說頗富於浪漫色彩,也許不是真實的,但不論真實與否,其表現禪的起源方式,卻把握了禪的根本精神。
迦葉之後,禪在印度傳了二十七代。到了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便東來中國。達摩來中國後,成為中國禪宗的初祖,六傳至六祖慧能大師,便展開了中國禪宗的蓬勃氣象。禪在中國之所以能夠發揚光大,乃由於中國人所具有的實踐精神。
二
禪在本質上是一種見性功夫,是掙脫桎梏走向自由之道。它使我們啜飲生命的泉源,因而使有限的人類從這個世界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我們生命中本身具有一切使人類獲得幸福的活力,只是由於我們的迷妄,才使這種活力受到阻礙而得不到適當表現的機會。禪的目的就是突破迷妄,使我們隱藏的活力得以自由地展開,使我們內心一切創造的動力得以自由地發揮。迷雲消失之後,我們便可以看到自己的本性了,也就是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了,現在,我們便認識生命的意義,便知道生命不是盲目的鬥爭,雖然我們並不確切知道生命的根本目的是什麼,然而其中卻有某些東西使我們在生活過程中感到無限的幸福。
佛家認定生命是痛苦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只要生命是一種鬥爭,是有限和無限、肉體和精神之間的鬥爭,就一定是痛苦的,但是為什麼有許多鬥爭呢?那是由於人的理智作用。理智使人起分別心,分別心一起,便產生二法對待。人為了解決生命中許多矛盾對立的問題,便產生語言文字等符號,因而從事概念分析,可是概念分析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徒然加深了二法對待,更加抓不住本來面目了。所以禪要超越名言概念,去捕捉事實的本來面目,禪認為在事實與我們自己之間並沒有任何中間物,一切有限和無限、肉體和精神之間的鬥爭,都是理智的虛構物。當我們感到饑餓時,便吃東西,當我們感到疲倦時,便去休息,這又哪來有限無限之別呢?只有當理智介入生活中而扼殺生命時,我們才中止生活而以為自己缺乏什麼東西。其實,我們本來具備,本來自由自在,有限和無限之間自開始就不必有任何鬥爭,我們竭心追求的平和,根本不曾片刻離開過我們。
蘇東坡有一首詩: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到來無一事,
廬山煙雨浙江潮。
詩中所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青原惟信禪師說:「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既參禪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可是禪悟之後真能得個休息處時,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了。」這裡所表示的也是這個意思。所以,禪家便有所謂:
教外別傳,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
禪家不訴諸名言知識,只直接訴諸親身體驗的事實,而親身體驗是生活。有一次,一個和尚問睦州:「我們每天要穿衣吃飯,如何能避免這些呢?﹂睦州回答說:「穿衣吃飯。」這和尚便說:「我不懂你的意思。「」睦州又回答說:「如果你不懂我的意思,就請穿衣吃飯吧。」人都是有限的,無法活在時空之外;只要我們活在這大地上,就無法抓住無限者,怎能擺脫存在的限制呢?這也許是那和尚所提的第一個問題中的意思。對於這個問題,睦州的回答是:我們一定在有限中尋求解脫;如果你真想追求超越的東西,這個念頭就會使你和這個世界脫節,這等於毀滅你自己,你總不會為了追求解脫而犧牲生命吧。所以,你就得穿衣吃飯,而在穿衣吃飯之中尋求自由之道。和尚不明瞭這層道理,因此,睦州繼續說:不論你了解不了解,都要活在有限之中,涅槃要在生死中去求。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並不是煩惱之外另有菩提,生死之外另有涅槃,而是菩提就在煩惱之中,涅槃就在生死之中,迷時為生死煩惱,悟時即菩提涅槃。這就像明和暗一樣,並不是先有暗,然後又帶來明,明暗自始就是一個東西,暗之變為明只是發生在我們內心,因此有限的即是無限的,無限的也是有限的。兩者不是分離的東西,只是我們的理智作用逼著我們把它們分開,從邏輯上看,這也許是睦州回答那和尚話中所含的意義。
現實世界就是理想世界,理想世界要在現實世界中去求,並不是離開現實世界另有一個理想世界可得。解脫要在現實生活中求,離開現實生活別無解脫可得。所以當和尚們請百丈涅槃禪師說法時,百丈叫他們先去田中工作,等工作完了以後再說佛法。可是當他們照著百丈的話做了之後,再請百丈說法時,百丈卻一語不發,只對和尚們張開雙臂。也許禪裡面終究沒有什麼神祕,一切都擺在我們眼前,只要我們穿衣吃飯、耕田種菜,就完成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需要做的工作,而無限也在我們身上實現了。
三
人的生活無法離開自然,人無法活在自然之外,人的存在根源於自然。所以,對禪來說,人與自然之間,沒有對立,彼此之間往往有一種親切的了解。青原惟信所謂:「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既參禪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可是禪悟之後得個休息處時,見山又是山。」禪就在其中。
未參禪時,見山是山,這是從常識觀點和理智分別心去看山,這時的山是沒有生命的山。既參禪後,我們不把山看作聳立在自己面前的自然物,把它化為與萬物合一,山便不再是山,可是當我們真正禪悟之後,便已把山融合在自己生命裡面,也把自己融合在山裡面,山才真正是山,這時的山是有生命的山。
這樣,一旦我們認識自然為自然,自然便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自然不再是與我們漠不相關的陌生者。我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在我之中。我與自然,不但彼此參與,更是根本的合一。因此,山是山,水是水,我之所以能夠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因為我在山水之中,山水也在我之中。我見山如是,山見我亦如是,我之見山亦即山之見我。「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亦如是。」如果沒有這種合一,就不會有自然。禪所謂的「本來面目」,就是要在這裡加以體會的。當我們達到這個階段時,純粹主觀即純粹客觀,主體即客體,人與自然完全合一。不過,這種合一並不含有為此而失彼的意思。山並沒有消失,我沒有吞沒山;山仍然聳立在我們面前。山也沒有淹沒我,我仍然保留著我的自覺。這是禪家的真如妙境。
那麼禪是不是神祕主義呢?禪不是神祕主義,更不是西方式的神祕主義,因為西方的神祕主義者自新柏拉圖學派的普洛丁納斯(Plotinus)以來,都想穿過自然或感官世界的障幕去體驗與更高實在者的直接合一,可是禪家否認這種將實在分為較低和較高兩個層面的二法對待。對禪家來說,較高世界和較低世界根本是一個世界;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根本是一個世界。而且,在神祕主義者身上產生意識滅絕現象或半恍惚狀態,可是禪家不會亡失於境中,仍然保留自覺,所以禪絕對不是神祕主義。
四
現代世界普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那麼,東方的禪道對現代人類的生活,能有什麼意義呢?我想,其意義是很深長的。因為西方文化到今天已進入窮巷,其文化上的缺失已使現代人迷失自己,所以現代人雖大多數仍然過著西方文化孕育出來的生活方式,但西方文化的深處已開始動搖。
西方傳統有兩大淵源即希伯來和希臘。兩者在根本精神上都是「二元」對立的。就後者來說,希臘人基於智理的觀點把實在分割為二,例如柏拉圖,他把實在分割為睿智世界和感官世界。希臘人的偉大成就,乃是把人類看作理性的動物。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不但把理性看作最高的功能,甚至把它當作我們整個人格的重心。柏拉圖在其洞窟的寓言裡,描寫人類好像生活在洞窟中,面對牆壁,洞外的光將外界事物投影到洞內牆壁上,人透過牆上的投影而認識外界。這裡所說的牆上投影象徵人類的名言概念,透過投影認識外界,就是通過名言概念認識世界,人與世界之間有一中間物,人不能直接認識世界,只能透過名言概念間接認識世界。這個觀點對西方世界的影響非常深刻,使西方文化走上知性主義道路,造成科學的蓬勃發展。於是西方人把自然完全看成為一種與人類對立的東西,人與自然之間沒有親近的可能;人只能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然而人非但未能征服自然,而且被自然的廣大無限所震懾,感到恐怖戰慄,更因為過分傾向理性主義,情意生活便相對萎縮,人格的完整性受到割裂,生活抽象化,於是人便迷失在自然中,內外都無依憑,這是西方文化的危機,也是現代人生活中的根本危機。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得曾經告訴過我們,理性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可是啟蒙運動的遺風卻迷信科學萬能,直到科學本身產生矛盾後,本世紀的科學才承認康得的觀點,海森堡︵Heisenberg︶的不定性原理和其他數學上的缺陷,都表現出理性的有限性。現代哲學家更從哲學上說明理性的缺陷,當代西方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哲學根本是一大錯誤。產生二法對待的理智,不但使人與世界離裂,也與自己離裂。
在理性主義冰冷的空氣中,人凍僵了,所以早有齊克果、巴斯葛、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義出現,雖然他們的呼聲蓋不住理性主義的洪流,卻也掀起了大洪流裡面的小浪花,到了本世紀,文學藝術方面,興起了反理性主義趨勢。現代藝術突破了保守的傳統,向東方尋求創造的靈感,勞倫斯(D. H. Lawrence)和喬埃斯(James Joyce)的小說,也脫離傳統的風格,前者反對無血色的理性主義文化而訴諸人的直覺,後者則打破美醜等二元對立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存在主義,更掀起了一股反傳統運動。存在主義者反對抽象生活,要求完整的具體生活,突破理性的藩籬而訴諸直覺的感受,從這一點看,存在主義可說是西方文化到東方文化的一座橋梁,存在主義之強調具體生活和禪家之強調切身體驗,頗有相似之處。然而,存在主義到底是西方傳統下產生出來的反動,與禪雖有相似之處,卻也有不同的地方。禪離不開生活,在生活中得到禪悟之後,產生禪悟的喜悅,自由自在。可是存在主義者在生活中所得到的卻是苦悶,因為存在主義者的無限自由,帶來無限責任,面對著無限責任,使人有畏懼焦慮之感。齊克果、沙特都有這種看法。沙特的煩惱是苦於物我不透,而人的自由又復可怕,人註定要領受苦悶,真是解脫無門。
再者,存在主義運動當初是在文學中表現出來,事實上也只有文學的方式才能表達具體的生活內容。可是,後來存在主義成為系統化思想,一旦系統化,就與活的生命脫節,最後又落入理智思想的陷阱中。禪雖也訴諸文字般若,但文字般若的目的是觀照般若而證實相般若,所以,禪始終抱著﹁言語道斷﹂的觀點,以語言破語言而把握本來面目。
最後,我們可以說,存在主義雖是西方文化接通東方文化的橋梁,雖是提醒現代人回到具體生活的呼聲,但它並沒有完成使命,所以,要拯救現代文化的危機,要使現代人不迷失自己而回到真正人的具體生活,東方的禪道將要擔負重大的責任。
一九七一年七月譯者於臺北
一
大多數人一聽到「談禪說道」,總以為這是非常抽象的,其實,禪是非常具體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經驗,無一不是禪機,所以禪不能離開生活,離開生活便沒有禪。只要我們看一看禪的起源,便知道上面所說的話不虛了。
相傳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說法,他手中拿著一朵花,面對大眾,一語不發。這時大眾面面相覷,唯有摩訶迦葉發出會心的微笑。於是釋迦牟尼便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禪就在拈花微笑之間誕生了。這段傳說頗富於浪漫色彩,也許不是真實的,但不論真實與否,其表現禪的起源方式,卻把握了禪的根本精神。
迦葉之後,禪在印度傳了二十七代。到了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便東來中國。達摩來中國後,成為中國禪宗的初祖,六傳至六祖慧能大師,便展開了中國禪宗的蓬勃氣象。禪在中國之所以能夠發揚光大,乃由於中國人所具有的實踐精神。
二
禪在本質上是一種見性功夫,是掙脫桎梏走向自由之道。它使我們啜飲生命的泉源,因而使有限的人類從這個世界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我們生命中本身具有一切使人類獲得幸福的活力,只是由於我們的迷妄,才使這種活力受到阻礙而得不到適當表現的機會。禪的目的就是突破迷妄,使我們隱藏的活力得以自由地展開,使我們內心一切創造的動力得以自由地發揮。迷雲消失之後,我們便可以看到自己的本性了,也就是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了,現在,我們便認識生命的意義,便知道生命不是盲目的鬥爭,雖然我們並不確切知道生命的根本目的是什麼,然而其中卻有某些東西使我們在生活過程中感到無限的幸福。
佛家認定生命是痛苦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只要生命是一種鬥爭,是有限和無限、肉體和精神之間的鬥爭,就一定是痛苦的,但是為什麼有許多鬥爭呢?那是由於人的理智作用。理智使人起分別心,分別心一起,便產生二法對待。人為了解決生命中許多矛盾對立的問題,便產生語言文字等符號,因而從事概念分析,可是概念分析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徒然加深了二法對待,更加抓不住本來面目了。所以禪要超越名言概念,去捕捉事實的本來面目,禪認為在事實與我們自己之間並沒有任何中間物,一切有限和無限、肉體和精神之間的鬥爭,都是理智的虛構物。當我們感到饑餓時,便吃東西,當我們感到疲倦時,便去休息,這又哪來有限無限之別呢?只有當理智介入生活中而扼殺生命時,我們才中止生活而以為自己缺乏什麼東西。其實,我們本來具備,本來自由自在,有限和無限之間自開始就不必有任何鬥爭,我們竭心追求的平和,根本不曾片刻離開過我們。
蘇東坡有一首詩: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到來無一事,
廬山煙雨浙江潮。
詩中所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青原惟信禪師說:「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既參禪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可是禪悟之後真能得個休息處時,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了。」這裡所表示的也是這個意思。所以,禪家便有所謂:
教外別傳,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
禪家不訴諸名言知識,只直接訴諸親身體驗的事實,而親身體驗是生活。有一次,一個和尚問睦州:「我們每天要穿衣吃飯,如何能避免這些呢?﹂睦州回答說:「穿衣吃飯。」這和尚便說:「我不懂你的意思。「」睦州又回答說:「如果你不懂我的意思,就請穿衣吃飯吧。」人都是有限的,無法活在時空之外;只要我們活在這大地上,就無法抓住無限者,怎能擺脫存在的限制呢?這也許是那和尚所提的第一個問題中的意思。對於這個問題,睦州的回答是:我們一定在有限中尋求解脫;如果你真想追求超越的東西,這個念頭就會使你和這個世界脫節,這等於毀滅你自己,你總不會為了追求解脫而犧牲生命吧。所以,你就得穿衣吃飯,而在穿衣吃飯之中尋求自由之道。和尚不明瞭這層道理,因此,睦州繼續說:不論你了解不了解,都要活在有限之中,涅槃要在生死中去求。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並不是煩惱之外另有菩提,生死之外另有涅槃,而是菩提就在煩惱之中,涅槃就在生死之中,迷時為生死煩惱,悟時即菩提涅槃。這就像明和暗一樣,並不是先有暗,然後又帶來明,明暗自始就是一個東西,暗之變為明只是發生在我們內心,因此有限的即是無限的,無限的也是有限的。兩者不是分離的東西,只是我們的理智作用逼著我們把它們分開,從邏輯上看,這也許是睦州回答那和尚話中所含的意義。
現實世界就是理想世界,理想世界要在現實世界中去求,並不是離開現實世界另有一個理想世界可得。解脫要在現實生活中求,離開現實生活別無解脫可得。所以當和尚們請百丈涅槃禪師說法時,百丈叫他們先去田中工作,等工作完了以後再說佛法。可是當他們照著百丈的話做了之後,再請百丈說法時,百丈卻一語不發,只對和尚們張開雙臂。也許禪裡面終究沒有什麼神祕,一切都擺在我們眼前,只要我們穿衣吃飯、耕田種菜,就完成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需要做的工作,而無限也在我們身上實現了。
三
人的生活無法離開自然,人無法活在自然之外,人的存在根源於自然。所以,對禪來說,人與自然之間,沒有對立,彼此之間往往有一種親切的了解。青原惟信所謂:「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既參禪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可是禪悟之後得個休息處時,見山又是山。」禪就在其中。
未參禪時,見山是山,這是從常識觀點和理智分別心去看山,這時的山是沒有生命的山。既參禪後,我們不把山看作聳立在自己面前的自然物,把它化為與萬物合一,山便不再是山,可是當我們真正禪悟之後,便已把山融合在自己生命裡面,也把自己融合在山裡面,山才真正是山,這時的山是有生命的山。
這樣,一旦我們認識自然為自然,自然便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自然不再是與我們漠不相關的陌生者。我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在我之中。我與自然,不但彼此參與,更是根本的合一。因此,山是山,水是水,我之所以能夠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因為我在山水之中,山水也在我之中。我見山如是,山見我亦如是,我之見山亦即山之見我。「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亦如是。」如果沒有這種合一,就不會有自然。禪所謂的「本來面目」,就是要在這裡加以體會的。當我們達到這個階段時,純粹主觀即純粹客觀,主體即客體,人與自然完全合一。不過,這種合一並不含有為此而失彼的意思。山並沒有消失,我沒有吞沒山;山仍然聳立在我們面前。山也沒有淹沒我,我仍然保留著我的自覺。這是禪家的真如妙境。
那麼禪是不是神祕主義呢?禪不是神祕主義,更不是西方式的神祕主義,因為西方的神祕主義者自新柏拉圖學派的普洛丁納斯(Plotinus)以來,都想穿過自然或感官世界的障幕去體驗與更高實在者的直接合一,可是禪家否認這種將實在分為較低和較高兩個層面的二法對待。對禪家來說,較高世界和較低世界根本是一個世界;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根本是一個世界。而且,在神祕主義者身上產生意識滅絕現象或半恍惚狀態,可是禪家不會亡失於境中,仍然保留自覺,所以禪絕對不是神祕主義。
四
現代世界普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那麼,東方的禪道對現代人類的生活,能有什麼意義呢?我想,其意義是很深長的。因為西方文化到今天已進入窮巷,其文化上的缺失已使現代人迷失自己,所以現代人雖大多數仍然過著西方文化孕育出來的生活方式,但西方文化的深處已開始動搖。
西方傳統有兩大淵源即希伯來和希臘。兩者在根本精神上都是「二元」對立的。就後者來說,希臘人基於智理的觀點把實在分割為二,例如柏拉圖,他把實在分割為睿智世界和感官世界。希臘人的偉大成就,乃是把人類看作理性的動物。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不但把理性看作最高的功能,甚至把它當作我們整個人格的重心。柏拉圖在其洞窟的寓言裡,描寫人類好像生活在洞窟中,面對牆壁,洞外的光將外界事物投影到洞內牆壁上,人透過牆上的投影而認識外界。這裡所說的牆上投影象徵人類的名言概念,透過投影認識外界,就是通過名言概念認識世界,人與世界之間有一中間物,人不能直接認識世界,只能透過名言概念間接認識世界。這個觀點對西方世界的影響非常深刻,使西方文化走上知性主義道路,造成科學的蓬勃發展。於是西方人把自然完全看成為一種與人類對立的東西,人與自然之間沒有親近的可能;人只能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然而人非但未能征服自然,而且被自然的廣大無限所震懾,感到恐怖戰慄,更因為過分傾向理性主義,情意生活便相對萎縮,人格的完整性受到割裂,生活抽象化,於是人便迷失在自然中,內外都無依憑,這是西方文化的危機,也是現代人生活中的根本危機。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得曾經告訴過我們,理性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可是啟蒙運動的遺風卻迷信科學萬能,直到科學本身產生矛盾後,本世紀的科學才承認康得的觀點,海森堡︵Heisenberg︶的不定性原理和其他數學上的缺陷,都表現出理性的有限性。現代哲學家更從哲學上說明理性的缺陷,當代西方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哲學根本是一大錯誤。產生二法對待的理智,不但使人與世界離裂,也與自己離裂。
在理性主義冰冷的空氣中,人凍僵了,所以早有齊克果、巴斯葛、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義出現,雖然他們的呼聲蓋不住理性主義的洪流,卻也掀起了大洪流裡面的小浪花,到了本世紀,文學藝術方面,興起了反理性主義趨勢。現代藝術突破了保守的傳統,向東方尋求創造的靈感,勞倫斯(D. H. Lawrence)和喬埃斯(James Joyce)的小說,也脫離傳統的風格,前者反對無血色的理性主義文化而訴諸人的直覺,後者則打破美醜等二元對立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存在主義,更掀起了一股反傳統運動。存在主義者反對抽象生活,要求完整的具體生活,突破理性的藩籬而訴諸直覺的感受,從這一點看,存在主義可說是西方文化到東方文化的一座橋梁,存在主義之強調具體生活和禪家之強調切身體驗,頗有相似之處。然而,存在主義到底是西方傳統下產生出來的反動,與禪雖有相似之處,卻也有不同的地方。禪離不開生活,在生活中得到禪悟之後,產生禪悟的喜悅,自由自在。可是存在主義者在生活中所得到的卻是苦悶,因為存在主義者的無限自由,帶來無限責任,面對著無限責任,使人有畏懼焦慮之感。齊克果、沙特都有這種看法。沙特的煩惱是苦於物我不透,而人的自由又復可怕,人註定要領受苦悶,真是解脫無門。
再者,存在主義運動當初是在文學中表現出來,事實上也只有文學的方式才能表達具體的生活內容。可是,後來存在主義成為系統化思想,一旦系統化,就與活的生命脫節,最後又落入理智思想的陷阱中。禪雖也訴諸文字般若,但文字般若的目的是觀照般若而證實相般若,所以,禪始終抱著﹁言語道斷﹂的觀點,以語言破語言而把握本來面目。
最後,我們可以說,存在主義雖是西方文化接通東方文化的橋梁,雖是提醒現代人回到具體生活的呼聲,但它並沒有完成使命,所以,要拯救現代文化的危機,要使現代人不迷失自己而回到真正人的具體生活,東方的禪道將要擔負重大的責任。
一九七一年七月譯者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