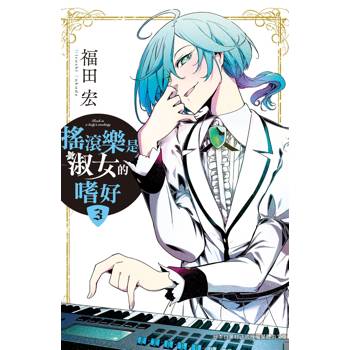致謝 5
張家家族成員一覽 7
序言 11
第一章 婚禮 001
第二章 生育 009
第三章 擇木而棲 017
第四章 合肥精神 024
第五章 祖母 039
第六章 母親 060
第七章 父親 073
第八章 興學 101
第九章 保母列傳 115
第十章 元和 129
第十一章 允和 160
第十二章 兆和 193
第十三章 充和 256
關於資料來源 287
註釋 288
參考書目 311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合肥四姐妹:一段歷史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合肥四姐妹:一段歷史 作者:金安平 / 譯者:鄭至慧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08-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8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中文書 |
$ 288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合肥四姐妹:一段歷史
張家四姐妹,指的是蘇州合肥張家。出身名門,曾祖張樹聲是晚清高官,父親張吉友是民初教育家,四姐妹則是第一批中國公學預科女生。她們是:大姐張元和(嫁崑曲名家顧傳玠),二姐張允和(嫁給語言學家周有光),三姐張兆和,四妹張充和(嫁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前面三個姐妹,嫁的都是當時社會名流。而三姐張兆和,因為沈從文的追求,名聲最響。
在中國近代史上知名程度僅次於宋家三姐妹,這四位女子分別於1907~1914年出生,見證了時代的劇變以及中國傳統仕宦階級進入現代後的改變。本書從1860年太平天國之亂寫起,一直寫到革命後20世紀的中國面貌,藉著四位女子充滿詩文藝術的生活,穿插她們的日記、信件與訪談,串綴出個人歷史在大歷史中的面貌。
作者簡介:
金安平(Annping Chin)
1950年出生於台灣,1962年隨家人移民美國維吉尼亞州的瑞奇蒙(Richmond)。後於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東亞研究所博士學位,並與其夫婿史景遷合著有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現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
譯者簡介:
鄭至慧
文字工作者。譯有《夢迴藻海》、《瓶中美人》、《白色旅店》等書,著有《菜場門口遇見馬》、《她鄉女紀》。
目錄
致謝 5
張家家族成員一覽 7
序言 11
第一章 婚禮 001
第二章 生育 009
第三章 擇木而棲 017
第四章 合肥精神 024
第五章 祖母 039
第六章 母親 060
第七章 父親 073
第八章 興學 101
第九章 保母列傳 115
第十章 元和 129
第十一章 允和 160
第十二章 兆和 193
第十三章 充和 256
關於資料來源 287
註釋 288
參考書目 311
張家家族成員一覽 7
序言 11
第一章 婚禮 001
第二章 生育 009
第三章 擇木而棲 017
第四章 合肥精神 024
第五章 祖母 039
第六章 母親 060
第七章 父親 073
第八章 興學 101
第九章 保母列傳 115
第十章 元和 129
第十一章 允和 160
第十二章 兆和 193
第十三章 充和 256
關於資料來源 287
註釋 288
參考書目 311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金安平 譯者: 鄭至慧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08-22 ISBN/ISSN:9571343579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