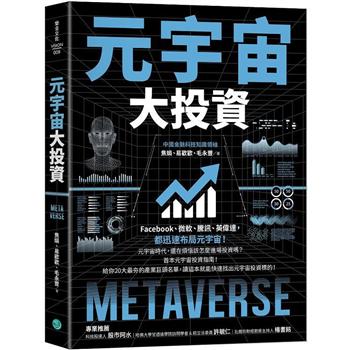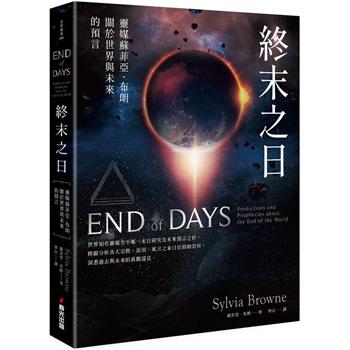前言
人生就像是火車之旅,一站過了一站,似乎坐著不動,但景色轉眼全非。我用火車形容我的人生旅途,是我對火車的偏愛。從小時候冒著黑煙、轟隆轟隆、震耳欲聾的火車,到今天飛馳如燕的超子彈列車,反映人生的經歷、時代的嬗變、世紀的更新。火車上看到形形色色的乘客,有的坐一站就下車,有的陪伴你整天整夜,變成多年老友般,向你訴說他的家人、他的事業、他的憂愁、他的欣喜。無論家人、親友、學生、同事、陌生人,不都像同車的乘客一般嗎?長聚短聚、不斷追求著什麼、尋找著什麼?
少年時代,人類學改變了我的命運,人類學讓人類學家走上永不停歇的田野之旅。為了追求新知,為了田野調查,我飄洋過海,跨越美洲、亞洲、大洋洲。旅程愈走愈遠,遠離家鄉,每次回到台灣小停,反倒像火車到達似曾相識的一站,還沒看清四周,便又悄悄開動前行了。
十八歲離家遠行,獨創我個人的新世界,在這本書裡,我寫我個人的故事,寫旅途上的種種回憶,多是常存腦中的一些小事,也是走進人類學經過的大站和小站。人類學的訓練,使我的思考分不開過去與現在,分不開工作和假期,分不開居家和田野,分不開舊厝與異地,也分不開個人與世界。
自從維蘭進入我的生活,旅行有了伴侶,開啟兩人同行的新世界。從二十多歲開始,
我們渡海求學,環遊幾大洲,馬不停蹄,年年飛行萬里,結伴遨翔廣闊有趣的田野,記憶中的旅途也愈來愈美味新奇。
我用「故鄉」、「田野」和「火車」寫出我人生的三部曲,我如何成為人類學家。第一部曲從北京出發,回到遙遠的老家南投,我從六歲開始領悟,我四周充滿了各種不同且交織共存的文化,我的生活多元又多變。我寫祖母,她是台灣傳統文化的代表,我欽佩祖母的知識、飲食技巧、神明信仰、教導兒孫的智慧,這些都是逐漸消逝的台灣農村文化。我從幼時的舊厝,看到住在祖先老屋裡的大家族,隨著都市建設和經濟劇變,而四散分離。從南投第二國小到台北國語實小,從師大附中到台中二中,我的「故鄉」生活,圍繞在幾個同時 存在而又階級明顯對立的文化世界。 回想我的成長,經過中國古老的古都文化、日本殖民地殘存文化、台灣蛻變中的鄉鎮文化、族群匯集的台北文化、台中軍眷區的難民文化;而在我進入台大之前,又經歷了南遷的最高學院文化。
在每一個有特色的文化裡,我都能自在地生活,習慣地扮演文化中的一分子。也許這是一種本錢,是我日後熟練表現人類學家的本領。家庭的不幸遭遇,帶給我多年內心痛苦和掙扎,但是我的自信和幻想未受限制,反而養成人類學家冷眼觀察外在世界的樂趣。
我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動筆寫我兒時的回憶,那是維蘭淋巴癌動過大手術兩年之後。那年暑假,我們從香港回夏威夷度假三個月,經台北小停三天,沒想到回到夏威夷次日,維蘭就進了醫院,發現腎臟幾乎衰竭,幾個醫生都查不出病因,州政府衛生局派人來了,怕從亞洲帶來不明病菌,醫生束手無策,只靠禁食和打點滴。住院兩週後,情況稍緩,我們決定維蘭必須繼續在夏威夷療養,於是我再向香港中文大學請假一年,靠同事們的諒解和支持,不致耽誤系務和課程。
本書第一部分「故鄉」的初稿,大致在一九九八年到九九年夏天之間完成。之後我們回香港一學期,我當時早已向校方提出,堅持要求次年讓我提早退休。我在夏威夷獨自靜坐,回想我的一生,腦中經常出現許多兒時影像、在我身邊的人物:外婆、父母、奶媽、祖母、叔叔、堂兄弟以及許許多多同學。兒時所經歷的事件至今仍歷歷如新,帶給我極大的衝擊和覺醒,就像一幕幕電影片段一般。我寫兒時回憶的時候,有所領悟,這是人類學的訓練,腦中自然歸類,放映出有共同背景的畫面。腦中出現的一景一物,都是當時我默默觀察四周、學習新的語言和文化,看到周遭的文化劇變和族群對立,到老而無法忘懷的事件。
我寫完第一部曲初稿之後兩年,讀了愛德華. 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A Memoir),才瞭解回憶兒時對人生的重要性,為什麼兒時記憶裡的「故鄉」人物深藏內心深處 。薩伊德是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系名教授,二○○三年因癌症過世。他一生學術成就斐然,特別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 一書, 解構歐美「東方學家」所代表的東方(亞洲包括阿拉伯人的世界),跟實際文化社會毫無關係,只是帝國主義為了統治東方而營造出來的想像中的東方。此書在八○年代以後,全盤轉變歐美亞洲研究學界的思考方向。但是薩伊德在美國社會和政界更為出名,保守的政客們受不了他嚴厲批判,美國中東政策的制訂人認為他是為巴勒斯坦復國而搖旗吶喊的偏激知識分子。
《鄉關何處》是他在九○年代中期罹患血癌時手書的回憶錄,細膩地道出兒時在出 生地耶路撒冷(當時還屬於巴勒斯坦)的親朋好友、在開羅長期定居的家庭生活,以及後來求學時代所聞所見。此書歷經五年才由助手編輯出版。雖然薩伊德的父親早在他出生前就成為美國公民,而他從小就讀開羅的英語貴族學校,後來一路在美國上貴族中學,畢業於哈佛大學。我看電視轉播他的公開演講,他一口美國土生土長的英語,但他臨老卻寫出了一生放逐異國的感傷和困境,他心中懷念的故鄉耶路薩冷已經變成以色列的聖地,是巴勒斯坦人永遠回不去的故鄉,《鄉關何處》敘說移民被迫飄離,連根拔起,在新居文化裡格格不入。薩伊德雖是英美文化的菁英,卻一輩子背著過客的情懷。這部回憶錄讓我深深感受薩伊德內心深處的悲痛,想到我離家十年,因為不准出國的底案,飛過家門而不敢停留,為了避免失去自由,之後每次到台灣都是短短兩天「過境」,薩伊德兒時「故鄉」的失落和感傷,於我心有戚戚焉!(註一)
我的第二部曲〈田野〉,代表人類學家的生命主題,描寫一個人類學家的學習過程,經年累月在遠方他鄉的田野生活,見證人類學家的養成必須橫跨多麼複雜、多麼廣闊的世界。
我走進人類學界是個極為獨特的例子。高中畢業後,不得已棄學求職,沒想到偶然機會進入當時還在「籌備」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更沒想到做了中國民族學前驅凌純聲所長的學徒,跟著所裡的前輩們跑遍台灣「山地」,學做人類學田野調查。在我出國之前,以青少年之身,累積了八年台灣原住民的田野經驗,這是我學術生涯的幸運開端,也是人類學同行極為少見的。後來在美國求學,面對很多新鮮陌生的科目,常能舉一反三,這是台灣田野實地心得的功勞。
第二部「田野」工作的回憶,以較大的篇幅,描寫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兩年的田野調查,反映人類學家寫自傳的傳統。 許多歐美人類學家都把自己的經歷寫成回憶錄式的 自傳,敘述如何走進人類學,如何到別的社會研究別人的文化。所描述的田野調查,通常是到最邊遠的異鄉,逗留最久、受苦最多的一次田野工作,而多半是為了收集博士論文資料而去的田野。回憶如何在非洲高原,或南美森林,或新幾內亞的小島,研究其他人類學家還沒見過的部落,跟土人同住一年、兩年,忍受寂寞艱辛的日子,像瘋子一樣,偷偷記載土人一言一行。近 十年來有好幾位同行都出版了這類回憶錄(註二),這些自傳多半只在人類學同行之間流傳,讓閱讀的人會心的微笑,也讓後生學子得以借鏡,學習前輩的經驗,為將來遠赴他方做心理準備。我跟維蘭前後兩年住在赤道島國,碰到許多有趣的人物,當時雖有驚險和病痛,但現在都已忘了,只記得這些妙人趣事,代表著族群意識、種族和文化認同的實例,表現種族與文化的變幻無常,絕非大家想像中的一成不變。我描述的新幾內亞之旅,不過是此生五大田野工作的序曲,卻是我人類學成長中的重要一步。
人類學家就是一個旅人。我的第三部曲「火車」,寫出我從小到大旅途中的特別感受:無論是求學期間、田野考察、演講開會,或客居執教,在許多國家,都跟火車結下不解之緣。這 些看起來像旅行遊記的火車故事,也是人類學家到處不停觀察旁人生活的紀錄,反映了人類學家積習難改的田野壞習慣,也反映了人類學家旅行人生的快樂。
人類學家是個永不停息的旅人,一輩子都是個(半自願)放逐遷移的旅人,這有兩層理論意義:一方面是離家遠赴他方,一方面則是思想之旅,經常得暫時放下自己文化的思考方式,學習被研究的「土人」的思考模式。可是我在本書最後一章〈吳伯大夢〉中寫了十多年前回台灣長住一段時間的感受,那次回到自己的故鄉,反而好像到了他鄉異國,離家久遠的旅人,不知不覺間失落了兒時的故鄉,也許等到哪天故鄉的火車重回過去的舒適和享受,能讓我回到起站,再次看到故鄉。
二○○五年二月初稿於夏威夷檀香山
致謝:初稿完成以後,維蘭仔細地讀過幾遍,做了不少改正和建議。胞弟燕鳴、蒲茵夫婦將初稿送去打字,跑了不少路,並親自用電腦修改許多錯字。李亦園師在煩忙之中看稿、為本書寫序,並介紹出版社。李先生和師母對我倆多年的照顧和關心 ,我們感激不盡,特此再致謝意。時報出版公司盡心盡力為本書編排、設計封面,特別感謝諸位費時費力,促使本書出版。
註一:薩伊德在這本書, 還有其他演講稿裡,特別提到他五十年後頭一次(一九八八) 回到出生地耶路撒冷,猛然驚悟他的出生地已經不存在了。他回去探望故居,每經過一道關口, 以色列的警衛 就從頭盤問他,看到他美國護照上寫著出生地是耶路撒冷,便問他:「你什麼時候離開以色列的?」他大聲回答:「我是一九四七年離開巴勒斯坦的。」因為那年以色
列侵佔了巴勒斯坦,他們全家被驅逐離境,搬到開羅。接著又問他:「你在耶路撒冷還有親人嗎?」他回答:「一個也沒有。」時突然心中湧出無以名狀的悲哀。
以色列邊境的查問是世界有名的,我跟維蘭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從香港經哥本哈根去了一趟
耶路撒冷,回程在海法的班哥潤機場辦登機手續時,受到安全人員有史以來最長的盤問:
1.你們兩個人有關係嗎?
答:有。
2.什麼關係?
答:我們是夫妻。
3.你們為什麼來以色列?
答;我接受耶路撒冷大學兒童教育研究所的邀請來開研討會。
4.誰給你買的飛機票?
答:是主辦單位托耶路撒冷某旅行社買的。
5.為什麼要經過哥本哈根?
答:這是旅行社安排的,這是經北極最短的路線,而且票價也較合理。
6.為什麼主辦人要請你?
答:因為我是研究中國幼兒教育的專家,主辦人大概看過我寫的書而知道我。
7.你認識他嗎?
答:在這次見面之前並不認識。
8.有什麼人跟你接觸過?
答:除了主辦單位、開會參加者、住宿的國家學術中心、國會、市政府之外,沒見過別人。
9.有沒有路過別的地方?
答:主辦單位帶我們到大衛城和伯利恆等地參觀過。
10.你們在耶路撒冷外出都坐什麼車?
答:除了集體坐大巴士,也坐過計程車。
11.有沒有一個人出去過?
答:有,在街上買東西和到銀行換錢(因為是我回答,沒提維蘭自己一 個人去博物館,還
上街逛過)。
12.有沒有跟別人碰過面?
答:沒有。
13.有沒有去過別人家?
答:有。去過總統懷茲曼的家,總統夫人招待我們喝下午茶。
14.行李有沒有在大廳裡擺放過?
答:沒有。
15.來到機場的一路上,行李有沒有離開過?
答:沒有。
16.你離開中國有多久?︵我們護照上寫著出生地北京︶
答:五十年了。
17.有沒有人托你們帶東西?
答:沒有。
18.從現在到行李托運進去,行李絕對不可以離身!
註二:多年前,馬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就出版過她的自傳《米德自傳》(Margaret Mead:A Life), 中文譯本由張恭啟先生翻譯(一九七七,台北,巨流),這本書在美國是暢 銷的通俗讀物。最近有下列幾位人類學家的學術性回憶錄,以人類學讀者為對象。
Von den Berghe, Pierre L.
1989 Stranger in Their Midst. Niwot, Co: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Hall, Edward T.
1992 An Anthropology of Everyday Life: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NY:Doubleday.
Schneider, David M.
1995 Schneider on Schneide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在國內用中文發表的人類學家自傳,以李亦園的《田野圖像》最為出名,全書出版資料見:李亦園著,一九九九,《田野圖像 ——我的人類學生涯》。台北,立緒文化。
第一章 祖母
1.從北京到南投
在我記憶裡,頭一次見到祖母,是在人山人海的熱鬧場面。我們從北京回到台灣,二叔、三叔、五叔來基隆接船,僱了兩輛大卡車,從基隆拉行李回到老家南投,我坐在卡車行李堆上,到了家門口,看到滿街的人群。
那天太陽很大,家對面正在上演野台歌仔戲,看戲的人都停下來,轉頭看我們,成群小孩立刻離開戲台,蜂擁到卡車四周。我坐在高大的卡車上,望著戲台一目瞭然;台上兩個女角,一下失去觀眾,雖然還在比劃走動著唱,但是眼神全集中在我家門口。記得我進了家門,從屋中往外一看,牆頭和牆外樹枝上全是小孩腦袋和會神觀望的眼睛。
幾十年後,我問過爸爸,才知道我們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回到老家的,當時我六歲,起先爸爸以為唱戲是為了歡迎我們回家,後來知道那天正好是拜拜敬神的日子。在人聲嘈雜、人群忙亂之中,有個滿臉笑容、黑衣黑褲的老太太,在人群中進進出出,大聲喊著,我聽不懂她在講什麼,好像在發號施令。這是祖母給我的第一印象。
祖母後來常在來訪的親友前講我從北京回來的笑話。她說:「我這個孫真悽慘,都轉來時尊(剛回來的時候),叫伊來呷ㄅㄥ(吃飯),伊走到桌腳,點點看看耶(安靜地看看),都行走呀(又跑開了)!」我自己並不記得有這回事,我聽阿嬤向別人訴說過幾次,不懂我為什麼不肯吃飯,也不知道該煮什麼給我吃。
我們在南投住了一年半,就搬到台北。剛回南投時,好像一直是祖母主廚,不記得母親下過廚。廚房還有一位粗壯的姑娘幫手,她早上來,晚上走。有天她帶我去她家玩,我們從田中小路走了很久,到達有高大煙囪的磚窯,原來是她家。我看工人做陶器,旋轉的輪子一下就變出一個罐子,又看到從模子裡壓出黃泥磚塊。臨走她包了一大塊黏土給我帶回家。我找鄰居小孩一起玩,教我做了幾艘軍艦,在太陽下曬乾,玩了好幾天,然後又泡在水中捏成鬼面具,其樂無窮。這是我自造玩具的開始,多半都是在鄉下學的。
祖母主廚,有天發生一件難忘的事。祖母在廚房燒菜,母親把我叫到裡間睡房,很神秘,低聲討好地說:「去跟你奶奶講,你愛吃煎的,不愛吃『撒』的。」我當時還不會講台灣話,不懂「煎」和「撒」的意思(煎是油炒,撒是水煮),更不懂我娘為什麼要我去跟奶奶說這些話。我走到廚房,跟灶前忙著煮飯的阿嬤,照娘的指示,大聲說了一遍。祖母好像只「哦」了一聲。我完成任務,回到裡屋,看到我娘滿面怒容,嚇了我一跳。我娘拉著我急促地對我說:「叫你跟你奶奶說『你』愛呷煎的,你怎麼說成『阮娘』愛呷煎的唉!你這麼笨..。」我覺得莫名其妙,不是你叫我去講你愛吃煎的嗎?為什麼賴我說錯話?
現在回想生活上的改變之大一定給母親帶來很大的衝擊。記得在北京有個孫媽帶我和大妹妹,帶二妹妹的奶媽是半瞎眼的張媽,原來是母親自己小時候的奶媽,家裡還有一位廚子老李,我記憶中吃飯常有烙餅、餃子、包子、饅頭、麵條之類,都是我愛吃的。北京家中還有外婆和小姨,外婆待我最好,小姨是母親最小的妹妹,比我大六歲,常跟我打架。
2.醬油與鹽水
我們剛回台灣,不習慣祖母的鄉下烹調,特別是青菜在滾水鍋裡燙熟,稱之為「撒」,然後沾醬油吃。常聽祖母跟別人說,她認為「撒蕹菜」(空心菜)沾醬油膏是最好
吃的一道菜。醬油膏是鄉下特有沾菜或肉吃的醬油,濃厚有味又不太鹹。大概醬油膏比一般醬油貴,鄉下人認為是美味而奢侈的沾料,捨不得天天使用,好像逢年過節吃白斬雞、白切肉才用,我猜這也是祖母偏愛的原因。
母親在南投初中教書,我的五姨隨我們來台,也在初中教書。後來,沒過多久,「二
二八事變」,父親被抓走了,母親回到北京托人營救,由祖母帶著我們四個小孩在家,有天晚上,小姑和姑丈來了,跟祖母坐在餐桌上,在昏暗的電燈泡下聊天。我聽到祖母笑著說:「醬油吃完了,今天晚飯我們只好泡了一碟鹽水來沾蕹菜吃,真是太可笑了。」小姑聽了,不但不笑,居然哭了,掏出手帕擦眼淚。我在旁邊覺得奇怪,鹽水跟醬油不都是鹹味而已嗎?不懂有什麼差別,不懂小姑為什麼哭?臨走姑丈掏出一疊鈔票塞到祖母手中。
那天我領悟到,原來醬油比鹽水珍貴。在南投的日子,父親常不在家,長大後才聽母親說,「二二八事變」,父親被抓過兩次,頭一次關了兩個月,第二次送到台中去關了半年。母親趕回北京去找她曾祖父(我的外高曾祖父)門生的兒子壽舅公幫忙,他做過駐墨西哥公使,聽說是當時台灣省長陳儀的同學。母親帶回壽舅公的名片和一封信,回到台北長官公署求見,當天長官一封電報打到台中就放爸爸回家了。(註一)
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員張俊宏來夏威夷東西中心開會,我記得他是南投第二國民學校的高班同學,小時候看過他們兄弟倆,他父親張慶沛又是我們校長,也是爸爸從小好友。我問張俊宏記不記得我,他說當然記得。他說,「你爸爸被抓去之後,還被士兵用草繩綁著遊街示眾,士兵握著上了刺刀的長槍在後面指著。一個鄉下紳士,這麼好的人,被他們百般侮辱,我們看到,心中都非常氣憤。」
張俊宏的話讓我很震驚,心想後來爸爸被抓去關在火燒島(綠島)十年,還不知受過什麼樣的折磨呢?爸爸從來沒跟我提過。
小時在南投的早飯桌上,經常有好幾碟醬菜,後來才知道都是祖母自己醃製的。祖母最喜歡吃她自己醃的醬木瓜和醃竹筍。生木瓜醃久之後,味道奇酸無比,我們小孩都不敢碰,幸好另外還有油炸鬼(油條)、花生米、肉鬆之類配稀飯吃,甚為美味。祖母說,醬木瓜配飯, 只要用筷子點一點,就可以吃一大碗飯。各種瓜果季節一到,祖母就忙著洗曬、醃漬。她在廚房地上排列陶罐,找來一堆大石塊,往每個醬菜醰子裡塞石頭。我不瞭解為什麼要塞大石頭,只是靜靜地觀看。廚房的兩口大灶對我是個好玩的東西,祖母升火煮飯的樣子,清晰如畫。記得她先往灶門大洞裡塞稻草,加上木柴,點火之後,她坐在灶前小板凳上,用一根粗竹筒不斷向火灶裡吹氣。我也要求讓我幫忙用竹筒吹,氣沒吹出多少,已經被煙薰得眼淚直流。逗笑了祖母,做為跟別人談天、誇獎大孫子的材料。
3. 青蛙與蝗蟲
祖母在灶上的大鐵鍋炒菜,有兩次炒了令我難忘的東西。一次看到大鐵鍋裡翻動著炒得焦黑 而形狀奇怪的菜,仔細一看才知道是一鍋青蛙(那時候我用北京話叫蛤蟆)。那天我肯定沒敢吃那盤祖母認為鮮美的炒青蛙。雖然後來初中暑假陪祖母到田間去釣過幾次青蛙,也幫過剖膛清洗,但是每次吃炒青蛙和燉田雞,心中總是不自在。祖母有時講二次大戰末期的艱苦生活,稀少的糧食配給,沒有肉吃,加上三叔生了肺病,只有靠祖母每天傍晚出去田間釣青蛙和田雞,燉草藥給三叔吃。祖母說,要不是她的田雞,三叔恐怕早已不在了。
還有一次在灶邊看到祖母炸蝗蟲(我叫蚱蜢)。有天我家對面和四周稻田裡 出現很 多蝗蟲,四鄰小孩都出動去抓,我也跟著去。每捉一隻就用田邊一種小草穿過蝗蟲背脊,收集成串。有的大小孩很會捉,手提著幾十串捉到的蝗蟲。祖母跟小孩們買了蝗蟲,她在灶上放了一大鍋油,上面飄浮一片炸成焦黃色的蝗蟲。祖母說真好吃,但我不肯試。大妹妹比我小兩歲,不知是傻,還是嘴饞,居然吃了好幾隻,還跟著祖母讚道:「真好呷!」
小學二年級寒假,我們搬到台北,跟祖母住在鄉下的時候不長,我記得的祖母總是跟吃分不開,有讓我害怕的、難以下嚥的,也有許多甜美糕點,除了年糕和龍眼乾糯米飯之外,每次祖母炊製特別糕點都跟某月某日某位神明的生日有關,用來拜神 。
記得有甜粿(年糕)、發粿、糕仔(模子壓出的乾糕)、麻糬等等,還有夏天加冰塊吃的米苔目和鹼粽。我最想吃的是包了甜豆沙的紅龜粿。做這種糯米甜餅,祖母一定要回半里路外的「舊厝」,用掛在廚房樑上的大石磨,把糯米磨成米粉。我跟著幫忙提東西,祖母推磨由我加水和糯米,一道一道的手續非常繁複,從磨粉、揉麵、做餡、用木模子倒出烏龜花紋、樹葉包紮,放在大蒸籠裡蒸。蒸出紅龜粿,總是讓我先嚐。
4.長孫、雞腿、流氓
後來我慢慢領悟,我在祖母心中佔有特殊地位。祖母殺雞拜神,或款待客人,雞腿一定指定給我一隻。她還向大家宣佈,雞腿是長孫的,不准別人吃。父親是長子,雖然四叔和五叔(小奶奶的兒子)都比父親早結婚,他們的兒女都比我年歲大,但是祖母說他們不算,只有長孫將來是替她捧斗的(死後出殯,在行列之前捧著香斗)。祖母做了什麼好吃的,總是晚上把我特別叫到一邊去吃。祖母認為我瘦弱,有一次燉了白鰻魚給我補身體,但第一次吃祖母的燉白鰻卻是頗為痛苦的經驗。我聞到碗中一股奇怪的味道,加上看見碗中一段段像是我被驚嚇過的花蛇,就不敢吃。祖母再三慫恿,我勉強喝了一口湯,味道難聞,我完全拒絕吃像蛇一般的白鰻。
原來祖母凡是做特別滋補的食品,都加放各種草藥。有次三叔從台北回來,他還在台大醫學院讀書。晚上祖母端出一大碗燉雞湯,放在餐桌上,只有三叔和我兩人,在昏暗的燈光下吃。過了一會,三叔莫明其妙地罵起我來了。三叔是親戚中唯一會講國語的,跟我們小孩講話都說國語,不像別的親友來我們家只說台灣話和日本話。記得三叔面有怒容地說我:「你怎麼這樣苦?這個甜的雞肉,你為什麼會苦?苦就不吃好了。」我當時不懂他的話,多年之後回想,我才猜出三叔的意思。因為祖母的雞湯加了當歸、九層塔之類的藥材,可能還加了米酒,我喝湯時大概做出難以下嚥的表情,惹得三叔看不慣,他把台灣話指食物鮮美的「甜」,直接翻譯為國語的「甜」,罵我吃最鮮美的燉雞做出痛苦表情——「苦」。當時祖母的雞湯確實像中藥一樣苦。
我跟著祖母,吃她特別燉煮的東西,也是學會不少台語的機會,但是一知半解,有許多混淆的領悟,要等到多年之後才弄清楚。祖母說河溝裡的鰻魚有兩種,白鰻的補身力量大過鱸鰻,但是我聽成「白麻」與「流氓」。早飯沾白煮青菜的醬油裡滴了幾滴「麻油」,祖母自製(在大腿上用荸麻皮搓成)的麻繩,也叫「麻」,我想這些都有關係,也許鰻魚的樣子 像一根草繩,所以叫白「麻」,我並不懂「鰻」發音跟「麻」一樣。黑色的鱸鰻名稱更讓我胡塗了,我聽成「流氓」。祖母有時提起街上有凶惡的人物叫流氓,小弟有時不乖,祖母也罵他流氓,我不知道跟鱸鰻發音一樣。三十多年之後,母親來美國小住,我問當時爸爸為什麼被抓。母親說頭次罪名是「流氓」,有人告他娶了兩個太太,一定是流氓。
從北京回到南投,我家生活上必定起了很大的改變,我當時只覺得一切新奇有趣,現在想想,我們這家在南投的親友四鄰眼中必然很奇特,是大家聊天的有趣話題。
有天,母親決定請親戚們吃頓水餃,母親忙了一整天。晚上小姑、姑丈、大姑、表哥、表姐、表弟、一大群人來到,興奮吵鬧地等著吃「北京水餃」。吃完水餃之後,大家繼續圍著飯桌聊天。過了一陣子,小姑丈問奶奶:「我們現在吃過水餃了,什麼時候才吃飯呢?」母親回答,我們吃水餃就是一頓飯,引起大家大笑,恍然大悟,原來吃北京水餃就是吃飯。我們奇怪的吃飯習慣,一直是祖母跟外人講笑話的材料。
5.祖母的動物園
走進南投新家的水泥柱子大門,經過小花園過道,就進入玻璃玄關,玄關左邊是一間西式的水泥地客廳,四周有開闊的大玻璃窗,客人不必脫鞋就可進入客廳,可以看到外面的花草樹木。面對玄關的右手邊則有一道木牆,側門通到屋內前院,廣大的泥地,院子就是祖母的動物園。
祖母養了一群雞、一群番鴨、幾隻鵝,後來還有火雞。雞籠、鴨舍、鵝舍各據前院一方。祖母一清早放雞鴨出籠,餵食之後,就放牠們到後面雜草叢生的大院,傍晚再把牠們叫回雞籠和鴨舍。祖母每天用米殼、米糠、剩飯之類攪拌餵雞鴨,有時我看她帶著大斗笠、穿著破衣服,提著一根長桿勺子和水桶,到後門外的田裡去撈浮萍水草給鴨子吃,鴨子最愛吃她撿回來的大蝸牛,也搶著吃用柴刀砍碎的蝸牛肉。
祖母養火雞最花功夫,新孵出的小火雞裝在木箱裡,用紗布罩著,以免被蚊蟲咬傷。
冬天把木箱放在廚房取暖,晚上還在箱裡點了一隻電燈泡,以免小火雞受凍。有的親戚看到祖母對火雞的照顧,笑她比對待嬰兒還要寶貝。祖母養大的火雞有十幾隻。有一天火雞從後門出去,傍晚雞群回家,火雞少了一隻。祖母在門外四鄰找了一遍,沒有找到。第二天祖母沿著大馬路挨家去查問,出去一整天,快天黑了,抱著那隻母雞回來。祖母一臉笑容講她找雞的經過。她說路上有人說好像看到火雞往南走,她不死心一路問一路找到牛運堀,離我家至少一兩里路外,看到她的火雞在別人的雞群中。祖母說她認得她養的每隻火雞,她指出火雞特點,那家人只好承認那隻是昨天自己跑來的,我很欽佩祖母的本領,認識每隻火雞的細微特徵,覺得很不可思議。
祖母養雞鴨有很多讓我驚奇的招術。她有次把幾個鴨蛋偷混在正在孵雞蛋的母雞窩裡,由母雞代孵。祖母很嚴肅地解釋,雞和鴨的天性不一樣,給母雞孵鴨蛋的時候,一定要放幾個雞蛋,以免小鴨孵出來之後不跟母雞,如果孵出的都是不認母親的鴨子,母雞會傷心到眼瞎。祖母還唸了一段順口溜:「天無邊,海無底,鴨仔出世無娘哩。」證明她說的話有根據。
逢年、過節或有客人來,有什麼神明生日,祖母就殺雞、宰鴨給大家吃,有時煎菜脯(蘿蔔乾)蛋,但是我記得祖母的火雞肉最為鮮美,而且肉又大塊。我們搬到台北以後 ,就沒再嚐過火雞的美味了。
6.北投埔
祖母閒談時偶爾會提到「爸臘撥」這個地方,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她的娘家。春節過後,有一天是媳婦回娘家的日子,大姑和小姑都會形式上來我們家走一趟。祖母宰雞殺鴨,招待回娘家的姑姑,那天她也提起想回自己娘家探訪。我上大學以後,查南投縣誌,才知道祖母娘家原來是離草屯不遠的「北投埔」。七歲那年,祖母帶我去了一趟北投埔的舅公家,在一片水田中有幢竹林環繞的土房子,門口對著一個大魚池。那天舅公家幾個年紀比我大的小孩,跳在混濁的池水裡表演游水給我看。我站在水邊,有個小孩潛入水中,突然從水中冒出來,臉上和肚子都塗抹了池底的爛黑泥巴,裝水鬼嚇我。
那天,最有趣的是帶我去看屋樑竹洞內的小鳥。他們搬了梯子架在屋側牆邊,一個小孩爬到頂上,從屋簷竹洞裡掏出一個小草窩,窩裡有幾隻蠕動著的小鳥。舅公聽到我們歡笑的吵聲,出來查看,罵那個小孩真夭壽,叫他趕快把鳥窩放回洞裡去。
舅公是自己下田種地的農夫,他的大兒子後來考上淡江英專,畢業後在台北洋行做事,不久自己做進出口生意成了百萬富翁。我考進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後,回南投去看祖母,祖母問我讀什麼「科」,我怕講不清楚,就告訴她,我在台灣大學讀「文科」。祖母問我:「你為什麼不去讀英專呢?你舅公的阿祥讀了英專,現在賺錢都數不過來。你舅公上次來還說阿祥『有孝』,常常給他錢,舅公再三叫他不要再給,他沒處花錢,前次給的都沒花哩。你看,讀英專多好!」
7.從拜神到信上帝
祖母沒受過教育,不識字,初中有次暑假回南投,問她會不會寫她自己的名字,我逗她寫,她用筆慢慢劃出「林氏傑」三個字,我才知道祖母姓林名傑,是個男性化的名字。祖母性格爽朗,但是脾氣火爆,正直敢言,大人小孩都很怕他。舊厝隔壁堂叔有次跟我說,四鄰大家都不敢得罪祖母。祖母小時綁過腳,後來又放了,雙腳肥短畸形,因為不易平衡身體,走路咚咚有聲,好像很吃力。祖母常笑我瘦弱無力,她自誇年輕時挑上百斤擔子都不吃力,當時她六十多歲的年紀,仍號稱挑得動五十斤米。
祖母的嗜好不少,抽煙、喝酒還有嚼檳榔。我剛回南投時很怕她,因為看到她口吐鮮血,後來才知道那是嚼檳榔的結果,飯廳外面院子地上常有祖母吐的一灘灘像血跡的檳榔汁。長年嚼食檳榔,祖母滿嘴的牙全都被石灰染得烏黑。
祖母雖不識字,但是記憶奇佳,中國歷史典故、三國演義之類,背誦如流。她又愛看歌仔戲,教訓大家的時候,經常引經據典。我上初中時,最小的弟弟跟著祖母住在南投舊厝。每次我回去,祖母都叫我考考弟弟的功課。祖母說,她每晚督促弟弟念書,但是弟弟大聲朗誦(國語),她也聽不懂,不知道弟弟真用功還是朗誦故事書騙她。
祖母篤信鬼神 ,無論媽祖、觀音、城隍等眾神的生日,她都不會記錯,特別煮了大
肉、雞鴨去拜祭。我第一次進城隍廟就是陪祖母去拜祭。本來看到廟裡的佛爺和小鬼樣子恐怖,但是看到祖母虔誠跪拜,口中唸唸有詞,求神明保佑我們全家平安,也就安心多了。要不是祖母不忘鬼神,我恐怕吃不到她逢年過節特製的糕餅點心。
三叔從台大醫學院畢業之後,回到舊厝開業行醫,因為篤信耶穌,不准祖母拜神。我在一九六六年出國之前,回去看祖母,她居然拿出羅馬字拼音的台語聖經讀給我聽。她說,沒想到一輩子沒上過學,不識字,到了八十歲卻學會讀「英文」了,最後,笑著告訴我,信耶穌全家才能得到保佑。小弟燕鳴告訴我,祖母拜神和信耶穌,背後有一套不簡單的思想。有次小弟聽到三叔和祖母之間的對話,對祖母的愛護子孫,甚為感動。祖母從小在農家,每逢初一和十五,必定吃素,一生遵行不斷。有天三叔責問祖母,為什麼信了耶穌還繼續吃素(三叔認為這是違背基督教的迷信行為)。祖母回答:「我信耶穌是為你信的,吃素是為了孫子吃的。」(想必是積功德保護子孫之意)三叔讀醫學院時,有次得霍亂發高燒,情況危急,祖母許願如果三叔病好,一定放棄拜神而改信(三叔的)耶穌。
我到了美國兩年後,三叔來信,祖母過世。年三十晚上,祖母跟兒孫吃過年夜飯,累了先去睡覺,一睡就沒再醒,那天她過了八十四歲。三叔提到我從美國寄給她的那套電動圍肚,祖母過冬,天天都在使用,說那比穿幾層毛衣都更保暖,逢人誇耀是長孫從美國寄來孝敬她的。
我接到三叔的信,很難過,不知該怎樣紀念祖母,最後決定帶孝一週。我剪了一塊黑布,做成臂環,帶在手臂上。到了校園,認識的人都問我怎麼回事。沒想到有位美國同學遠遠地迎面笑臉而來,衝著我說:「真沒想到,你終於也表示意見,反對美國打越戰了!」
註:小時候母親提到,外公、外婆祖上都當大官,母親不清楚他們當什麼官,只知道外公的祖父張亨嘉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我在第七章(註一)說明,考證外高曾祖的經歷。其實母親到北京求救的壽舅公,壽洙潾,是外高曾祖的門生,浙江紹興人,清末進士翰林。他收外婆為乾女兒,母親稱他為舅公。壽舅公第二子壽羲民,做過駐墨西哥公使或領事,南開大學畢業,娶了同學,是馬寅初的大女兒。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去過母親稱為二舅的壽家。他拿蘋果給我吃,先用酒精擦過消毒,聽說在美國久住,特別講究衛生。
一九九九年底,我在香港訪問過遠親吳長生,當時他是香港人民日報社的主任。他對外婆賈
家瞭若指掌,我根據重建外婆家五代親屬和婚配。附在後面的圖表是外公張家和外婆賈家的
家譜, 顯示從前官宦之家,親上加親的婚俗。外公兩代單傳,十三歲由福建老家到了北京,
後來娶了十幾歲的買家獨生女,就是外婆。賈家來自山西,住在門樓胡同的庭院大宅(在菜市口西接近廣安門),我記得三、四歲的時候去過,兩層樓的雕樑畫棟,尚有印象。據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遷出住戶辦了工廠,文革之後,在宅地蓋了四棟大樓。外公、外婆幼失 怙恃,不務生計,成群家僕慫恿揮霍,又嗜好鴉片,偌大家產、古董字畫,變賣一空。我五 歲時外婆因肺癌過逝,年方四十八歲。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的圖書 |
 |
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 作者:吳燕和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5-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197 |
中文書 |
$ 198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
人類學家為什麼到落後地區居住?問東問西又記在本子上,不禁令人懷疑是外國間諜,是稅務局的調查員,是警局密探,還是假藉研究之名來尋找寶藏的……
本書以流暢生動的文字描繪出一個趣味盎然的故事。
吳燕和的人類學家三部曲,由童年故鄉的記憶開展,歷經中國古老的古都文化、日本殖民殘存文化、台灣蛻變中的鄉鎮文化……,這些族群融合的過程多元又多變,養成他冷演觀察和探索外在世界的樂趣。因緣際會踏入人類學領域,與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凌純聲及李亦園教授等人,一起從事台灣原住民的田野調查,考進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後,體會這門學科的奧妙,與王維蘭女士夫唱婦隨悠遊學海、遨翔萬里,足跡跨越美洲、亞洲、大洋洲等地從事田野調查,一起在地生活觀察、記錄不同的文化模式以及社會變遷。
人類的文化發展像是火車之旅,有令人驚奇的變異也有其必然的軌跡。吳燕和這趟人類學之旅,也在研究他人的過程中,學習如何認識了解自己。
作者簡介:
吳燕和
台灣南投人,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碩士,澳洲國立大學人類學博士。一九六六年赴美,七○年代中任職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研究員,兼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一九九三年赴香港擔任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
赴美前,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技佐、助理員,其後並擔任兼任研究員及學術諮議委員。
從事田野工作四十餘年,早期活躍於台灣原住民地區,偕同妻子王維蘭女士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東南亞、中國雲南及東北少數民族地區做多次田野調查。
發表的專書有十餘種、論文近百篇,著作多在歐美出版。
二○○○年偕王維蘭女士返夏威夷就醫,現專心從事寫作。
章節試閱
前言人生就像是火車之旅,一站過了一站,似乎坐著不動,但景色轉眼全非。我用火車形容我的人生旅途,是我對火車的偏愛。從小時候冒著黑煙、轟隆轟隆、震耳欲聾的火車,到今天飛馳如燕的超子彈列車,反映人生的經歷、時代的嬗變、世紀的更新。火車上看到形形色色的乘客,有的坐一站就下車,有的陪伴你整天整夜,變成多年老友般,向你訴說他的家人、他的事業、他的憂愁、他的欣喜。無論家人、親友、學生、同事、陌生人,不都像同車的乘客一般嗎?長聚短聚、不斷追求著什麼、尋找著什麼?少年時代,人類學改變了我的命運,人類學讓人類學家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吳燕和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5-08 ISBN/ISSN:9571344702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