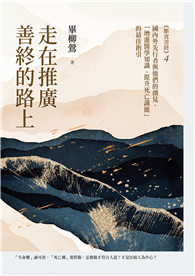張超英書序文
劉黎兒
我是在1982年到日本的,2004年離開新聞界,目前依然住在日本,張超英二度派駐日本大顯神通時我都是見證人,許多的功績甚至張超英這個人本身,都是在我離開新聞界之後,更能客觀地來下自己的定論,以及確認自己所受的影響。
我到日本不久,接任工商時報特派員(後來才出任中國時報特派員),張超英便馬上要我加入日本記者俱樂部,他認為不僅是外交官,台灣特派員加入關鍵性的組織,也是增加台灣發言權的作法,但要成為會員需要二家日本報社推薦,張超英為我安排了他關係深厚的「河北新報」以及「長崎新聞」(前身為「長崎日日新聞」)當我的推薦人,讓我順利入會,協助台灣的特派員大量加入日本記者俱樂部也是張超英的功績之一,不過跟其他的功績比較起來,連提都不值一提吧!但最初沒邦交而能打下這塊地盤,也是靠他了解日本人,又擁有日本人較為脆弱的新聞自由、民主自由的理論武裝,才能理直氣壯去爭取到的吧!
當時我對日本圓的扁的都還搞不清楚,不僅跟日本全國性大報關係稀薄,對地方報更是無知,只對「河北新報」的「河北」覺得有趣,當時還未開放到大陸探親、觀光,地理課本上讀的「河北」居然在日本邂逅到,奇妙無比,要等日後我在櫪??木縣的那須有個家,常去附近的白河等小鎮玩,才知道原來「河北」是指白河以北的日本東北(陸奧)地方;因為當初加入不易,即使離開新聞界,但還為報紙、雜誌撰寫時事評論,至今我都還維持日本記者俱樂部會員身分。
張超英第一次到任後,便很積極展開對產經新聞以外報社的交流,尤其是推動朝日、讀賣新聞等的關係,日本新聞界是比肩看,尤其是二大報報導的話,其他報也都會積極跟進,但如此作法引來有人批判張超英「大小眼」,其實這與日本媒體習性有關,亦即擒賊擒王,「大小眼」是一種權宜措施,而且要「大小眼」很不容易,因為大的地方很難攻破,日本媒體人事都有輪調制度,張超英到任當初,除了產經之外,其他媒體的名單都是失效的陳年名單,早已換了不知道多少輪,一切從零開始去衝刺。在美國工作一、二十年的張超英也注意到,歐美媒體派駐東京的單位總控整個亞洲的報導,因此跟派駐東京的歐美特派員打好交道,也等於控有全世界媒體,東京新聞組的作用因此可以發揮到極致。
在廿幾年前,我剛到日本時,日本關於台灣的報導只有女人來賣春與走私毒品等,形象很差,認識很有限、荒謬,甚至有日本人還認為台灣人是生活在熱帶雨林裡吃香蕉等;張超英告訴我,他的原則是只要日本記者願意去台灣,他不會以任何條件來束縛的,果然開始在一些雜誌、綜藝節目等也都開始出現台灣的相關鏡頭,從軟性到硬性消息,「台灣」兩個字開始在日本媒體上登場。
許多大報記者都跟我說:「因為去過台灣,我們是用我們的肌膚來感受台灣的民主,實感到與中國的不同!我們跟報社內部已經成為化石的老左派不一樣。」因為平時不斷積極與日本媒體建立關係,在關鍵時便見真章,如92年廣島亞運時徐立德代替李登輝出席,按理「徐立德」三個字的日文發音很聱牙,但日本電視主播都不得不學會唸這三個字,其後95年辜振甫出席大阪APEC等,台灣出席問題均成為日本報導焦點,每天見諸頭版頭條,因為新聞操作成功,因此代理出席比李登輝本人出席效果要好千萬倍,最後集大成是96年張超英促使廿幾位日本記者跟李登輝訪美,這樣的成果在當時根本是破天荒、難以想像的。
單單這三大次新聞操作,換算成廣告價值至少是上兆日圓計算吧!在張超英時代,日本媒體有關台灣的報導與日俱增,新聞局駐日的新聞組也開始能每年彙整出一本厚厚的統計與重要剪報,張超英並沒有強調這點,或許也是無意將功績全部算在自己身上;張超英之後,這些年新聞局科班出身而接班非常出色的朱文清,也是曾在張超英身邊見識過張超英手法的,朱文清後來在2000年李登輝訪日時操盤也很成功,連續二、三個月日本媒體不分左右都以人道觀點來報導,而且不論大小報均推出3篇以上的社論,也是更加奠定張超英為台灣報導打下的基礎,換算廣告價值也同樣是無價的。
張超英發現在日本要宣傳台灣,打李登輝牌是比較容易做的,不僅李登輝訪美,還有積極拉線促成的「台灣的主張」日文版賣了20萬本以上,擴張了李登輝在日本的影響力,也是讓李登輝被北京視為首位罪魁的原因。
張超英的手法也讓我學習模仿過一次,亦即2001年11月我得知剛卸下巨人職棒監督職務的長島茂雄有意到台灣觀看世界盃的日本隊的比賽,正好自己跟讀賣集團有關係,便安排當時駐日代表羅福全跟讀賣人士一起去拜會長島茂雄,並邀請他訪台,長島快諾,因為長島到台灣,日本電視(NTV)便轉播了日本隊在台灣的比賽,而且共有百位記者同行,大概是台灣連續出現在日本電視鏡頭上最久的記錄,我暗自竊喜。
不過正如我自己牽線的這次經驗一樣,做得是日文所謂的「?方」的幕後黑子的工作,如果今天沒寫出來,誰也不知道,張超英做過千萬件比我規模、影響力更大的幕後工作,但若非他這次自己用回憶錄形式道出,或許天下人很快就會忘懷,而且加上他曾經不斷幫他覺得有知遇之恩的宋楚瑜,更惹上額外的政治恩怨,讓他更沒機會得到應得的正面評價;也讓我覺得我這樣的文字工作者其實是占盡便宜,寫什麼都讓天下人知道,不像張超英這樣應該在日台交流史扮演重要地位的人,至今華人世界對他並不大清楚。
日本外務省主管中國政策的官員曾經對我說:「妳對張超英那麼肯定,可是在我們看來他未免太『強引』了,不像在做外交!」「強引」就是強硬、蠻幹的意思,我內心想:「以當前日台現狀,不稍微強硬些,台灣就什麼國際地位都爭取不到的!日本也不會主動給台灣的!」而且我也知道,張超英是超出外交框架在做事,但絕不是蠻幹,他深知日本人講求人脈關係,他在日本曾經住過文化學院創辦人西村伊作家裡、又跟曾任文部大臣及朝日新聞客座主筆的永井道雄是世交等,關係赫然,加上本身涵養、談吐都有魅力,在日本自然很吃得開。我也因為他的關係認識了某些日本媒體人士,如朝日新聞著名的天聲人語作者的白井健策等,後來也代張超英去出席白井感人的喪禮!
書中提到的讀賣新聞記者戶張東夫,當年也曾經對我說過:「日台關係中應該特別列出張超英時代的一個章節,有張超英跟沒有張超英,日台關係其實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當時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使其後有些現實政治干擾,我的看法現在也沒有改變,張超英這樣的人可以在沒有舞台的地方創造出舞台來,這是他偉大的地方。當然有些或許是時代讓他很容易去打拼,例如「為台灣」、「台灣民主化」的價值,在1980年起的20年是比較容易認同的,也會讓在海外的人有衝勁,不顧一切地奮身前衝,但2000年之後就是認同等都逐漸比較困難的時代,要有如張超英的神力不可能的同時,要單純地衝刺也不容易。1980年代起到亞洲經濟危機為止,經濟看好的台灣在亞洲的發言權也很大,或許也助長了台灣各種國際宣傳工作的聲勢,亦即那時的台灣說話可以比現在大聲多了,或許也有時代幫了張超英一把的小因素存在吧!
不過最主要的是,我到現在才體認到張超英是一位真正自由的人,沒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對現實利害並不計較,才能跳脫官式框架乃至時代、國境的框架,或許也跟他優裕的成長背景有關係;有許多餘裕的大少爺才能不計較的,或許這正是我這種普通人家出身的人所難及的。
我生平最不喜看自圓其說的回憶錄,但張超英的敘述精確平實,加上陳柔縉深厚的日治時代史學素養,算是我自己第一本可以接受的回憶錄,讓我很羨慕張超英有一個可以如此敘述的精彩人生。真正自由人的他直呼高官權貴名字,我也想仿效,只稱他為張超英,就算當著面這樣叫他,他也不會生氣吧!
序2
世家子弟
阿舍 黑狗兄
李昂
認識張超英先生多年,他如此精彩的家世與生平,讓我都想用筆記錄下他的生平,可惜彼此忙碌,未能如願。
現看到陳柔縉女士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完成此書,張超英先生種種有趣、特殊的事蹟躍然紙上,我一面看一面想:
真比小說還精彩。
很少人有像張超英先生這樣的家世,在此先簡單做個陳述。第一代張聰明先生白手起家,靠礦業成為鉅富,時值日據時代早年。第二代張月澄先生,研究台灣近代歷史、文化的人,都會知道這位抗日人士,為追求台灣的自立自治被抓被關。
好不容易二戰日本敗戰,張月澄先生像當年企望祖國的台灣精英份子,等到的是二二八殘酷的鎮壓與屠殺,雖未失去生命,家族花了極大的代價將他救出鬼門關,但從此幻滅鬱鬱以終。
第三代便來到了張超英先生,他就是本書的主人翁。當然是含著金湯匙長大,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看著他娓娓道來如何十三歲與台灣當時首富吃飯,富貴如這位台灣商界鉅子,吃的也不過是一碗切仔麵,而且隔天中午即因病驟逝。
這給了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張超英先生很大的啟示:
「我開始隱約感覺擁有很多錢的虛無,覺得知道怎樣賺錢並不重要,知道怎樣花錢才是人生更重要的事。」
這幾句話無疑道出了一位「阿舍」的真正心聲。張超英出生時家族已富到第三代,生在日本、在香港求學、到過上海,在東京受完大學教育。小時候便見過最繁華的大都市裡的大排場,以及,都市邊緣人饑餓、凍死路邊的慘狀。這些,都像「大觀園」裡的「賈寶玉」,很容易參透人生的無常吧!
童小到青少年的回憶,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本書部分。我們看到一位富過三代的「阿舍」,而且是位十分善良、有點柔弱易感的年輕人,更重要的是,長得文秀而好看。我常和張先生開玩笑,如果他生在今日,不知會引來多少女性的主動追求呢!
這位既是「阿舍」又是「黑狗兒」的世家子弟的生活,兩代獨子當然倍受寵愛,尤其母親早逝,沒被寵壞多半來自他本性純真善良吧!我們看他坐上卡車踩油門就往前開;有第一部台灣的速克達,在二戰物資匱乏時,從上海帶來值四、五佰塊美金呢!
當然也讀到他怎樣在上海喝到第一口可樂,感嘆「怎麼有這樣好喝的東西」,而後,一輩子最愛的飲料便是可樂。
我認識張超英先生時,看到他年紀不小但還像孩子一樣的嗜喝可樂,真覺得這位可愛的「黑狗兒」,一輩子真的是個「阿舍」。
「阿舍」形容的是張超英先生的氣質,他絕非我們刻板印象一事無成的「了尾仔」。隨著二二八之後家道不如以前,張超英先生靠著自己的能力在新聞局工作,拍記錄片獲獎,開工作室,而且最重要的,在時代的洪流中,見證到了幾個重大的歷史片刻:
比如蔣經國在美國遭刺殺未成那次,他在現場,中國進聯合國後台灣成外交孤兒,張超英先生藉著家中累積的日本關係、人脈,讓宋楚瑜能在高爾夫球場「偶遇」日本首相,都充份展現他的能力。
而且,張超英與賢慧能幹、同樣家世良好的太太顏千鶴女士結婚後,生育出色的孩子,有的還在科技界頗有成就,打破「富不過三代」這樣的說法。
從祖父靠礦業成鉅富,父親是日據時代聞人張月澄先生一代,在日本讀書時坐自家黑頭車,請有秘書,學生有此排場,到花了大把的錢抗日。到張超英這一代,年輕時代享盡榮華富貴的生活,這本書記載的,當然不只是張家的家族史,毋寧也是台灣的一頁近代史吧!
但我個人最喜歡的,仍然是這個有點害羞、十分可愛的「阿舍 黑狗兄」。畢竟,像張超英先生這樣的世家子弟,隨著過去的台灣,不會再以這樣的方式重現了。
那麼,讀者不妨從書中,體會一下那個過去的時代台灣人的風華吧!
後記
一九九○年初,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出任駐日代表,針對此事,我任職的政論周刊老闆給我一個電話號碼,「打去找張超英,做一個專訪」,那是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老闆說,他是已卸任的駐日新聞處處長。
這位子說大不大,整個政府同階的何止千百。張超英既卸了任,又不是部會首長,做專訪實在不符常例。那時剛好又和一位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聊起,他告訴我,如果他要寫台日關係史,有一章一定要寫「張超英時代」。張超英這個人三頭六臂嗎?我心裡長了一朵好大的問號。
慢慢,我知道張超英之名確實在新聞界和外交界如雷貫耳。名氣響亮,不是因為他當過甚麼部長、總司令,相反的,他的官位頗小,就只是個處長。對新聞界來說,他有點像電影裡布魯斯威利所飾不受節制的警探,以不按理出牌和神勇無比出名,單槍匹馬,做了跟他的職位不相當的大事來。
一九八○年代,他就能憑個人之力,讓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原本不看台灣一眼的日本主流大報,紛紛被他打開;九○年代,李登輝成為日本家喻戶曉人物,背後的大推手正是張超英。
一九九三年,張超英從紐約回來擔任公視顧問,經老闆引介,我終於見到張超英的廬山真面目。這次,承蒙不棄,他委託我幫他寫口述回憶錄,我因而有更多機會來探究清楚「台灣政府的布魯斯威利」何以神勇的面貌與秘密。
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前後拖延十二、三年,一來是中途張超英回任東京新聞處五年,完全中斷,再者,我們從沒有設定截稿時間,也沒有一張採訪綱目。每年他從紐約回台灣幾個月,我們有空就聊,東南西北,毫無次序。
我從三十歲寫到年過四十,斷斷續續,聽他講故事,永遠充滿驚奇與趣味,如看花火。直到今年最後收網階段,好像終於可以靜靜回顧他的人生,我開始常常邊寫邊流淚。有時,一個人在咖啡店敲著電腦,那裡的喧鬧絲毫無法稀釋我的情緒。
以我對張超英個性的瞭解,他八成難解我的心情;他自尊自重,知道自己無愧於工作,無愧於台灣,很欣慰自己所達到的成就,有甚麼好落淚的。十幾年來,無數輕鬆或嚴肅的談話裡,我從來沒聽過他一聲怨,怨權力者沒回報他更高的位子。我採訪過不少大小官員,十個有九個自認懷才不遇,攻訐與輕蔑同僚就像吃三餐一樣頻繁。轉頭過來看張超英,他老像個政治競技場的新生,沒浸染半點官僚味,頗有權力名位於我何有哉的天真。他會抱怨、生氣、惋惜的都是事情沒做好,台灣沒辦法更有尊嚴、更進步、更民主。十幾年來,我有更長時間檢視張先生的人格和成就,因而更容易流淚;他那麼淡然,那麼快意,反讓我幫他懷著委屈。
有一次和出版界前輩聊起張先生,對方在長長的談話裡,輕輕說了一句「像他這種小人物」,突然,我有種很深很深被刺傷的痛感。在那以前,那樣的形容,我可能不以為忤、不覺有異,張超英不過就是個處長而已,連常務次長都不是,更不是特任官,形容為小人物,何不當之有!?但當時,我確實非常難過,也很慚愧。
幾十年來,我們的眼裡只有位子高的大的政治人物,我們受惑於位子,誤以為位子高的,才是功勞大的,他們說的話才值一聽,歷史是他們創造的,他們的身影才值得留在歷史。那一刻,我恍悟自己錯亂了甚麼是大、甚麼是小。
雖然,我無意把張先生捧成大人物,但他絕非小人物;他那種要盡一己之力,不媚當道,讓台灣更好的純粹念頭和不謀權位的純情行動,特別在此台灣政壇權慾薰心、道德毀棄的時代,民心一片沉悶與低迷中,更值得大家體味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