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漫長的告別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0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漫長的告別 作者:瑞蒙.錢德勒 / 譯者:宋碧雲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7-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故事從加州的一處酒店開場,私家偵探馬羅遇到了爛醉如泥的藍諾士—一個穿著得體、蒼白有禮但臉上有疤的男子,接下來他們將開始一段短暫卻要命的友誼,這段已經被視為偵探小說史上經典的動人友情將會為馬羅帶來難以探測的危機,他將會捲入一段不名譽的婚姻、一場牢獄之災、牽扯出一場讓馬羅動心的感情,以及一位懷才不遇的作家。
本書特色
首次登台:《漫長的告別》中文繁體正式授權版。超值獨家收錄::2007年村上春樹為自己新譯的日版《漫長的告別》所寫譯後記<準經典小說《漫長的告別》>。
這部作品1953年出版,問世至今45年,1973年勞伯.阿特曼曾擔任導演將其搬上大銀幕。
舊金山有家推理專門書店,老版是推理迷,他書店中央擺了張桌子,專門陳列最近的暢銷書或好書,不過有一疊書從來沒有下架過,那就是《漫長的告別》,那疊書的下面夾著一張手寫紙,上面寫著”Best book in the store.”
明年是錢德勒逝世50周年,為了向大師再致敬,時報選擇《漫長的告別》做為重新推出錢德勒譯本的第一砲,一來是因為錢德勒書迷也是時報重量級作家村上春樹在去年推出了新譯本,二來《漫長的告別》是錢德勒最具野心也是最受文學界重視的一本作品,當然無論是哪一本錢德勒都值得編輯們的努力,因為光是因為他給了我們馬羅,就足以讓我們永遠記得他。
獲獎記錄
瑞蒙 錢德勒獲MWA(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票選為「150年來最出色推理小說家」第一名。
作者簡介
瑞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
1888年出生於芝加哥,但因父母離異,隨母遷居倫敦,錢德勒的童年都在英國度過,大學念的是杜爾威奇(Dulwich)學院,成年之後返回美國加州定居。
錢德勒開筆甚晚,45歲才正式發表第一篇小說〈勒索者不開槍〉,刊載於當時的廉價雜誌《黑面具》(Black Mask)上,然而,以漢密特為首加上錢德勒等人領軍的這批廉價小說,卻成功的推翻了英國古典推理對美國偵探小說的限制,開啟了美國冷硬派私探小說的傳統,後來這段歷史成了推理史上有名的「美國革命」。
錢德勒逝於1959年,畢生共完成七部長篇和二十部左右的短篇。其中以偵探馬羅為主角的系列更是他寫作的高峰。馬羅就像海明威筆下的硬漢,即便處境艱難也不肯拋開君子風度與誠實價值,每每讓讀者受到震撼。深愛馬羅系列作品的西部片名導比利.懷德就曾說:「錢德勒的小說,每一頁都有閃電。」
錢德勒的電影劇本寫作在美國史上也有相當重要性,他曾與知名導演希區考克、比利.懷德以及羅伯.阿特曼等人合作,福克納也曾受雇將他的小說編成電影腳本。有趣的是以通俗小說起家的錢德勒,多年來其作品慢慢受到文學名家的喜愛,詩人奧登、寫作艾佛林.沃夫、格雷安.葛林、佛來明、錢鍾書、阿城……等人都曾公開推崇他的寫作,而日本最受歡迎的作家村上春樹更表明自己從小至今看《漫長的告別》不下幾十次,去年更自己動手譯出新版本,寫出長達兩萬多字的譯後記,分析這部小說與《大亨小傳》如何在精神面上共通,以及錢德勒作品獨特難學的風格。
譯者簡介
宋碧雲
台大外文系畢業,專職翻譯。
譯有《一百年的孤寂》、《蘇東坡傳》(遠景)、《浮華世界》(桂冠)、《天生嫩骨》(高寶)等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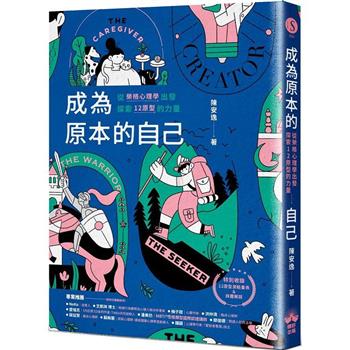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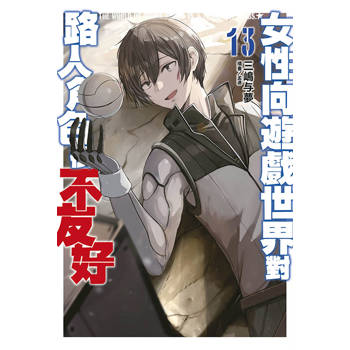





一開始讀這本書時,我覺得好難看,平常都看本格派跟社會派的我,完全無法進入冷硬派的世界,我心想可能是翻譯的關係,導致閱讀比較不易,可是我想要把這本,冷硬派的代表作「漫長的告別」看完,所以我硬著頭皮繼續看下去,當我開始靜下心,慢慢的去閱讀這本書時,我第一次進入了冷硬派的世界,對我來說看推理小說最有趣的,就是能進入作者所創造的推理世界,明明只是坐著,卻可以環遊世界,跟著偵探一起解謎,這是推理小說最迷人之處。 而我覺得瑞蒙.錢德勒,他的寫作功力真的非常厲害,我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推理小說,它得內容很真實,錢德勒把謀殺還給有理由犯罪的人。 書中滿是嘲諷對話,是讓我覺得,很有趣的部分,馬羅與其他角色,有著共同的語言,就像平常我跟朋友之間得對話一樣,讓我看本書時常常會感到會心一笑。不知道是我即將步入45歲這個屬於半百老翁的頑固年紀,還是心胸越來越狹隘,近來讀的一些書籍,明明都是佳評如潮人人稱許\的「經典書籍」,我讀起來卻感到彷彿如嚼臘地枯\燥。 會選擇這本「漫長的告別」,主因是村上春樹為這本書寫了一篇翻譯後序文,同時他也是本書日文版的翻譯者,反正就是村上春樹很推崇這本書與作者雷曼錢德勒就對了,其實,我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明明自己對於這類冷硬派偵探小說毫無咀嚼力,卻又要硬著頭皮嘗試;二是我應該先翻閱\一下村上春樹的推薦文。 如果你是喜歡日式社會心理派推理小說(如宮部美幸、松本清張)亦或是喜歡本格推理派(如柯南)的讀者,通常無法順利的進入英式冷硬派的推理世界,至少我就是這樣。而我也忽略了村上所寫的序,長篇大論式的村上的序,其實只有幾個重點,村上很欣賞雷曼錢德勒用詞遣字與文法結構,這句話的用意有如我推崇某位財經大師的作品「有嚴謹的數理模型或綿密可不斷驗證的推論與結論」,我想本書已經屬於「文學研究所」上的授課內容了。 村上推崇的另一個理由是本書暗喻著1950年代美國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沉悶與腐敗,沉悶年代已經夠沉悶了,本書還用暗喻的方式,除了會「沉悶+沉悶」的三次方之外,不然就是「沉悶無限大」。 對!這本書就是沉悶,或許\是我的閱\讀能力不夠(我是位一年讀不到五百本書,寫不到三百篇書評的沒有水準也沒住大安區的三低一高人士),或許\我正如李家同所言「網路文章看久了會變笨」(那寫網路文章的人豈不笨蛋最高級了),我就是無法很順利地進入本書所營造的硬漢推理氣氛,這本書我一共看了七天,試了各種最適合閱\讀的場所:候機室、慢速火車車廂、大雪紛飛的雪地溫泉旅館的窗台邊書桌、板南線捷運(當轉到文湖線後就不適合看書了)….就是無法讓我專心。 讀這本書時心思總是會不小心飄到書本以外的世界,不知不覺就會去計算「在忠孝東路被狂奔的河馬撞斃」的機率,這本書每句與每段都會讓我搞不太清楚發言者到底是誰,到底是奧姆真理教教主還是對著便當咆哮的洪蘭老師,一不小心就分心去馬總統的臉書網站按「讚」(他馬的臉書只能按讚、不能按「戳」),閱\讀這本書竟然會讓我悶到想要重拾股票看盤的時光(我已經六年沒看盤超過一分鐘)。 當然,這本嚴肅的文學經典作品除了「悶到看不太下去」的小小缺撼以外,就沒有其他缺點了,更別說本書還具有「絕佳的文學開創高度」、「嚴謹的文字架構」、「臻至夢幻的經典境界」、「值得思考的典範」、「擁有寫實自我的文字運鏡魔力」…..等等我寫了都不知道什麼意思的禮讚詞藻,然而大家可別小看這些詞藻,這些可以讓中學生抄在「寒假閱\讀作業」裡取悅中學老師,或用在高中基測與大學學測的作文內來考取高分呢。 看完之後,除了搞不太清楚整本書的劇情架構外,同樣的我依然算不出「在忠孝東路被狂奔的河馬撞斃」的機率,更搞不清奧姆真理教到底有沒有在文湖線上出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