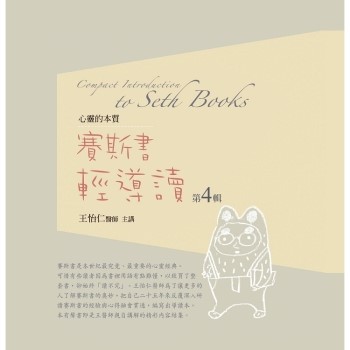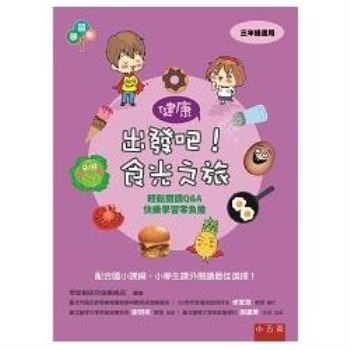十二年前創下美國影史票房記錄的《鐵達尼號》(全美票房六億七千八百萬美金)捧紅了兩大巨星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凱特‧溫絲蕾,但這對傳奇的螢幕情侶至今未再同台演出,直到這部經典小說《真愛旅程》的劇本送上門,兩人決定再度合作,但這一次他們要詮釋的不再是瘋狂勇敢、生死不渝的愛情,而是一對在現實與夢想中掙扎並失落的年輕夫婦,該片由《美國心玫瑰情》導演山姆‧曼德斯執導,預計2009年上映,未演先轟動,已被預言是明年奧斯卡的超級焦點。
這部影片能夠未演先轟動,除了卡斯超強之外,原著也大有來頭。《真愛旅程》原著小說出版於1961年,一出版就驚動文壇,知名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當年就以「這本書好得太超過了!」來表達讚嘆。英國暢銷作家尼克‧宏比也說:「這本書輕而易舉就擄獲了我。」這部傑作也入選了2005年美國《時代》雜誌的百大英語小說,與《大亨小傳》等書並列。故事描寫惠勒夫婦法蘭克及艾波這對年輕夫妻,受不了郊區生活的無聊平庸,渴想與眾不同。他們一方面想要改變自己、改善生活,但終致變成自欺欺人,使彼此的人生都變成一場悲劇。
作者簡介:
理查‧葉慈(Richard Yates)一九二六年出生於美國紐約揚克斯市,二次大戰期間加入美軍,戰後在雷明頓蘭德公司(Remington Rand)擔任文宣撰稿員,六○年代曾短暫為甘迺迪參議員撰寫演講稿。一九五三年,他開始有幾篇得獎故事問世,而他的第一本小說《真愛旅程》,於一九六二年入圍美國國家書卷獎。除此之外,他還有八部作品,包括三本小說:A Good School、The Easter Parade,及Disturbing the Peace;以及兩本短篇故事集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和Liars in Love。理查‧葉慈離過兩次婚,有三個女兒,於一九九二年辭世。
譯者簡介:
鄭淑芬,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主修國貿、英文、翻譯。目前專職翻譯,具備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英譯中證書。譯作有:《1001個自閉兒教養祕訣》(久周)、《樂透人生》(時報)、活出最真的自己(時報)等二十餘本。譯文賜教:ajanejane@gmail.com。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我很喜歡理查‧葉慈的人和作品,《真愛旅程》是本魅力無窮的小說。」
──麥可‧謝朋
「理查‧葉慈的《真愛旅程》是我今年在文學上的大發現……它就跟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一樣層次豐富,跟費滋傑羅的文字一樣傷感。」
──尼克‧宏比
「我每年都要讀一遍《真愛旅程》,除了它細緻的文字架構外,我最欣賞的是他筆下角色自我欺騙的過程。」
──大衛‧塞德里
「我這個時代的《大亨小傳》……是這一代最好的小說之一。」
──馮內果
「就我所知,這是少數幾本毫無缺點的小說之一……理查‧葉慈成就了費滋傑羅在全盛時期成就的事,重現了生命不可承受的沉痛辛辣:生命給人希望,往往又在同一時間推翻了這份希望。」
──詹姆斯‧亞特拉斯(James Atlas)
「《真愛旅程》可說是它那個時代的《包法利夫人》。」
──道格拉斯‧甘迺迪(Douglas Kennedy)
「我到處送《真愛旅程》這本書給人,只要對方願意收……這是美國文學史上,最感人、也最確實描寫郊區生活的小說之一。」
──大衛‧海爾(David Hare),《觀察家報》
「美國文學經常拿酸腐的美國夢大作文章,但很少有作品能超越理查‧葉慈作品中敏銳的情感。他在《真愛旅程》這本書中,以充滿力道的筆觸,描寫五○年代注定要走向失敗的中產階級夫妻感情,使得後來的作品,都顯得有氣無力。」
──《泰晤士報》
「理查‧葉慈是美國戰後最好的小說家及短篇故事作者,寫出了那一代最精彩的小說;讓有幸能發現那些小說的讀者,繼續享受閱讀的樂趣。」
──《獨立報》
「理查‧葉慈是個運筆如神的作家。他的文字洗練而敏感,熱情與諷刺巧妙平衡,用詞充滿新意,隨時展現智慧靈光,精確捕捉人物感情,但又適時抽離,提供辛辣而不濫情的觀察,讓閱讀充滿意外的樂趣。」
──《週六評論》
「一字一句,都反應了作者最極致的正直個性與純熟文筆。閱讀《真愛旅程》,就好像不得不重新面對現代社會最關鍵的缺陷:失敗的工作、教育、社會、家庭、婚姻……連面對的勇氣也失去了。」
──《新共和週刊》
媒體推薦:「我很喜歡理查‧葉慈的人和作品,《真愛旅程》是本魅力無窮的小說。」
──麥可‧謝朋
「理查‧葉慈的《真愛旅程》是我今年在文學上的大發現……它就跟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一樣層次豐富,跟費滋傑羅的文字一樣傷感。」
──尼克‧宏比
「我每年都要讀一遍《真愛旅程》,除了它細緻的文字架構外,我最欣賞的是他筆下角色自我欺騙的過程。」
──大衛‧塞德里
「我這個時代的《大亨小傳》……是這一代最好的小說之一。」
──馮內果
「就我所知,這是少數幾本毫無缺點的小說之一……理查‧葉慈成就了費滋傑羅在全盛時期成就的事...
章節試閱
定裝彩排的最後聲響逐漸淡去,桂冠劇團的演員們什麼事也不能做,只能無助地站在那裡,默默地眨著眼睛,看著空曠觀眾席上的腳燈。他們大氣也不敢出一聲,等著導演那矮小嚴肅的身影,從空蕩蕩的座位上起身,加入在舞台上的演員們。導演從舞台旁邊拉出一個摺梯,發出刺耳的聲音,踩著梯子爬到一半,然後轉身,清了好幾次喉嚨,對他們說,他們是才華洋溢的一群,能夠跟他們合作真是太棒了。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說著,掃視舞台,眼鏡發出冷冽的閃光。「我們遇到很多問題,坦白說,我多少已經說服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可是,聽我說,也許這句話聽起來像陳腔濫調,但今晚舞台上產生了變化。今晚我坐在台下,突然感覺,打從心底感覺,這是各位第一次全心全意投入演出。」他撐開一隻手的手指,放在襯衫口袋上,讓大家知道「心」是多麼單純而具體的東西;接著他又將同一隻手握成拳頭,緩慢晃動,閉上眼睛不發一語,捲起濕潤的下唇,形成一個勝利又驕傲的表情,讓這長長的停頓製造出戲劇效果。「明天再同樣做一次,」他說:「我們就會有一場精彩絕倫的演出。」
他們大可以喜極而泣。但沒有,他們顫抖著,歡呼、大笑,互相握手與親吻。有人搬出一箱啤酒,大夥兒圍著劇場裡的鋼琴唱歌,直到全體一致同意,該收工回家,好好睡一覺了。
「明天見!」他們喊著,高興得像孩子似的。沐浴在月光下開車回家的路上,他們發現可以搖下車窗,讓帶著泥土與鮮花芳香的健康空氣灌入車內。這是很多桂冠劇團的團員,第一次以這種方式迎接春天的到來。
這是一九五五年,而這裡屬於西康乃狄克州。三個發展迅速的小鎮,最近才由一條寬廣、喧嘩的高速公路連接起來,這條路被命名為十二號公路。桂冠劇團是個業餘劇團,但他們捨得花錢,態度認真。團員是從三個鎮上的青年人中慎重挑選出來的,而這是他們的處女作。一整個冬天,大夥兒輪流聚在某個團員的客廳裡,興奮地討論易卜生、蕭伯納、歐尼爾。最後以舉手表決的方式,多數人選擇了《石化森林》這齣戲。接著,又為了準備初步的角色分配,他們感覺自己一週比一週還要投入。私底下,他們或許認為導演是個逗趣的小矮子(從某方面來說,他確實是的:他似乎只會用慷慨激昂的方式說話,說到最後,往往還要搖頭晃腦一番),但他們喜歡他,也尊敬他,並且全心全意相信大部分他說的話。「每一齣戲都值得演員盡全力表現。」這句話他說過一次,還有另一句:「記住,我們不只是要演一齣戲,我們是要創立一個社區劇團,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麻煩的是,打從一開始他們就怕到頭來會讓自己出糗,而害怕承認這件事,又讓這不安更加深刻。剛開始排練都安排在週六--似乎總是那種無風的二月或三月午後,天空是灰白的,樹是鬱黑的,逐漸消融的雪堆之間,露出光禿而脆弱的土黃色田地和山崗。團員們,從各自的廚房後門走出來,稍停片刻,扣上外套、戴上手套。這時他們看到的景色,彷彿只有非常古老、飽經風霜的房子才能撐得住;這讓他們自家的房子顯得搖搖欲墜、不堪一擊,如同時空錯置般可笑,就好像把一堆嶄新的玩具丟在屋外,結果被大雨淋了一夜。他們的車子也顯得很不搭調--大到有點多餘,還閃著糖果和冰淇淋的顏色,每濺起一次泥水,就彷彿要瑟縮一次。這些車子小心翼翼沿著殘破的道路,從四面八方往平坦寬闊的十二號公路匯集。上了公路,這些車子立刻放鬆下來,彷彿到了自己的地盤,讓身上的彩色塑膠、強化玻璃及不鏽鋼--金剛玻璃、莫比膠業、幻景塑膠、伊特鋼業,形成一條長而明亮的車河。不過最後,它們還是得一輛接著一輛轉下公路,開上蜿蜒的鄉村道路,往位於中央的高中校園前進;它們還是得放慢車速,最後停在高中大禮堂外一片靜謐的停車場。
「嗨!」演員們會害羞地彼此打招呼。
「嗨!……」「嗨!……」然後不情願地進屋去。
他們把厚重的雨靴脫在舞台周圍,用紙巾擦了擦鼻子,對著印刷不良的劇本皺眉頭,但最後還是會大笑幾聲,表示諒解,緩和僵局。他們也會一次又一次互相安慰,說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讓他們慢慢來。但並沒有很多時間,這點他們很清楚,而加倍再加倍的排練時間,似乎只有讓情況更糟。等到導演所謂的「真的要開始了;真的要好好走一遍了」的時間過去許久,情況還是一片呆滯、混沌、沉重,慘不忍睹;他們一次又一次看到注定失敗的前景:在彼此的眼神中;在道別時充滿歉意的點頭與微笑中;在大夥笨拙而慌忙地走向各自的車,開車回家,投入可能在那裡等著的、更古老、更隱晦的失敗前景中。
而今晚,離首演還有二十四個小時,他們總算有了成果。在今年第一個有暖意的夜裡,被不習慣的化妝與戲服弄得有點暈暈然的演員們,終於忘了害怕,讓戲裡的動作像浪潮一樣迎頭打來,把他們席捲而去;也許聽來確實陳腔濫調(就算是又怎麼樣?),但他們真的全心全意投入演出。誰還能夠要求更多?
第二天晚上,車河像條細長又整齊的蛇,載著觀眾陸續抵達。這些觀眾也非常認真。他們跟演員一樣,大部分年紀都在三十出頭左右,身上穿的衣服,符合紐約服飾店所謂的「鄉村休閒風」,十分醒目。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些人從教育、工作和健康情況來說,都屬於中上階層,而他們顯然也認為,這一夜意義重大。當然,《石化森林》稱不上是偉大的戲劇,這一點他們都知道,在陸續進入禮堂就坐的同時,也一再這麼說。但它終究是一個不錯的劇本,它所要強調的基本觀點,就算在今天也跟三○年代一樣適用(「甚至更適用。」一個男的不斷對他妻子這麼說。他妻子咬著嘴唇,點點頭,瞭解他的意思;「仔細想想,妳就會發現,甚至比以前更適用。」重點,其實並不在這齣戲本身,而是這個劇團--這個勇敢的構想,這個健康又充滿希望的概念;鎮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在當地催生一個真正優秀的社區劇團。正是這樣的動力,促使出席的鎮民踴躍前來,坐了大半個禮堂還有餘;也是這樣的動力,讓他們在禮堂燈光漸暗時,屏氣凝神,準備好好享受這一夜。
帷幕升起,某個工作人員在最後一刻急忙退場,舞台後方的簾幕因此而搖晃著;後台意外的摩擦與碰撞聲,蓋過了頭幾句台詞。這些小小的混亂,再再證明桂冠劇團團員逐漸升高的激動情緒。不過這些混亂漫過腳燈傳出去,似乎更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增加了他們對好戲的期待。那氣氛彷彿在說:等等,還沒有真正開始。
定裝彩排的最後聲響逐漸淡去,桂冠劇團的演員們什麼事也不能做,只能無助地站在那裡,默默地眨著眼睛,看著空曠觀眾席上的腳燈。他們大氣也不敢出一聲,等著導演那矮小嚴肅的身影,從空蕩蕩的座位上起身,加入在舞台上的演員們。導演從舞台旁邊拉出一個摺梯,發出刺耳的聲音,踩著梯子爬到一半,然後轉身,清了好幾次喉嚨,對他們說,他們是才華洋溢的一群,能夠跟他們合作真是太棒了。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說著,掃視舞台,眼鏡發出冷冽的閃光。「我們遇到很多問題,坦白說,我多少已經說服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可是,聽我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