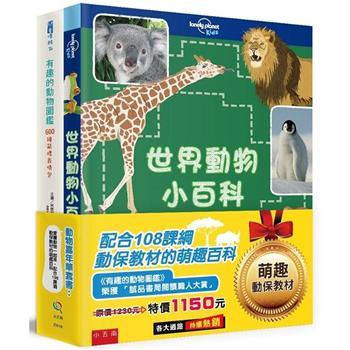李家窖子 灶王爺回宮繳旨的那幾天裡,李元泰的鬼魂就從鳳翔集上晃回家來了。還是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安安靜靜地穿過焦老太太的雞窩,焦老太太正拿著副針線給一隻吃繃了囊的肥雞縫肚子,嘴裡黏黏叨叨地數落著:「得說多少回才記得住?平日少餵了你穀皮菜葉兒的麼?能饞到這步田地—」說著一撒手,肥雞撲掀撲掀翅子,搖搖蹦蹦地走了。焦老太太順眼瞥去,正瞧見李元泰的鬼魂杵在井邊打水吃。
「回來過年啦?元泰!」焦老太太一面撿拾著方才從雞肚子裡掏出來的槍藥,一面說:「喝罷了把蓋兒給蓋嚴實;樹上那老鴉老往井裡給我拉屎,誰喝了誰鬧咳嗽,年前非找你兒子來把牠那窩給扒了不可。」
「裘老四露臉了沒有?」李元泰的鬼魂抬袖子擦擦嘴,才蓋上井蓋兒,和著碎冰碴子的清水便打從肚子上的十七、八個窟窿裡淌了出來。焦老太太向例不搭他這個茬兒,躡起小腳扭頭朝屋裡走,道:「快回家去唄!早一步還能揀兩塊冬瓜糖吃,晚了都讓窖子裡的閒漢蹭光了。」
李家窖子是早年李元泰還活著的時候挖下的。長寬各有五十丈,深可一丈五六。四圍百來根棚柱都是李元泰和裘老四、郭二竿他們哥兒幾個大老遠打沂蒙山伐回來的。棚頂上鋪著二九一十八層麥和茅草,雨雪不透。比旁的窖子還多一番考究的就是四面牆了。砌牆的那年一鄉鬧豬瘟,積下兩個多月的餿水沒處擱置,李元泰出了個主意:「把來和上泥,咱們給窖子砌一圈兒矮牆。」這牆砌得可結實,連桐油捻子的火都轟它不倒;只是長年蒸著股子餿味兒,等閒引得一頭頭逃過瘟劫的豬崽子前來舔了又舔。
到了大年下,窖子裡一開了賭,往來人等總少不得嫌怨兩句,可也沒礙著誰的手氣不是?大夥兒推牌九的推牌九、押寶的押寶、擲骰子的擲骰子……就衝著李元泰的信用和元泰嫂子的茶飯手藝,誰也沒工夫忌諱那氣味,人人下得窖來,一擄袖子,深吸一口氣,倒益發覺出年節的喜慶味兒來。
窖子的南牆緊捱著元泰嫂子的灶。打從李元泰教裘老四的一排槍子兒撂倒在鳳翔集上之後,每年臘月底,李元泰的鬼魂便一路飄回鄉來,到窖子裡和熟客拱拱手,寒暄片刻,隨後才低頭信步踅回土階,打南牆邊的角門上穿進灶屋裡去,先在撥火凳上歇息歇息,吹兩口火,烤烤手臉,一陣暖過來了,才呼喝他老婆:「和尚他娘!」吆喝罷了,便靠著柴火打盹兒。元泰嫂子自凡人在鄉裡,無論多麼遠都聽得見這聲喚,登時就撒下手邊的活兒,趕回家來。一路之上逢人便喜孜孜地傳著話:「和尚他爹爹回來了!和尚他爹爹回來了!」
李元泰死的那年和尚還不滿三歲,人若問起:「你爹爹哪?」他就拿手指往肚皮上點點指指,意思是吃了槍子兒死了。人若再問:「是誰害死你爹爹的?」他就朝東北角望一望,然後伸出右掌,拶開四根手指頭:東北角出閭門七里半,那是裘家寨子,四根手指比畫的就是裘老四了。問話的倘使還不稱意,再問他:「要不要替你爹爹報仇哇?」和尚可就不答了,輕輕低下他那頂小光頭,下手搓搓衣角—那是元泰嫂子的吩咐:「人前人後,誰要是拿報仇的話擠搭你,你一個字兒也別說。知道麼?」他要是說了什麼,難保不和郭二竿的下場一樣—別看他還是個孩子。
郭二竿是在李家窖子裡聽一個路客說起李元泰教人轟死在鳳翔集上的。當時他已經輸了一屁股;正輪著推莊,手上一副「天對」、一副「猴王」,估量著剛夠翻本兒,那路客就闖進來了,渾身上下混泥撲雪,打從棚頂和矮牆之間不足二尺寬的罅隙裡竄進來,一頭砸翻了牌桌。郭二竿掀起來一陣亂拳惡搗,直打得路客吐了一地的和血牙,才聽見他唔唔噥噥地說:「李元泰死在集上了!」下手的是自家摺過鞋底兒、換過帖的結拜大哥裘老四。郭二竿順手抄起一條門栓,翻牆出窖,沒人瞧見他是奔了東北裘家寨子、還是西北鳳翔集。當天夜裡一場暴雪來得忒急,足足積了三尺深。
雪融之後有人在窖子北半里多地的所在拾回那條門栓來,可再也沒人見過郭二竿的一根屌毛兒了。
非獨郭二竿沒了蹤影,就連裘老四也不見了。李元泰的屍首打集上抬到了家,已經是六天以後的事;正趕著臘月二十三,家家祭著灶王爺。元泰嫂子一滴眼淚也沒落,只衝著四面八方圍過來看熱鬧的男女老小磕足七七四十九個響頭,不住地說:「大年下出殃,敗了鄉親的興致,真對不住!真對不住!」一旁的和尚啥事不明白,一屁股騎上屍首的脊梁,衝人傻笑。大夥兒這才看不下去,紛紛散了。
還是地保馮大麻子差使了幾個年輕力壯的搗子,給釘了一副薄板木棺,草草收了屍。馮大麻子背著人對元泰嫂子說:「裘老四也跑了,裘家人撒下話來:自凡嫂子您開口,他們沒有不應承的—」「這我可擔待不起!」元泰嫂子陪著一臉苦笑說:「他們是八拜之交;自家兄弟合著是一條命,傷了一個就是傷了一雙。我疼,人家裘家就不疼了麼?你叫我開什麼口?馮大爺!」「好歹這是非曲直得問清楚—」「問清楚了元泰就能活回命來了麼?」「集上的人說—」「說什麼我也不聽!多謝大爺您好意。」
元泰嫂子不聽,鄉裡人可沒有不愛聽的。一連幾個月下來,口耳間翻來覆去就傳著這麼幾樁事兒。頭一樁說的是裘老四在年前一直嚷嚷著要徵捐銀、拉壯丁、買槍辦團練的事。一個替洋人吆喝火槍買賣的上海路客千里迢迢來到集上,待了三天,沒見著裘老四的面,卻聽人說起裘老四一梭亂槍打死把兄弟的事。上海路客垂頭喪氣地走了,臨走時撂下幾句怪話:「我嘛是搭他裘家人軋格朋友,才費盡唇舌,同洋人講成格樁生意;今朝碰著他格頭耍個槍花,將來連個見面格時候才嘸末噸!」
客棧掌櫃的闕日昌能通驢言馬語,把這番話嚼咕出來,大夥才明白了:上海佬是來賣槍的,以為裘老四成心耍他一記,氣狠了,傳話教裘家人留神:將來見面的時候都不好看。在裘家寨子方圓幾百里地之內敢這麼人五人六地說話,這還是頭一遭兒,至於裘家人聽沒聽見?聽見了有什麼表示?這可是誰也不敢吭問一聲的。
第二樁說的是沂蒙山桐油捻子龔瞎子。有行商年底打關外來,教大風雪給困在山坳子裡。山腰刁斗之上放哨的捻子登時擂鼓鳴號,不過幾眨眼的工夫,第一撥放槍的人馬就到了,正待下手,忽地又傳來一陣鑼響。先行的捻子發急猶豫起來;隔不多時,龔瞎子居然單人匹馬奔進坳子,眼見這滿坑滿谷的大豆、紅參和毛皮,彷彿不值半個狗屁似地,只繃著一張冷冷的棺材臉,對那幫刀出鞘、槍離套的捻子道:「隨我來!」有個貪紅了眼的嘍囉想分辯什麼,才開口,龔瞎子一聲厲吼,但見伏在他肩頭那隻金絲長毛猴兒縱身一撲,撲上嘍囉的腦袋,底下猛可一爪,打從他腔子裡掏出一粒綠油油、亮晶晶的膽來。「嗯!你的膽子不小!」龔瞎子從猴爪裡捉起那粒膽來,放進嘴裡吞吃了。
又吩咐手下人把那嘍囉抬回去:「好生給我縫上他那張破皮;其餘的—走!」還不待行商人等定過神來,進出山坳的狹路已經空了,雪地上只留下斑斑點點的血跡和千瘡百孔的蹄印兒。—要說這事兒雖然蹊蹺,可怎麼會和李元泰、裘老四的恩怨搭上干係呢?這得說第三樁風聞。
裘家寨子聽說裘老四在集上殺了人,當天派出兩個槍棒教頭、六個護院家丁,由裘家長房的大少爺、外號人稱「金瓶聖手」的裘易乾率領,奔鳳翔集探問究竟,走在半道兒上,卻讓龔瞎子給截了下來。「你四叔的事,有我料理。」龔瞎子說:「你是小輩兒,回家孵著去吧!」裘易乾見自己的人少,對面的人多,論功夫氣魄、膽力架式,桐油捻子都要高一大截兒,可是父命如山,不敢違逆,真要教對方這麼驅回去,裘家寨子百年來在地頭上扎下的威望,豈不像秋風殘葉一般,轉眼就敗沒了影兒?龔瞎子彷彿看穿了他的心事,登時笑了起來,道:「我沂蒙山和你裘家寨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你四叔和我也算有那麼點子交情,咱們犯不著為了屁眼兒大小的事傷了和氣。
不過,今天這宗案子,原不該由裘家出首問事,你當真要問,鳳翔集上誰敢不賣貴寨的面子?如此一來,哪裡還有公道底細可說?這麼不明不白地問出個什麼首尾來,江湖也罷、街坊也罷,誰能心服?」龔瞎子說到這裡,也還了一揖:「裘世兄!煩你捎個話兒給令尊裘大爺,就說是我說的:裘家寨子少問一句,這事就多明白一分。到時候兒,跑不了誰一個公道!」裘易乾提拎著這番交代回轉家門,據說裘大爺惱得很,可又拿桐油捻子沒轍,只好把兒子撲打一頓出氣,害得裘易乾整一年出不了裘家寨子,漸漸地,出入窖子的賭客都忘了他那個「金瓶聖手」的諢號—說也奇怪,打那時候起,任誰推天九牌,就是沒人拿過一對「金瓶」,彷彿這副牌就此絕了。
李家窖子的賭局倒是開得早。李元泰就只和尚這麼一個兒,照說頭七一過,就得發喪,可一來中間耽擱了六天,凡事備辦不及;二來正趕著大過年的,怕散晦氣,又拖了半個月,上元節第二天,就出了殯。正月十七,賭局就開張了。元泰嫂子跟沒事兒人一樣,依舊張羅三頓飯食、兩巡點心、九道茶水,依舊趁著手腳不忙的時節到各桌上轉悠轉悠,依舊團著張自來笑的臉招呼輸贏各家,渾不似新寡的模樣兒。久不久的,人也不覺得她髮角上那枝生綢布絞出來的小白花和腳下那雙白布棉鞋有什麼礙眼的了。元泰嫂子出入不由正門,可逢人非但沒減了親暱勁兒,倒顯著更熱呼起來,開口就是:「上窖裡來捉兩把呀!您福大手氣好,撒手掙元寶了哪!」
就這麼著,李家窖子這一年聚散抽轉的錢財,要比頭兩年加起來的還敷餘。再到臘月,鄉裡人管元泰嫂子已經不叫元泰嫂子了,叫「財寡婦」;她也滿不在乎。臘八兒這一天煮了百來升八寶甜粥,除了招待賭客之外,還給鄉裡人捱家捱戶地分送了。口口聲聲說:「財寡婦守制在身,不興給鄉親拜年;幾碗甜粥,算是謝謝鄉親的照應,不成敬意的。」眾鄉親喝了粥才見出奇巧來—赫!隻隻粥碗的碗底當央都嵌著一枚通寶;不消說,還是純銀的。倒是在送粥的時節,又傳出一檔子閒言,有人總見元泰嫂子對幫著分送甜粥的焦老太太說了一句悄小話兒:「他準來麼?」焦老太太拍拍她的手,深深一瞑眼皮:「準來的!你等著唄!」
這話再一傳開,就不怎麼中聽了。說是焦老太太邪門外道的把式多,想必是相中了財寡婦的家業闊綽起來,便攛掇著給說扯了一門姻緣。財寡婦發放「錢糧」,為的就是堵堵人的口。眾鄉親吃了拿了,自然不好意思斜眼撇嘴地瞎褒貶,只是沒礙著伸長了耳朵扇子,成天到晚地打聽著李家窖子裡的動靜—有什麼生眉生眼的外路行客沒有?焦老太太聞聽這話,氣得捉起一頭老母雞來,橫刀一抹,給裂了脖子,繞著棚窩灑了一地紅灩灩的雞血,再把傷口搓合搓合,趕雞入棚,嘴裡則潑剌剌地喊著:「誰再要胡扯八道,壞了婆婆的法術,婆婆抹了他的臭爛脖子,可不管治的!」
沒有誰當真信服焦老太太的門道;可也沒有誰不怕她動刀殺人—那可是說幹就幹的。至於焦老太太究竟替元泰嫂子牽了誰來?過不幾天,誰也懶得問了。李元泰的鬼魂回家一趟,打從臘月二十三待到大年初一,也沒旁人能瞧見。要說焦老太太打通這一道陰陽門檻,落著什麼好處沒有?—那也是旁人不知道的:和尚成了焦老太太的半個兒,從此肩挑兩門擔,兼祧兩門神。
李元泰的鬼魂並不十分樂意。每回他一進灶屋,烤罷手臉,靠在柴堆上打著盹兒的時候,就琢磨起這檔子勾當來。元泰嫂子一進門,總會聽見他歎一聲長氣,問道:「和尚沒跟焦婆婆學那些門道吧?」元泰嫂子也總是陪著笑,上前摟摟他那冰柱也似的脖梗,柔聲道:「沒那些門道,你還出不了枉死城呢!—和尚還小,要學也學不來的。」李元泰的鬼魂便在這個當兒站起身子,打個寒顫,黯然說道:「別當我死了,什麼囑咐就全給忘了。在外頭混口飯吃,講究的就是一個『和』字兒,焦婆婆煞氣重,不定把和尚給搗飾成什麼德行;真要壞了和尚的性子,明年我可是說什麼也不回來了……」
話是這麼說,他可也沒少回來過,和尚的性子也沒見怎麼壞了—一個傻頭楞腦、連話也說不上三句的孩子,能壞了什麼呢?可今年李元泰的鬼魂忒憂忒躁,才由元泰嫂子攙回房,就又迸出那句老話來:「裘老四露臉了沒有?」元泰嫂子斜稜稜瞪了他一眼,道:「又忘了焦婆婆的吩咐?教你這麼瞎問來、瞎問去,萬一真問出人家裘四哥的下落,你是去見不去見?好!由你見著裘四哥,問明白當初開槍打殺你的底細,你就不冤了?」李元泰的鬼魂點點頭。「你不冤,就住不得枉死城;日後教焦婆婆往哪兒去發錢糧、打關節,召喚你呢?萬一、萬一你再喝了忘川水,下了輪迴道,投胎做人也就罷了,做了雞羊狗馬,我、我—」說著,元泰嫂子紅了眼,哽著嗓子,可虧她平日練得扎實,硬是一滴淚水也不落。「可這麼不明不白,你知道我有多麼窩囊?
城裡的兄弟們成天價唉聲歎氣的,個個兒不服;怨得離地三尺就是一片烏雲,五尺就是一團黃霧。我一年到頭兒杵在裡頭,腸子都悶臭了—不信你聞聞!」鬼魂猛一敞前襟,果真搧出一股子瘴酸味兒,元泰嫂子還迭不及眨眼,屋裡倏地一暗,夾黃夾黑的雲霧漫空湧動,桌上的油燈乍明乍滅起來。
臘月二十七,焦老太太賣出那批吞吃過槍藥的老母雞,正拾掇著刀砧案板,忽然睇見西北角漫地颳起一陣遮天蔽日的黃土來。不多時,塵埃漸落,荒原盡處掠出十幾匹騾馬影子,轉眼飆到面前,煞住蹄子,焦老太太性陰怕見人,逕自扭頭朝棚裡走,背後當先一匹健騾上的漢子開了腔:「老大娘!借問一聲:裘家寨子怎麼個走法兒?」焦老太太也不回身,順手往東北旮旯兒一指,啞著嗓子道:「出閭門七里半,有株雷劈岔兒的枯皮大槐樹,就是了。」那漢子聞言拱拱手,牽動一身機轔叮噹的鐵器,焦老太太心頭一凜,再回頭,只見一行十餘名壯丁個個兒背脊上交肩叉掛著兩排窄皮褡褳,褡褳上密匝匝縫著百來支銅釘也似的物事。騾馬撒蹄奔去,又是一陣灰黃的煙塵,可漢子們腰底、脅間和鞍橋旁邊兒插著的火槍卻在老日頭的照耀之下發出閃爍刺眼、黑白難辨的光芒。焦老太太這才覷瞇起一對夾紫犯灰的陰陽眼,掐著皺皮皴裂的指尖算了算,唸叨著:「窮禍犯帝宮,貪狼當頭,七煞出西北……肏他娘!—馮—大—麻—子—」
馮大麻子剛打醬園裡回來,渾身浸著股子豆腥味。他一聽是焦老太太喊,當下連襖子也沒敢換,一骨碌衝出家門,連跌帶撞地往雞棚奔,半道兒上還蹭了李元泰的鬼魂一肩膀,肩窩陡地一陣刺疼。焦老太太正趕了來,一把揪住他的衣襟,道:「地頭兒上有什麼動靜沒有?」馮大麻子把個腦袋搖得像支博浪鼓似地,順手指了指焦老太太緊緊握在掌子裡的宰雞刀,道:「先、先放、放下。」
焦老太太反倒把刀高高一舉,一深一淺兩隻眼珠兒「噗」的聲朝外凸了凸:「問你聽說了什麼風吹草動的沒有?」馮大麻子見識過焦老太太發狠摘了個青皮混混的心肝、啐上口唾沫,又給塞了回去—爾後那混混成年價鬧鬱氣,說起話來老犯結巴;這麼一轉念頭,馮大麻子更揪了心,趕緊歛容正色,思忖了片刻,必恭必敬地說:「什麼動靜也沒有,婆婆!大年下的,一片太平盛景—」「放你娘的狗臭屁!」焦老太太一把推開他,端端把他推進了剛轉回身來的鬼魂懷裡。馮大麻子不知怎地就站穩了腳跟,回頭瞧瞧,啥也無有,他緊了緊給扯鬆的襖襟,哆嗦了起來。焦老太太見李元泰的鬼魂還杵在一旁,便幽幽然歎了口氣,道:「今年,你還是早回吧;萬一裘家寨子鬧出點兒禍殃來,保不準明年你還進得了家門。」馮大麻子聽不懂,卻不敢不應承,搶忙點頭帶打躬,按著刺疼的肩窩便衝家跑。
「我說的是你,元泰!」焦老太太道:「聽見了沒有?」「聽見了。」李元泰的鬼魂囁聲說道:「婆婆!我央求您件事兒行不?」「除了你和裘老四那樁案底,別的都好說—我可是答應了你老婆在先的。」「不是那個,是……」鬼魂支吾了好半天,終於打了個嗝兒,噴出一陣嗆人的槍藥味兒:「是和尚的事—他是個憨實性子,我只求他能沒災少病、傻吃賴活。婆婆您那些個行當,好不好別傳給他?」焦老太太哼哼冷笑了兩聲,道:「死都死了好幾個年頭兒了,你還牽罣這些作啥?」說罷,連連搖著頭,一面朝回走,一面喃喃唸道:「就知道你家裡有個兒子;家家都有兒子哪!年頭兒不對,誰家的兒子都不好過喲!……」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富貴窯的圖書 |
 |
富貴窯 作者:張大春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2-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中文書 |
$ 253 |
小說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富貴窯
水滸傳現代版 良善豪邁百姓大翻身
兩岸三地原創說書第一高手張大春使出絕活傳唱人間事
他們也許是撚軍也許是盜賊也許開賭場也許刮碑土摻煙做買賣,但是從歸德鄉歡喜賊戶到馬鬃山的李家窖子賭坊,盜有道,匪有義,還有一肩扛責的好漢,連冤鬼都愛待住。
人間裡的窮荒惡野搖身成為江湖野性,好漢當道的鄉裡;故事元氣淋漓 宛如民間傳唱攝人心魄的歌謠。
怪譚、民間佚事、遠離廟堂的世間生存潛規則,都在鄉野傳奇的故事裡。
二十年前張大春寫的《歡喜賊》,曾經讓當時的鄉野傳奇名家司馬中原讚道:如星雲爆炸般具有強烈震撼。七個故事,將豐富的鄉野文化栩栩展現。悲苦之外,更有一份溫柔敦厚的情境。《富貴?》一書除收錄《歡喜賊》的七個故事外,另收錄續集〈刮碑記〉等六篇故事,再現賊寇裡翻身致富的這群人的新故事。
作者簡介:
張大春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曾任教輔大、文化等大學、亦曾製作主持電視讀書節目,現任電台主持人。曾獲聯合報小說獎、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等。著有《春燈公子》、《戰夏陽》、《聆聽父親》、《城邦暴力團》一 ~ 四、《最初》、《公寓導遊》、《四喜憂國》、《雞翎圖》、《大說謊家》、《張大春的文學意見》、《歡喜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我妹妹》、《野孩子》、《沒人寫信給上校》、《撒謊的信徒》、《尋人啟事》、《小說稗類》(卷一、卷二)、《本事》等。
章節試閱
李家窖子 灶王爺回宮繳旨的那幾天裡,李元泰的鬼魂就從鳳翔集上晃回家來了。還是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安安靜靜地穿過焦老太太的雞窩,焦老太太正拿著副針線給一隻吃繃了囊的肥雞縫肚子,嘴裡黏黏叨叨地數落著:「得說多少回才記得住?平日少餵了你穀皮菜葉兒的麼?能饞到這步田地—」說著一撒手,肥雞撲掀撲掀翅子,搖搖蹦蹦地走了。焦老太太順眼瞥去,正瞧見李元泰的鬼魂杵在井邊打水吃。「回來過年啦?元泰!」焦老太太一面撿拾著方才從雞肚子裡掏出來的槍藥,一面說:「喝罷了把蓋兒給蓋嚴實;樹上那老鴉老往井裡給我拉屎,誰喝了誰鬧咳...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大春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2-23 ISBN/ISSN:97895713499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