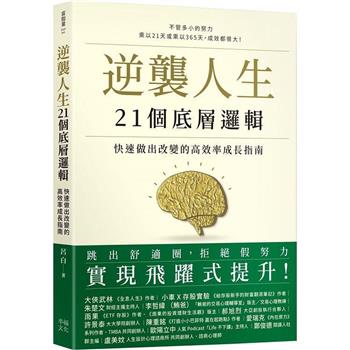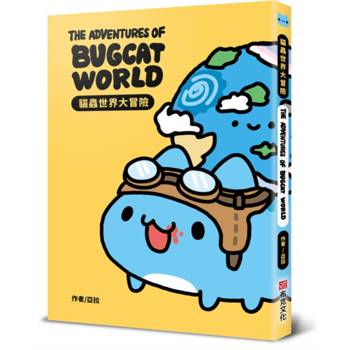古巴革命五十年,傳奇至今未了。
第一本描述哈瓦那黑手黨的紀實著作,黑手黨迷與《教父》迷必看!
二○○九年愛倫坡獎最佳史實犯罪故事 決選
本書出版期間,卡斯楚仍然健在,見證古巴革命五十周年。
大鬍子卡斯楚的革命有兩個敵人,一個是巴蒂斯塔政府,另一個就是美國黑手黨。
一九五○年代的哈瓦那,猶如一八九○年代的巴黎,一九三○年代的柏林,是許多人夢想永遠不會結束的派對,賭戲、歌舞女郎與曼波活色生香,各方政商名流、文藝人士與明星樂手雲集,而最後進場的游擊隊,用革命的槍聲使一切落幕,也留下黑手黨與革命黨人交會的一頁傳奇。
如果沒有美國黑手黨,可能就沒有五○年代的卡斯楚與切.格瓦拉。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以棒球與雪茄聞名前,曾是最紙醉金迷的溫柔鄉,豪奢的賭場、飯店與夜總會林立。汲汲營營的美國黑幫頭子,與巴蒂斯塔政府掛勾,共同「建設」他們的理想天堂。不過像田納西州一樣大小的古巴,當時是美國對外投資第三多的地方,哈瓦那儼然是世界黑幫首都,此事後來也被寫進《教父》第二集。
當時美國禁酒時期已經結束,聯邦政府打擊組織犯罪的手段日益嚴峻,對黑手黨而言,古巴代表未來出路的最大希望。在小個子藍斯基的帶領下,黑幫各大山頭挺進哈瓦那,坐擁最具規模的豪華飯店與賭場,引進最精彩的娛樂節目、最頂級的明星、最美麗的女人與最龐大的賭博事業。然而他們的夢想終將與革命黨人正面對決,這場史詩般的文化戰役,在殷格利胥筆下格外煥發出性感、糜爛與醜陋的光彩。
殷格利胥匠心獨具,避開正面評論卡斯楚,藉由貪腐時代的崩潰,鋪陳其革命的成功因素。他訪談多位黑手黨年代的遺老,揭開塵封已久的歷史。漫步今日的哈瓦那,觸目仍可見往昔輝煌世代的流風餘韻,舊日的飯店與賭場、美國製的老爺車、閃爍的霓虹燈招牌,在在訴說著這一段消逝的歲月。
作者簡介
湯瑪斯.喬瑟夫.殷格利胥(T. J. English)
擅長黑幫題材的愛爾蘭裔美國作家,在專責寫作之前,當過酒保、計程車司機、警衛等等,一九九○年出版《西幫分子》(The Westies),描寫紐約的愛爾蘭黑幫一砲而紅,開始在《花花公子》雜誌開設專欄「新黑幫」。《殺戮成性:美國最惡名昭彰的越南幫派,以及組織犯罪的變化面貌》(Born to Kill: America's Most Notorious Vietnamese Gang,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Organized Crime)與本書皆獲愛倫坡獎(Edgar Award)提名。殷格利胥也跨足影視,幫《紐約重案組》(NYPD Blue)與《情理法的春天》(Homicide: Life on the Streets)寫劇本,還因此獲得人道主義獎(Humanitas Prize)。目前長住紐約。
譯者簡介
閻紀宇
資深譯者。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副主任。主要譯作有《超級菁英》,《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別對我撒謊》,《非理性的魅惑》,《強國論》,《決斷2秒間》,《未來在發酵》,《當知識份子遇到政治》,《魔鬼詩篇》,《遮蔽的伊斯蘭》,《中國即將崩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