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重評蔣介石/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繼承性創業者」的難局
日本評論家山本七平著的《帝王學》,從「貞觀政要」中體悟領導藝術,提出「繼承性創業」的概念,認為無論是唐太宗或德川家康都屬於繼承性的創業者。乍看之下,這一名詞似乎矛盾,其初意是指後繼的領導者打開局面時,勿忘初志,保持前人的創業精神,實乃兼含創業與守成二義。創業屬陽剛,辛苦奮鬥才能獲得;守成是陰柔,必深處「憂患慎重」之中。蔣介石一生矢志恪守孫中山主義、遺志。一九二○年代孫由建國走到主導政治新局,志業尚待展開而撒手人間,蔣以軍事強人、黑馬姿態獲取大任,且以孫的繼承者自居,既要守成還得創業,革命歷程矛盾糾結,險象環生,艱苦備嘗,終其一生實未曾完成建國使命。蔣介石初期自視為革命家,既握大權,還常慨嘆「無組織、缺人才、沒情報」,對立者迭起,被視為保守主義者、現實投機者,終與民主鬥士無緣。一九四九年避難臺灣,自認感受平生未有之辱,人亦多以失敗者視之。雖以頑強意志,亟思再起,但終賚志以歿。這位「繼承性創業者」蓋棺之後,幾十年來其事業肯定、否定由人,稱他矛盾一生、一生困頓,實不為過。蔣介石的確是二十世紀複雜又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要寫好他的傳記並不容易。
二、製作的蔣介石
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個人的奮鬥史,可以反映民國歷史發展的許多重要面向,他辭世三十年仍然看不到一本好的傳記。根據柏克(Peter Burke)的說法,像法國路易十四這樣的「偉人」,形象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當然也可能被他的敵人「醜化」。從一九二○年代初葉開始嶄露頭角到七○年代中葉過世,蔣從來就不是沒有爭議的政治領袖,對他評價的消長,正反映了政治的現實與時代的劇變。早期的傳記、年表,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毛思誠編,一九三七年),熊式一的蔣介石英文傳記(一九四八年),董顯光的中、英文《蔣總統傳》,秦孝儀主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一九七八年),甚至於透過日人古屋奎二執筆的《蔣總統祕錄》(一九七四年),多是出自官方授權,刻意型塑「偉人」形象做為宣傳利器,其中多數的作品看不到蔣介石這個「人」。在中共開動反宣傳機器之前,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九四七年)應該是較早從政敵角度「揭發」蔣的負面書;待二戰後到七○年代,國共鬥爭激烈化,中共出版《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一九四八年)、《金陵春夢》(唐人〔嚴慶澍〕,一九五八年)、《黑網錄》(陳少校,一九六三年)等書,貶抑蔣為「流氓」、「草包」,把蔣等同「賣國賊」、「人民公敵」、「帝國主義走狗」,很影響大陸一般人對蔣的觀感,甚至成為當年臺灣留學生出國必讀的海外「禁書」,影響不可小覷。西方的早期著作,如林百樂《蔣介石的中國》(Paul M.A. Linebarger,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1941),項美麗的《蔣介石別傳》(Emily Hahn, 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1955)、白英《蔣介石》(Robert Payne , Chiang Kai-shek, 1969)等,內容僅及蔣的前半生,不嚴謹也不完整。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之後,在臺灣學界首見的蔣傳,是出自擅長「細說」歷史的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一九七七年)或因係匆忙推出的應景之作,最多只能是相當粗糙的「淺議」書。隨後幾年,臺灣民主化,史學研究的鐘擺,擺向政治史、人物研究之外的領域,國共關係雖開始改變,政治史材料也空前開放,但國共歷史卻都引不起史學界的興趣,蔣生平的研究也幾近停擺。不過,九○年代臺灣同時出現了對蔣看法截然不同的兩本傳記。一九九四年,旅美史家黃仁宇,出版了《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當時蔣日記還沒開放,黃辛勤的淘沙撿金,從毛思誠、秦孝儀及古屋的書中截取日記作為素材,用慣用的「大歷史」手法,把蔣的錯失歸咎於時代,給人家「小批大捧」的印象。一九九五年李敖、汪榮祖合作出版的《蔣介石評傳》,引人矚目。李說要「以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批判味十足,這種幾近「自力報復」的蔣傳,有學者評之為「雷聲大雨點小」。
有意思的是,這些年中國大陸學界對蔣介石看法有了轉變。不過在八○年代前後,仍可明顯看出中共的態度決定了學者的角度。最近二十年來,大陸學界連續出版過蔣「生平」、「傳」、「傳稿」、「評傳」、「外傳」等,不下十數種書刊,仍多在特定意識形態內打轉,不免「戴帽」、「穿鞋」貼標籤,看不到「學術」。一九八○年代初期,榮孟源以「封建吸血鬼的兒子」、「上海流氓」為蔣的身分定調,楊樹標以「肯定」、「否定」分階段給蔣定位,到近年有限度肯定蔣在抗日時期正面的戰場領導地位,直到九○年代才給他「民族主義者」的稱號。對蔣而言,或許得來不易,但嚴格說大陸學界還不能不聽「黨」的話。世紀末,有些學者(如楊天石等)開始以紮實史料為基礎,以專題研究還蔣本來面目。但迄今仍看不到一本完整學術性的蔣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同樣的轉向也在西方出現。七○年代美籍華裔學者陸培湧(品清)寫過一本用心理史學解釋蔣介石的青年時代專著(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1971),很具學術意味,可惜他沒能看到後來才公布的「蔣介石日記」。蔣過世之後,寫過戴高樂和史達林傳的英國傳記作家柯如齊(Brian Crozier)與前香港《大公報》資深記者、被中共視為「叛徒」的周榆瑞(Eric Chou),兩人合寫的《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1976)號稱第一本蔣介石全傳,內容卻沿襲七○年代中共官方對蔣的論調,以二手材料認定蔣教育少、思想保守,頭腦簡單、缺乏創見,反共不反日,是戰術家不是戰略家,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可謂陳說畢見。有意思的是這本七○年代的應景批蔣作品譯成中文,一九九二年先在蒙古呼和浩特出版,當時未受注意,到今年(二○一○)改由北京國際文化公司重新包裝上市,卻大大引起媒體矚目。中文版把合著者周榆瑞的名字刻意抹去。二十一世紀初的譯書,竟引導讀者回到七○年代對蔣的認識和評價,令人詫異。
八○年代之後,美國歷史學者開始自由進出大陸實地觀察與研究,「一覺醒來回到解放前」,對文革、對現實中國的重新認識,使漢學家重評毛澤東的個人和時代,相對的也重估蔣介石的個人與時代。芝加哥大學的艾愷(Guy S. Alitto)在一九八六年發表〈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長文,代表西方學界重評蔣介石歷史地位較早的呼聲。二○○五年,香港南華早報記者范比出版他的新作《委員長:蔣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國》(Jonathan Fen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2005),號稱是近三十年來第一本蔣的傳記。范比以西方人角度,拋開國共兩黨的觀點和框架,試圖由蔣介石的發跡到中國大陸淪失的歷史過程中,尋求蔣的角色、美國對華政策的得與失。他對蔣和毛俱無好感,但在「成王敗寇」的意識下,仍不免對蔣有武斷批評。他有新聞記者的文筆,行文引人,可惜討論歷史重要事件多用二手材料,談到蔣氏夫婦個人生活問題,多人云亦云,又喜歡用假設語式,不符史法。尤其以一九四九年為斷限,終有所不足。 顯然,加工製造寫一定看法的蔣介石,不難;寫不帶成見、真實的蔣介石,不易。
三、追尋「凡人」蔣介石
為歷史人物作傳,要能不曲筆、不隱惡、不虛美,前提是要有寬鬆自由的社會與政治環境,能找到關鍵性原始材料。過去中外學界對蔣介石的研究,都受制於「政論」與「成王敗寇」式的論定,擁蔣、貶蔣各趨極端,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蔣介石」這一人物的歷史仍未有學術研究的成熟時機;另外就是史料遲未開放,學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近年這些條件幾全成熟,西方學者最能掌握先機的是陶涵(Jay Taylor)。
二○○九年,曾為委員長之子立傳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在哈佛出版為學界矚目的新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這本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與範圍上,大大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大量使用一手史料,尤其作者是西方學者大量利用二○○六年才開放的蔣介石私人日記的第一人,這是本書絕大特色。同時作者以過去研究蔣經國的基礎,擴大且較為詳細地討論臺灣時期(一九五○∼一九七五)的蔣介石,相當程度地超越前人的論述,蔣一生功過因此有了異於往昔的完整交代。陶涵的文筆極好,特別是刻劃蔣和他身邊人物細膩動人,對史事解說常有肯棨論點,畫龍點睛之術更教人佩服。也許因外交官出身,書中對中美外交關係論述最多也最精到,史迪威事件雖屬舊題仍具新義,五○年代後金、馬外島的棄與守,曾見中美之間的外交角力,作者甚至認為蔣多次以「勒索」方式辦成外交,讀來偶會嘖嘖稱奇,但也見到蔣介石頑強特質與靈活一面。至於「反攻大陸」的虛與實,恐怕不是只靠單方面的外交文書就能推定的。書中有些論斷難免牽強,例如作者不認為西安事變有什麼關鍵性影響,說法不足服人;談蔣與周恩來亦敵亦友的關係,靠密使來推定,諜影幢幢,不無大膽。書中顯示有些問題確是一個洋學者不敢多碰的,例如蔣介石與傳統文化,特別是蔣對宋明理學的興趣;例如蔣的複雜人際網絡,兼及黨內派系和黨團關係;又如蔣日記中所表現的內心世界等,均描述不足。本書也不諱言蔣的矛盾性格,最嚴重的是個人清廉但卻縱容部屬貪腐,最後自食其果。總的說,本書對蔣一生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功大於過、譽多於毀。對臺灣學界而言,有些論述或有似曾相識、老調重彈之感,但放在西方學界或中國大陸觀點下,這絕對是一本翻案性很強、適時「重評蔣介石」(Re-assessing Chiang Kai-shek)的鉅著。
作為歷史研究者,對蔣介石的瞭解:是一介凡人、一個繼承性創業者、又是中國近代動亂歷史的時代見證人。論者早已指出:蔣既是軍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基督徒;是革命家又是傳統的護衛者;出身農家,卻與富豪名媛結褵;一生致力民主理想,執政時卻難脫獨裁形象;一位重視克己修身的道德家,卻不免容忍官員貪腐。他的確具有時代矛盾與衡突的色彩,但也決定了近四十年中國歷史的發展。在國共鬥爭中,他是輸家,但對近代中國確有諸多貢獻。他在臺灣時期的政治建設與措施,有可褒亦有可貶,但力圖與西方接軌,走向現代化也是不爭的事實。蔣介石算不上是梟雄,也稱不上是聖賢,要準確研究蔣的一生,這些論說都算面太廣、實太虛。蔣介石比毛澤東幸運,因為他較早步下神龕成為「凡人」。至此,歷史研究沒有擁蔣、反蔣的問題,學者只想知道蔣究竟是怎麼樣的平凡「人」?做出過什麼不平凡的「事」?
第九章 大失敗
東北失守,國民政府之敗或許也已注定,但國共內戰的最慘烈一役還有待開打。瀋陽淪陷之後才幾天,雙方就在華東展開這場決定命運的大戰。主要戰場在淮河北方(淮河是黃河、長江之間一條東西向流通的大河)。杜聿明率領的四十五萬大軍沒有撤到長江以南,反而奉蔣之命等候即將來臨的大殺戮。林彪的七十五萬大軍,武器精良,沒停下來休息、整備,就從冰封的東北挺進,進入關內。十一月一日夜裡,他們進攻、包圍天津。政府軍工兵炸堤、水淹天津四周運河網,構成嚴重防阻。解放軍並不放手,著手準備抽水。
更南方,陳毅率領的華東軍,利用虜獲的美、日大炮,在徐州東方約三十英里的碾莊,包圍了國軍十個師。蔣下令政府軍馳援,包括受美式訓練、裝備的第五軍及其坦克師(由其養子蔣緯國率領)。國軍向碾莊緩慢前進,解放軍在初步交戰時將它打退。委員長又祭出靜態防衛以及注定無效的救援,而且這次沒有諸如提振國家士氣或爭取國際同情、尊敬,可做為國軍必須慷慨赴義的好禮由。十一月二十日共軍突破碾莊,國軍司令官自戕,只有三千人逃出,奔向徐州。蔣傳話給蔣緯國,不能讓解放軍虜獲他的一百輛美式 M3-A1坦克,蔣緯國先把大部分坦克往南送到南京,然後自己才搭機逃回首都。然後他安排這些坦克以鐵路、平臺船運到上海,以便撤退到臺灣。
十一月九日,消息傳抵南京,杜魯門意外擊敗杜威。蔣拍發賀電給杜魯門,但也提出警告說,「民主國家或將喪失中國」。他緊急呼籲美國立即給予軍事及財務援助,希望美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中國政府對抗有蘇聯撐腰的中國共產黨;還要求杜魯門派一名美國高階將領到中國考察軍事局勢,訂定軍援計畫。毫無疑問地,他並不期望得到正面答覆。
到了這個時候,絕大部分中央軍高階將領已對局勢感到絕望。有些將領如何應欽,已準備飛往廣州或其他地方,有些則已經前往臺灣。行政院會議命令非軍事機關遷往重慶和廣州兩地辦公。副總統李宗仁公開主張停火、談判,明白表示委員長是「唯一的絆腳石」。在這種戰敗、絕望的低迷氣氛下,蔣仍保持他儒家的鎮定。司徒雷登也說蔣出現令人困惑的「自信、沈著」,以及近乎「亢奮的情緒」。當週的《時代》雜誌也登出一則封面故事,描繪「在災禍集聚的漩渦中」,蔣「愉快、堅定」,在他的私人地圖室忙進忙出,接見數十名訪客,並以長途電話對前敵指揮官下指導棋。他曉得下一步要往何處去。
美國聯合參謀本部和麥克阿瑟現在明白,蔣在中國某地守住與中共分治的微小可能性,已不復存在。即使最親蔣的共和黨人也不主張動用美軍部隊去拯救國民黨。
十二月十四日,解放軍包圍北平,守將傅作義統轄二十四萬沙場老將,卻派人洽降,展開漫長的祕密談判。傅要求蔣准他辭職,但蔣拒絕了,告訴傅別把勝負看得太嚴重。他說,輸可以給我們教訓、使我們更堅強,「亦不為革命歷史之羞」。傅回頭繼續和毛澤東祕密談判。太原方面,老軍閥閻錫山和十萬部隊深溝高壘,固守在三十六公尺厚的城牆裡。
同樣是十二月中旬,杜聿明所部僅剩十三萬人,被包圍在安徽、河南交界處。杜的其他兵團還有十萬之眾被切割成小股兵力、遭到殲滅或投降。出乎意料的是,指揮這個戰場的鄧小平並沒有猛攻杜聿明已被包圍的部隊;這些國軍部隊住在帳篷或露宿於零度以下的天候中,靠空投補給存活。委員長要求杜聿明別試圖突圍南奔長江,而是要往北進攻,進行最後決戰。他說,別想避開敵人,要摧毀敵人。他又說,這個攻擊將是一舉扭轉情勢使之有利於我的關鍵。
蔣曉得杜聿明部隊,甚至傅作義、閻錫山部隊的命運已定,但是基於軍人的使命,以及退往臺灣需要更多準備時間,蔣需要杜「戰至最後一兵一卒」。蔣可能也不希望在歷史上留下隔江分治中國的罵名。此外,他不肯全面退守長江可能也是因為不想讓大軍落入副總統李宗仁手中。蔣一旦下臺,李必將繼位,或許會期待能爭取到美援。無論如何,蔣起碼排除了在中國大陸某地劃界固守的方案。聖誕節時杜聿明報告說,他的部屬「吃樹皮、草根,為了取暖只好燒房子、衣服和家具」。可是,這十三萬忠貞部隊,只有一萬人降敵。
白崇禧從武漢行轅致電委員長,指出長江以北軍事作戰已經全面潰散;他又派出密使,要求蔣下野。副總統李宗仁也提出同樣的計畫,公開談論委員長的辭職。自從抗日以來,蔣、白即發展出親密關係;因此由白提出此議,肯定令蔣愕然。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日記寫下:「桂白逆謀之畢露,內外幾乎皆受其買空賣空虛偽煽惑之影響。」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即新年除夕,他發表聲明宣稱:「對當前國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同時,蔣夫人努力奔走、試圖爭取美援,卻一事無成。蔣承認大陸局勢已「成不可收拾之勢」,但仍「泰然處之」。在他儒家克己復禮的思緒下,他甚至認為在這場大災禍能不憂懼,「不可謂修養之無進步也。」也就是說,他變成更好的人了。
蔣在年終檢討寫下:「各地敗戰消息如雪片飛來,華北和關內岌岌可危。」得知開封、鄭州之間鐵路已斷,蔣下結論說:「國家已亡。」可是,他仍說自己「須臾不敢放鬆」。自勵即使時局動盪,仍能重建浙江到江西的鐵路,以及若干座水壩。他說:「我們必須完成一些東西,不論環境多麼惡劣……我不覺有過,我已盡了全力。」雖然他考慮退守臺灣的想法已逾兩年多,這一年來也認為退守臺灣是最可能的結果,但自從兵敗東北,其實退守臺灣早已成定局。
即使如此,蔣在新年元旦日記中正式檢視他留任的理由,以及他應該下野的理由。留,只有模糊、不確定之得;走,則是因為-「甲,痛惡現在黨政軍積重難近,非退無法改造,不得整頓;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丙,另起爐灶,重定革命基礎。」他告訴白崇禧,任何和平方案一定要中共保障長江以南仍能繼續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理架構和生活方式。他說,為達成此一目的,任何犧牲-包括把你、我「當戰犯吊死」,都不礙事。當然,他曉得這情況發生的機率等於零。一月中旬,他已把海、空軍總部移到臺灣;到了六月,國民政府空軍在一月仍剩下的千架左右飛機,已有六分之五進駐臺灣。上海及江南若干工廠和兵器廠,也已開始把最好的設備拆卸、運往臺灣。
這些動作根本無從隱瞞,但遵循《孫子兵法》的蔣兵不厭詐,仍需部署欺敵之計。目標是混淆視聽,讓毛認為固然臺灣是蔣最後的避難所,但是他還有其他選擇,包括在華南或西南若干地方堅守待變。毛的確擔心,一旦蔣下臺、李宗仁繼位,美國會以大量援助支持新政府,甚至出動戰機和部隊試圖在長江以南維持一個非共的中國。毛焦慮地傳話給史達林,據情報,美國有意動用原子彈和日本部隊對付解放軍。史達林可不擔心。透過他的英國間諜菲比(Kim Philby)和其他管道,他頗能掌握英、美對華政策的可能範圍-華府方面根本沒人提到這樣的軍事干預,即使最支持委員長的「中國遊說團」也沒出現這種聲音。
從上海往南的大陸各港口已經兵荒馬亂。政府官員、商人及其眷屬擠上貨輪、渡輪、拖船等各式船隻,跨越臺灣海峽。大批部隊帶著武器裝備也擠在碼頭候船。臺灣的基隆、高雄港塞爆了。委員長下令少帥張學良和愛妾趙一荻也收拾行囊遷到臺灣。許多有錢人則覺得臺灣前途未卜,沒逃去臺灣,而是逃到香港或其他地方(主要是美國)。蔣經國一度考量把太太、小孩送到香港或英國,但是他沒有錢,而且不肯接受宋家的援助。
蔣經國的青年軍幹部,現在已以政工人員之姿回到軍中復設的政治部工作。他們負責查察、過濾數十萬前往臺灣的老百姓。蔣經國還有其他特殊任務。一月中旬某天夜裡,他持父親手諭,率領一群武裝政工人員帶著卡車隊來到上海中央銀行。蔣經國先去載了央行總裁俞鴻鈞,俞恭敬地打開金庫,看著士兵把金塊、銀幣、外國鈔券一箱箱搬上卡車。不久,海軍一艘艦艇載著大筆財物沿黃浦江而下,駛往廈門-不是臺灣。這是中國財物運往臺灣兩船次的第一批。經過廈門再轉臺灣,是委員長要讓毛澤東搞不清他要退守何地的策略之一。
一九四八年底,經國也負責把第一批為數上千的北平故宮博物院藏品,用兩艘海軍船艦運到臺灣。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領東北之後,蔣介石下令將一萬九千多箱故宮珍藏,先運到上海、轉南京,再溯長江、過三峽而至重慶,藏在四川山區。一九四六年,它們回到南京,但迄未開箱。一九四九年一月,經國又督導另外兩次運載任務,連同這批藏品的典藏人員一起送到基隆港。總計約有三千八百箱運到臺灣,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二十二,不過它們是故宮收藏的精華。
一月六日,解放軍終於對困守在安徽青龍集、又冷又餓的杜聿明部隊發動攻擊。杜聿明拍電報給委員長說,他已盡了全力,準備做最後的反攻。他提到因為最近捐了一顆腎給他的兄弟,導致腎臟疼痛。蔣答覆說他身邊沒有其他具備作戰經驗和鬥志的高階將領可以替換杜。接下來幾天,杜聿明部隊在共產黨徵集民伕所挖的同心圓壕溝中,和共軍進行激烈的白刃戰。一月九日,杜以電報報告,他的精銳部隊已全部摧毀,他和殘部只能「戰鬥到底」。蔣告訴杜,次晨會派一架飛機去接他出來。可是,次日黎明,蔣獲悉解放軍已犁庭掃穴、圍捕杜及其殘部。在第二次緬甸之役告捷的這位Y部隊名將,證明他英勇、忠誠直到最後一刻:接下來二十五年,杜的身分都是戰俘。由於認為對杜聿明及其部屬應負責任,蔣自我安慰,慶幸沒有早早下野交出總統大權。他在日記寫下:「我問心無愧。」
一月中旬,毛澤東發表和談八條件:包括懲處戰犯(除了宋慶齡之外,蔣、宋家族統統在列);廢除「偽憲法」;「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換句話說,國民黨要無條件投降。若情勢反過來,蔣也會有同樣的要求。
四天後,蔣主持最後一次會議。當出席人士多數主張停火、和談時,蔣表示他預備放棄總統職位。一月二十一日,他非正式地「引退」,交出中華民國總統和三軍統帥的權力,但他不是「退休」或「辭職」。副總統李宗仁明白此語意的重要性,因此李只是「代總統」。蔣還留著國民黨總裁的身分,還保有多數國民黨殘存將領的支持。
次晨,蔣再次扶案寫下他簡短但十分坦誠的分析,檢討一度強大的政府何以潰敗。這一次,他沒有責怪馬歇爾或美國。他說:「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適合現在之國情與需要,而且並未成熟與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他再度暗示致命之失是他領導的黨、軍不團結、分裂、無紀律,還有他本身未能建立一個現代化、有效率的組織。他的結論是「今後立國建軍,以確立制度為最重要」。
蔣從來沒從國家偷錢,也沒有私有的金庫。為了支應他遷到臺灣之前的開銷,他向陳立夫主持的中國農民銀行辦貸款,借了一百萬元快速貶值中的金圓券(依那時的官方匯率為一萬美元)。同一天,委員長和長子蔣經國坐一輛黑色大轎車,在維安車隊的陪同下前往紫金山。經過二十分鐘的車程,父子倆來到孫中山陵寢。中山陵的拱門鐫刻著很可能是蔣親選的兩個字:「博愛」。下了車,父子倆緩緩走上八段的陡石梯,偶爾佇足休息。他們把保鑣留在外頭,兩人獨自走進陵寢,在中國現代革命之父的雕像前,直直站著、低頭不語。
摘自本書 第九章 大失敗
〔導讀〕重評蔣介石/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一、「繼承性創業者」的難局日本評論家山本七平著的《帝王學》,從「貞觀政要」中體悟領導藝術,提出「繼承性創業」的概念,認為無論是唐太宗或德川家康都屬於繼承性的創業者。乍看之下,這一名詞似乎矛盾,其初意是指後繼的領導者打開局面時,勿忘初志,保持前人的創業精神,實乃兼含創業與守成二義。創業屬陽剛,辛苦奮鬥才能獲得;守成是陰柔,必深處「憂患慎重」之中。蔣介石一生矢志恪守孫中山主義、遺志。一九二○年代孫由建國走到主導政治新局,志業尚待展開而撒手人間,蔣以軍事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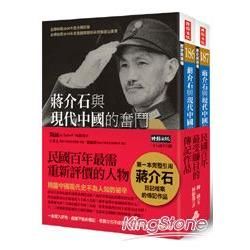

 2016/04/13
2016/04/13 2014/08/17
2014/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