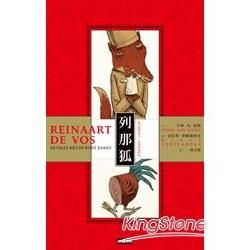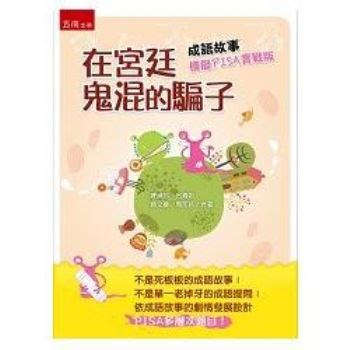導讀1
黃鼠狼給列那狐拜年--各安各的壞心腸 林則良(詩人、小說家)
列那誠懇地說:「……這個世界的人彼此欺騙,其中最高明的騙徒就在朝廷裡!不會說謊、不懂得阿諛諂媚的人是當不了國王的寵臣的。說實話並不難,但事實通常很無趣。謊言能吸引人,而且通常比較動聽。……或許國王是唯一一個可以隨時隨地說實話的人。可是你要如何變成國王,何林貝特?」
「我不知道。」何林貝特說,他覺得談話的內容太過沉重了。
「通往王位的路是用謊言鋪成的,」列那說:「我很確定。」─── 《列那狐》
「哎,」老鼠說:「整個世界一天比一天萎縮變小。起初它大到讓我畏懼,我跑呀跑呀跑的,當我看見不遠處左右有牆我還開心得很,但這些長長的牆面立刻變得狹窄,以致於我落在這小小的房間裡,沒辦法我只得撞進屋腳的陷阱裡。」
「你換個方向就不會了。」貓說完便將牠吃進肚子裡。─── 卡夫卡,〈小小寓言〉
「惡德」傳統的極致展現
列那是一頭有著紅鬍子的狐狸,他淫「狼」妻子,戕害弱肉,能吃的都騙來吃,不能吃的都騙來戲耍、提供娛樂(「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啦,哈哈哈!」—把黑的講成白的,黑白「狐」君),死到臨頭「貓哭耗子」裝嚴肅懺悔,上絞刑架舌粲蓮花,誇先父之德,以黃金誘惑獅子王諾伯爾,更以死無對證、滿口雌黃來賴罪,最後深受君王寵幸,其狡猾被視為聰明才智一舉榮登全國皇室公關。
這樣一隻以惡德爬上鳳凰枝頭(遂取而代之)的狡狐,以法文命名:《列那狐小說》(Roman de Renart),在中世紀從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這個幾世紀以來被德國法國畫過來畫過去的地區,擴張到法國然後歐洲陸地,竟最終成為法國最受歡迎的精神領袖?這是將法國的「惡德」傳統推上極致?或者是對法外之徒的「必須犯罪」,是進行哲學辯證的最佳「似非而是,似是而非」(paradox)?
「人性」和「野性」的歷史交纏
讓我們先倒帶,回到「很久很久以前」,那些狐狸就只是(或只叫)狐狸,狼就只是(或只叫)狼的年代,亦即我們的「後搖籃時期」。我們(一群「小野獸」)就隨著這些會講人話的動物,一起被「馴養」成人,像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狐狸;為誰跑最快而爭吵的烏龜和兔子;老是喊狼來的放羊的小孩(古希臘《伊索寓言》)。一隻被百獸之王嘲笑的牛虻卻叮得牠盛怒又抓又咬自己,因而遍體鱗傷;兩度瞎眼掉進兩戶黃鼠狼家,一說自己是「老鼠」,一說自己是「鳥」,因而倖免於被吞下肚的蝙蝠(法國《拉封登寓言》);或者童謠「我揹著我的房子走路…我揹著我的房子爬樹。」(楊喚,〈蝸牛〉)。等到大了,動物不必再說人話(成為暗號和隱喻),警世哲理依舊隨處可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說苑》);「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記.世家》)。動物如影隨形,其「狗」活的警世之道,在指桑罵槐的表面玩笑裡,成為道德和「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間,彼此相互拉扯的「一命懸絲」。因而在動物寓言裡,「擬人」在天平兩端的律法和本性間溜滑,讓道德懸而未決。
「有腦袋就保得住腦袋」的小聰明
這些動物寓言全有著相當鮮明而幾乎一致的個別性(簡直可以直接置換成各國的字母或者注音「狐」號):貓必然生性多疑;狼必然常餓肚子、呆又貪婪;羊必然溫馴;雞必然生一窩;獅子必然是王;而狐狸必然狡猾 & &但讓《列那狐》推到最極致的,除了它常以鄰近國家語言所命名的動物、近親和遠親脫離科屬種的動物血緣,以及常開的地理距離玩笑之外,它更接近中世紀「黑暗世界」庶民的風俗奇譚,宛如套了動物外衣的《十日譚》、《坎特伯里故事》(或晚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相對於人的世界、進而諧仿於人的「化外」(異地),對昏瞶的封建君王,對教會神學,對人云亦云、見風轉舵的一般無知市井小民,進行指桑罵槐、厚黑學式的嘲謔以及善惡的滲透換血。這些也將《列那狐》對生命的不確定性、倫理的曖昧,以及「有腦袋就保得住腦袋」的小聰明,全推到一個極致。
列那這徹底的惡棍最終雙贏,成為英雄。生命虛無,活著是殘酷劇場裡打著「狐」光燈歡喜跳舞的一場馬戲團:善惡走鋼索;血腥泛著田園風光;「倒錯」反正;皺眉嬉鬧 & &在較為原始版本的插圖裡,主角都套有人的外衣,旗幟或階級服飾,而在這本以荷蘭文寫就的比利時新版裡,插圖雖還原回動物但更顯奇異(歧義),不是套裝扮裝,就是雙手演金光布袋戲(並將人直接置放並陳),而斷頭的雞則像一截鋸斷了的空有外型的木頭。
動物的寓言,自己的變形
就在那麼一天,一群曾歸化於動物寓言的「小野獸」,突然褪去那層童話外皮,進入青少年,進入身體與「人」群體的戰場。身體的異化(或隱喻裡的病變),人掙扎於自身的存在(我不同於他人,我是他們其中之一),動物寓言立即轉化為卡夫卡(《變形記》裡一天醒來成了一隻翻不了身的大甲蟲)和布魯諾.休茨(裡頭退化成鳥的父親),甚而狼人、變蠅人 & &或更顯古怪的生物,與暗影同生。正如同那亙古以來的「幻想生物」(波赫士曾收集了一百二十則的《幻想動物集》),人(神)獸的同一換形(如《山海經》裡精衛:「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於是動物圖鑑裡的形象退下,換上人本思考裡的「自己的變形」。這一時這一刻的「動物」寓言,將再度回歸神話。
導讀2
從《列那狐》談西方中古時期審判制度 涂永清(成大歷史系教授)
「列那狐」(Reynard the Fox)是中古時期日耳曼地區以動物為主人翁的民間故事,目前流傳的列那狐故事主要根據法國現存的《列那狐小說》演化而來。西元十、十一世紀左右的法蘭德斯和日耳曼地區,就已經流傳一組紀以狐狸為中心的拉丁文故事詩,後來法國人以「八音節」詩句形式,重述部分故事。這部作品經過不斷修改增補,形成長達十餘萬行,由二十七組寓言故事綴成的諷刺童話詩。
《列那狐》故事經多次修改增補,故事很完整,人物性格十分鮮明。故事是說:列那狐誕生於亞當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之時。上帝把人類祖先逐出伊甸園後,基於憐憫而給亞當一根「神棍」,只要拿它去打擊海面,就可以得到需要的動物,果然亞當得到不少有益的動物;但上帝告誡亞當不能將神棍交給夏娃,因為她會帶來災禍。可是夏娃卻偷偷地使用神棍,結果變出了許多毒蛇猛獸,而狡狐列那和狼伊森格倫就是其中二隻有害的動物。
整個寓言故事的主要焦點,集中於列那狐和狼伊森格倫的鬥爭,而全書的精彩章節包括〈列那狐偷魚〉、〈列那狐教伊森格倫捉魚〉、〈列那狐的審判〉等十來篇故事,其中以〈列那狐的審判〉最著名,本書即以〈列那狐的審判〉為藍本所改編而成,整篇故事除襯托出列那狐臨危不亂的鎮定工夫以及善於抓住對手的心理外;對於社會的黑暗面及人性的貪婪、昏庸、好聽謊諛之言、殘暴自私,都刻畫得入木三分,因此許多人認為這部動物寓言具有高度的鑑賞價值。
辛克森法庭戲展示中古西方審判制
列那狐故事中敘述動物王國公審列那狐的情形,原告與被告兩造之間的辯護過程,亦是十分精彩,案情的發展亦緊扣著中古西方封建法進行。西歐十二世紀時,羅馬法雖已逐漸復興,教會法亦已存在,但各地的法律仍以日耳曼人的「習慣法」為基礎,換言之,當時並無「立法」的觀念,也就是說法律不是以立法條文為基礎,封建法是依部落或采邑的古老習慣而成的。封建法庭審理分成:「同僚審判」(trial by one's peer)、「神聖發誓」(solemn oath)或作「助誓」(compurgation)、「神斷法」(ordeal)還有「司法決鬥」(judicial combat)等。
所謂「同僚審判」,通常是某一封建附庸被控違反封建法時,要求「同僚」組成法庭審理相關的案件,避免領主單獨處理導致其權益受損,有人認為這就是西方「陪審制」的濫觴。「神斷法」或「神意裁判」,基本上是為救濟神聖發誓(助誓)的不足而採取的辦法,即被告提出的證據薄弱,難以取信於法庭,他個人的神聖發誓,或證人的保證,均無法證明他的清白時,上帝的判斷就成了最後一道關卡。按規定被告要受冷水、沸水或烙鐵的試煉,以決定其是否有罪。而《列那狐》一書裡對列那狐公審所採用的審判法,主要為「神聖發誓」和「司法決鬥」。
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法庭公平
「神聖發誓」是根據《薩利克法》(Salic Law)、《盎格魯撒克遜法》(Anglo-Saxon Dooms)或其他日耳曼人的類似法律而來:要是甲(原告)擬告乙(被告),法庭會先傳訊被告,被告若未依規定到庭,法庭則授權原告採取任何方法強制於被告;惟被告準時到庭,並提出適當抗辯,則原告要按封建法規定正式提告,被告亦以同樣方式抗辯。在兩造攻防答辯過程中,被告必須提證證明自己清白,或採免罰宣誓以證明清白,或請人擔保其誓言,即所謂的「神聖發誓」或「助誓」。過程非常繁複,原告必須完全記住所有的誓言和證言,反之,被告亦然,但如果兩造中有某方的本人與保證人在口頭證詞中稍有差錯或漏洞,這場官司他就敗了。
這種審理方式表面看是公平的,但實際上有差別性,因為當時在法律面前並非人人平等,全然取決於社會地位的高低,因此就有「發誓價值」(swearing worth)的差別,當時一個貴族的發誓就可抵六個普通人;名聲狼藉的人在法庭上還不能作免罰宣誓證明自已的清白。此外,如貴族殺死一個自由人,有七個人助誓便可脫罪;一個自由人殺死另一個自由人,則需十一個人幫其助誓。由此可知,貴族與平民的身價是不同的。《列那狐》故事中再次公審列那時,母猴露肯瑙對列那的仗義執言,以及其他親友加入站在同一陣線,即屬「神聖發誓」或「助誓」的絕佳例子。
狼辯不過狐,遂提決鬥險招
決鬥其實也是一種神斷法,這種以決鬥定輸贏的神斷法盛行於法蘭克(今法國北部、德國大部份和局部義大利),而《列那狐》的舞台,就是法蘭克的一部分,因此故事結尾時安排了狐與狼的決鬥。決鬥由狼提出,因他在法庭上說不過能言善道的列那,為扳回劣勢遂提出了這招險棋。只是他未料到列那會採取封建騎士所不屑用的謀略戰,加以他的前爪已被列那做了朝聖鞋,身體有傷行動不俐落,以致未能在體型與力道上占上風,反遭慘敗。而列那不但獲得清白與自由,更得到加官進爵的機會,成為獅王諾伯爾的執行官兼發言人。
決鬥可說是中古封建社會審判法中的下下策,一般而言領主在附庸間發生糾紛時,會進行疏通、調解,希望兩造能和解。若調解不成,雙方即在領主許可與監督下,擇日以武力解決彼此的爭端,雙方決鬥時,主持人和旁觀者都要保持超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也不可加以干預,惟當某一方損失過於慘重,影響其義務之履行時,主持人(領主)就會出面干涉,這也就是《列那狐》故事中,當決鬥分出勝負時,狼伊森格倫的親友懇求獅王諾伯爾下令停止決鬥,而獅王也及時宣布停止決鬥的原因。列那在接到停止決鬥的命令時亦表明:「國王的意願對我即是命令。」
列那狐故事中文版的歷史意義
《列那狐》一書譯文流暢,插畫十分可愛有趣,而故事情節的開展是從森林王國對列那狐控訴與公審起,讀者透過雙方攻防辯證過程中,可了解列那狐如何作弄其他的動物,也看到列那狐奸詐詭譎,自私自利的性格。但列那腦筋機靈能用智,因此二次面臨吊刑時,利用人性貪婪,好聽阿諛的弱點,以虛構的寶藏逃過死劫;更妙的是,知道寶藏者竟然均為已逝者,大家在死無對證狀況下仍被列那的故事所眩惑。列那利用死人虛構黃金寶藏的情形,讓人想起《伊索寓言》中,曾有一段描繪好說謊而不臉紅的狀況:「你盡量說謊吧!沒有一個人會從墳墓裡跑出來揭穿你的謊言的。」
《列那狐》故事經過長期演變改寫,但迄今仍廣受人們普遍喜愛,法國人仍以「列那」(renard)稱呼狐狸,取代原來通用的「goupil」(狐狸)一字;十三世紀時,法蘭德斯作家以法文版《列那狐》故事,譯成了荷蘭文及日耳曼文之散文著作;英國作家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的《坎特伯利故事集》(Tales of Canterbury)一書中〈女修道院教士的故事〉(The Nun's Priest's Tale)一文,乃仿《列那狐故事》而成(按此故事敘述公雞、母雞與狐狸間,彼此鬥智、欺騙的故事);英國出版商威廉.卡克斯頓(Wolliam Caxton, 1422-1491)發行廉價的《列那狐》普及版出售;甚至德國大文豪歌德(Goethe, 1749-1832)也曾寫過《列那狐》(Reineke Fuchs)。由此可知《列那狐》的故事受人歡迎的程度及流傳之廣。
譯者杜子倩小姐今直接從荷蘭文譯出的《列那狐》,是部老少咸宜的動物史詩作品,相當值得一讀。而更有意義的是,本書幫助台灣與低地國文學(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做了接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