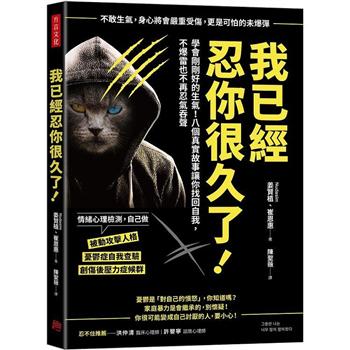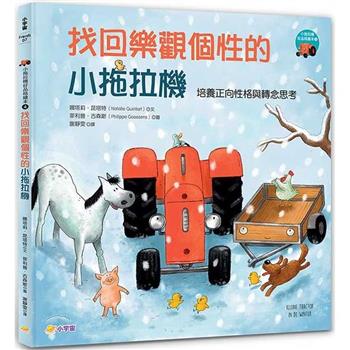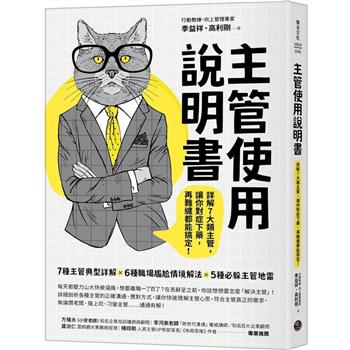推理書迷的至高品味--雷蒙.錢德勒(1888-1959)
村上春樹最愛的小說家,譽為二十世紀罕見的「完全小說家」
美國推理作家協會WMA「150年來最出色推理小說家」 第1名
偵探馬羅系列第3號,全新譯本,本書三度拍攝成電影
偵探小說當中難得一見的愛情
《再見,吾愛》1940年出版,瑞蒙.錢德勒第二部以洛杉磯私家偵探馬羅為主角的小說,是偵探小說當中難得一見的愛情物語,集浪漫、憂傷、華麗、驚險和死亡於一身。
一宗普通的黑人謀殺案?一張被藏起的少女照片?價值連城的珠寶卻被平價收回?
事情發生在中央大道一個族裔混雜的街段,那時那裡黑人還沒有完全變成黑人區。那天馬羅剛從一家理髮店走出來,馬羅的客戶說他要找的理髮師可能在那家店工作。
馬羅只是幫理髮師的妻子尋找先生,卻意外被捲入一樁古怪的愛情故事中:一名身高七呎、才出獄不久的巨漢麋鹿摩洛伊,多年後正在找尋他所摯愛的紅髮歌舞女郎薇瑪,摩洛伊無意間殺死了弗羅里安俱樂部的黑人經理,馬羅是唯一的白人證人。馬羅拜訪了俱樂部前經理的遺孀──酒醉的放蕩女子……似乎,薇瑪已經去世了。
稍晚,馬羅受雇於林賽.馬里歐特,協助馬里歐特的一位女性友人,轉交一條價值超過八、九萬翡翠項鍊的贖金八千元。會面的時間地點是午夜在峽谷中。然而,馬羅遇襲;馬羅醒來遇見路人安.李奧丹,而安發現馬里歐特被謀殺了……。
在安的協助下,馬羅得知項鍊的主人是葛雷耶夫人。馬羅前往拜訪夫人,夫人是位嫁給年長富豪的金髮美人,她告訴馬羅,該條項鍊被歹徒搶走了。
馬羅調查與馬里歐特的相關疑點,發現了一張「心理顧問」裘爾斯.安索的名片。同時馬羅發現弗羅里安俱樂部前經理的遺孀,她住房的所有人登記者居然就是馬里歐特。馬羅和裘爾斯.安索約在安索山頂「現代化」的家見面,馬羅卻被壞警察痛打一頓。接下來馬羅被移往一處療養院,注射了麻藥……。前經理遺孀被發現陳屍家中。
馬羅回到了他位於好萊塢的公寓,葛雷耶夫人找到了馬羅的藏身處。兩人談話中,發現了薇瑪和夫人的關聯。
《再見,吾愛》寫於《大眠》之後,卻是最先搬上大銀幕的馬羅故事。1942年電影《獵鷹接管》就引用了《再見,吾愛》小說情節。1944年電影《謀殺,我的甜心》即以小說為藍本,該片在英國上映時,片名恢復和小說同名。三十年後的1975年,《再見,吾愛》三度拍攝成電影,羅伯特.米徹姆飾演馬羅這位私家偵探硬漢。
作者簡介
瑞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生於芝加哥,但因父母離異,隨母遷居倫敦,錢德勒的童年都在英國度過,大學念的是杜爾威奇(Dulwich)學院,成年之後返回美國加州定居。
錢德勒開筆甚晚,45歲才正式發表第一篇小說〈勒索者不開槍〉,刊載於當時的廉價雜誌《黑面具》(Black Mask)上,然而,錢德勒和達許.漢密特所領軍的這批廉價小說,卻成功的推翻了英國古典推理對美國偵探小說的宰制,開啟了美國本土冷硬派私探小說的傳統,是為推理史上有名的「美國革命」。
錢德勒逝於1959年,畢生共完成七部長篇和為數廿部左右的短篇。其中以偵探馬羅為主角的系列更是他寫作的高峰。馬羅就像海明威筆下的硬漢,即便處境艱難也不肯拋開君子風度與誠實價值,每每讓讀者受到震撼。深愛馬羅系列作品的西部片名導比利.懷德就曾說:「錢德勒的小說,每一頁都有閃電。」錢德勒的電影劇本也是其重要的創作。
雖然以通俗小說起家,錢德勒的作品卻深受文學名家艾略特、卡繆、錢鍾書、村上春樹等人的喜愛,在西方文壇更有「犯罪小說的桂冠詩人」之稱。錢德勒以馬羅為主角的系列作有:《大眠》、《再見,吾愛》、《高窗》、《湖中女子》、《小妹》、《漫長的告別》、《重播》。
譯者簡介
許瓊瑩
台北市人,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美國芝加哥帝博大學電腦學碩士,曾任電腦程式分析師,長期僑居美國,近年返台定居專事翻譯。譯作廣泛,包括兒童教育心理學、文學、推理小說、大眾科學暨史哲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