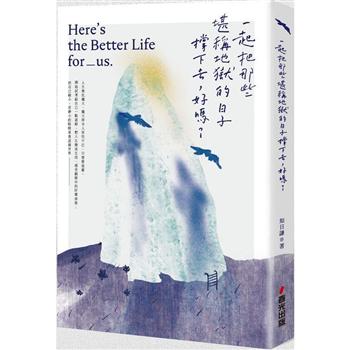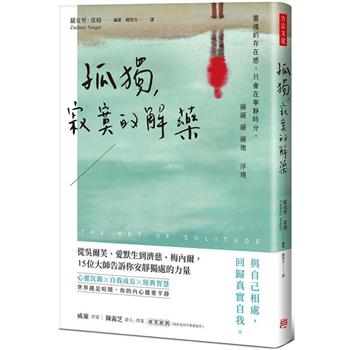他那支筆是怎麼練的?──讀李長聲
一到東京,就認識了李長聲,那是二○○八年的春季。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很快成為朋友,似乎是認識很久的朋友。你問日本的歷史,他能告訴你;你問日本的風習,他能回答你;你問日本的文學,他能說出個子午卯酉來;連點雞毛蒜皮的問題,也能給你個完滿答案。單這個本事,我就佩服得不行。用父輩的老話形容,叫「日本通」,今天則稱之為「知日派」。
去東京的淺草寺,離廟門尚遠,已然人流如織,熙熙攘攘。很敗興!看看旁邊的李長聲,走得精神抖擻,講話興致勃勃。我不禁問道:「你陪國內的朋友來過多少次了?」
他淡淡一句:「無數次。」
在販售紀念品的商店裡,我拿起一個銅製菊花工藝品擺弄。他雙手接過來自言自語道:「菊花,皇家紋章,十六瓣……」
聽了,頓生感動:他的自語,實則為我。既讓我知道這非同小可的日本菊,也意在保全「章大姐」的體面。
我們一起到日本現代美術館,參觀「紀念東山魁夷百年誕辰畫展」。觀後出來,早過了午餐時間,又渴又餓。路上,碰到一家紙店,我興致陡起,不管不顧地一頭鑽進去。東挑西撿,搞了半日。李長聲默默陪我,靜靜等我。出得商店,我突然想起:他有糖尿病,是需要及時進食的。
返京的日子到了,李長聲開著漂亮的「雷克薩斯」送我去機場。分手時真有些捨不得,希望他的話匣子老開著。由於帶的書太多,超重了!日本小姐二話不說,隨手在一張A4複印紙畫了幾筆,舉到我的眼前。一看:一萬七千 !心想,這肯定是「罰金」了。回到北京,用「伊妹兒」告訴李長聲。他在郵件裡回覆道: 「不貴,大姐,一切都值得。」
以細節識人,大抵無誤。從此,「長聲兄!」我叫得爽爽的。
李長聲待人好,書也寫得好。筆下,頗有苦雨齋的派頭和味道。一副閒適沖淡的神態,寥寥幾筆卻言之有物,清爽簡約的文字是極其考究的。寫春色,如嫩竹;話秋色,似晨霜。舉個例子吧,那麼多的人描寫日本櫻花,說它如何之美麗,怎樣地清雅。不承想我們的長聲兄將它比做潑婦,「嘩地」開了,又「嘩地」落了,神了!
李長聲所寫,涉及範圍極廣。像個萬花筒,拿起輕輕一搖,就是一幅日本社會圖景。五色繽紛的,煞是好看。而他所寫,又無一不是日本現實中的人、事、物、景,結結實實的。筆觸始終落在「實」的社會生活的層面上,這使得他的文章有著非常執著和強悍的內容。不像某些東渡客,給我們送來洋洋灑灑的日本觀感和色彩極佳的圖片,看著總不免輕飄浮蕩。依我淺見:再宏偉的敘事、再華麗的文采,「文學」的大廈都需要一個「實」字碑做基石。李長聲的作品很實在,不易被時間和時尚淘洗,即使再短的小文,你也會有所得。是啊,文學比戰場更慘烈|被剽竊,被查禁,被金錢收買,被政治打壓以及整體「邊緣化」。但是,並非所有的春花,惟有到了秋日,才能確認它的存在。
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物景,牽引出李長聲的喜怒哀樂。這些具體又真摯的感情以一種灑脫的態度,將文思推入到「性靈」的層面。文壇上常說的「獨抒性靈」,簡單說來,不就是指作者能對「人」有所認識,且不斷深入嗎?換言之,也就是作家能以個體生命去體驗人類生存途中所共有的基本狀態,包括各種心緒、心理。李長聲善於思考,文筆上佳,許多人還記得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好文章。我想,堅持真實的、自由的「個性」筆墨,當是他成功的奧秘。
李長聲另一特點是在「實」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長期觀察與潛心思考,融入相關的|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民俗的、心理的、地理的各種因素,彼此交叉、演化、滲透、合力推進,最終完成一個文學主題。日本藝伎是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也多少與我的專業相關。對這個延綿數百年的事物,李長聲寫得縱橫馳騁,自與別人不同。從藝伎歷史淵源、名稱演變到職業規範,仔細道來,並澄清了國人的許多誤解。他在《風來坊閒話》一書裡,告訴我們:藝伎集中住地叫「花街」,又稱「花柳巷」。但花街不是娼妓館,藝伎賣藝不賣身,「以歌舞彈唱為能事。客人談事則默然斟酒,客人取樂就陪著談笑遊戲。」她們的服務「現在以兩小時算帳,而在江戶時代則以燃盡一根香計算時間」。李長聲又說,藝伎從少女時受訓,「像日本庭園一樣,看似自然,其實是極盡人工。」連她們穿怎樣的木屐、哪隻手提和服的下襬等瑣細之處,均有所交代。其專業化程度,不亞於戲曲服飾、穿戴制度研究。李長聲非但有很好的社會洞察力,且視線廣泛。他能從藝伎與政治家、文學家的往來關係方面,開掘出更深的文化內涵。前者有伊藤博文、田中角榮、小泉純一郎,後者如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渡邊淳一。政治家包養藝伎的傳統風習,使藝伎日後有了寫作的本錢;而文學家則用生花妙筆,將她們寫成了國色。難怪李長聲歎道:大和魂實質不是好戰,是好色。
筆走到此,準備「收官」,不想臺灣遠流出版社給我寄來他的新作《東京灣閒話》。翻開目錄,立即看到「搞笑藝伎」的篇目。花街女子是日本歷史的一抹餘暉,它既是人們樂此不疲的談資,也是作家反覆咀嚼的素材。但像李長聲寫得如此出色,畢竟不多。
李長聲寫飲酒,寫捕鯨,寫街景,寫書店,寫浮世繪,寫辭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闢。敘事,娓娓動聽;狀物,不厭其煩;寫人,道地白描功夫。不明白了:他那支筆是怎麼練的?
平淡瑣細之中有真知灼見,酣暢淋漓之中見深厚質樸|沒有歲月的洗禮,沒有生活的磨礪,這個文學境界是達不到的。
先天稟賦 後天學養──讀唐德剛
我第一次讀唐德剛的書,是刪節版《晚請七十年》﹝湖南嶽麓書社出版﹞。幾頁讀下來,激動得難以克制。毫不過分地說,就像遭遇八級地震,全身血脈如翻江倒海,連續幾天衝動得不能睡下。別樣的見地,別樣的敘述,別樣的文風,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我又去書店買了幾本,分送朋友。他們和我一樣,都驚了,也都快瘋了,其衝擊力與原子彈爆炸沒什麼兩樣。唐德剛提出的「歷史三峽」論如池塘漣漪,一波一波推得越來越遠。至今每與朋友聚會,唐氏關於時代變遷的主題,是我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聯繫到眼下的社會現象,也越發地引人深思。若說他是「一人敵一國」,從這個意義上講,並不誇張。
唐德剛的作品還原了歷史,這個歷史包括了人和事件,還有人與環境的關係、人與時代的關係,以及人與自身﹝即內心﹞的關係。人物是真實的,環境是實在的,時代是準確的,內心是可視的。他的語言是個人化的,充滿文學的魅力,也充滿了真知灼見。他說﹝張﹞大千之作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的,是略帶「現代新意」的「傳統國畫」,基本上和梅蘭芳的京戲一樣,都是「傳統藝術」的「收山大師」。這話,即使專搞藝術研究的人,恐怕未必能概括的這樣好。
唐德剛的一篇〈梅蘭芳傳稿〉,我都翻爛了。後來,方知竟是人家的處女作,況且還不認識梅蘭芳,怎麼寫得這麼好?神了!從此,我把唐德剛確立為自己終生效仿的楷模、學習的榜樣。學不好,也要學。於是,在動筆前和寫作過程中,我開始比較注意研究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內心之間的關係了。比如寫翦伯贊,就要好好想想政治與學術的關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翦伯贊還能化解政治需要和學術良心之間的矛盾,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受不了了,畢竟是讀了些書的。翦伯贊是主張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但他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級地伺候於政治;翦伯贊是主張學術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但他不能容忍學術如此卑賤地跪拜於權力。對於那時的教育革命和史學革命的種種做法,他有投入,有參與,有調適,但也有不滿,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衝突非常激烈,內心變化也十分複雜。畢竟政治難以取代常識,環境無法窒息心靈。可以說「文革」前夕的翦伯贊,思想上有了極其明顯的轉折。對吳晗也是需要審慎研究之後,方能下筆的。他以學術起家,未以學術為業;他成於政治,又死於政治。但我以為吳晗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政治範疇。他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符咒,是對中國的學術和學者的一個戒語。吳晗的不幸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不幸,更是時代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千年遺傳下來的根性,使很多文人、知識份子對權勢抱有敬畏,也懷有期待,期待自己也能進入權勢。關於人與內心的關係,主要指心態、心理、心緒、心情等。羅隆基一生,身邊的女人沒中斷過,即使成為右派也如此。反右運動結束沒幾年,就有漂亮年輕的女性表示願意嫁他。羅隆基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一直獨身,但一直背著「流氓」的罵名。拙作〈無家可歸─羅隆基情感世界〉,我有意集中筆墨來寫他的情感世界,以其日記、年譜為依憑,把他從小到老的私生活做了梳理。我有意識地涉及他的性心理,從形成到表現都做了點滴分析或歸納。也許說對了,也許錯了,但我覺得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
別以為「口述歷史」就是「你說我記」,口述史的優劣與高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採訪者,取決於他的史學知識、社會積累和考證功夫。唐德剛一方面善於提問,逼出傳主「說」出一切,另一方面,他能發現和糾正傳主的記憶疏漏,加以考證和補充。眾所周知,他給胡適寫口述史,胡的口述部分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內容則靠他找到相關材料加以充實﹝《李宗仁回憶錄》屬於傳主本人的口述僅占百分之十五﹞。拿《胡適口述自傳》與此前的《四十自述》對照,正如唐氏所言,胡氏「並未提出什麼新材料」,但是,唐德剛的注釋確為不可不讀的好文章!難怪臺灣學界認為,就學術意義和史料價值而言,注釋部分恐怕還在傳文之上,說「先看德剛,後看胡適」,並不過分,也非過譽。
讀唐德剛的作品常常是拿起就放不下,其原因還在於他的一支筆,能把歷史寫得非常好看,即用文學來寫歷史。史書有無價值,在於史料的真實;史書能否流傳,則在於文學的功力。唐德剛曾這樣講:「胡適用十多年時間研究《水經注》,電腦十幾秒就出來了……但是,我們史學研究還有一部分可以與科技相對抗的,那就是在史學之中,還有文學。」實踐證明,他是對的。
有人說唐德剛的路子有點野。野,是指他研究和表述歷史不夠嚴格、也不夠正統。的確,不夠嚴格,不夠正統。因為在他筆下,不但「文史不分」,且性情張揚。需要說明的是,唐德剛的張揚,決非肆意妄為,而是源於其畢生對歷史的親歷和對社會的感受,風瀟瀟,血淋淋!有了親歷和感受,就自有言說的欲望和衝動。閱盡天下炎涼,歷遍世道滄桑,唐德剛是最懂人心與人情的!一落筆,人物就有血色,時間自會倒流。那些遠去的靈魂、遺忘的歷史,都被他的筆掃到了眼前,格外生動,也格外分明。讀他的〈梅蘭芳傳稿〉,你能感受到濃濃的哀婉之情和淡淡的舊日夢痕。那既是梅蘭芳的內在氣質,也是唐德剛的海外孤魂!洋洋灑灑的文字背後是一個人的情懷!
據說,在離別二十五載之後,一九七二年他首次歸來。當從飛機舷窗眺望到家鄉山水時,激動不已的唐德剛,躲進洗手間,失聲痛哭。
「臨去且行且止,回頭難收難拾」。這是他的詩,也是他的心。
沙
我喜歡望海,我喜歡看沙。
第一次望海是在一九四七年的香港;喜歡望海則是在一九四九年即將離開香港的時候。一天,母親告訴我,一家人要北上了。
我問:「什麼叫北上?」
母親低聲說:「到北平去。」
「很遠嗎?」
「很遠。」
我再問:「北平有什麼?」
「北平有個毛澤東。」
「毛澤東是什麼?」
「一個人的名字。」
……
離港之前,母親帶著我和姐姐最後一次吃了霜淇淋,最後一次坐渡船。下午,我們從九龍渡到香港;深夜,從香港渡到九龍。望著黑黑的海水、亮亮的燈光、靜靜的港口,我突然想哭,捨不得這樣美麗的海水與夜色,還有好吃又好看的霜淇淋。我什麼話也不講了,靠著船舷死盯著海!我也知道了:北京啥都有,就是沒有海。
若問自己是什麼時候喜歡沙的?說起來可笑,是從一個裝滿沙子的玻璃瓶開始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家迎來了「改革開放」,我家迎來了隔絕數十年的海外親朋。母親從小的同學、後來成為遠親的周女士從巴西飛來。她帶來幾樣禮物。其中一件就是巴西沙瓶|一個小小玻璃瓶,裡面裝著用彩色細沙製成的一幅圖畫。我很吃驚:沙子可以成型,沙子可以有色,沙子可以成為畫作。我對母親說:
「把這個瓶子給我吧。」
母親點點頭。從這一刻起,我喜歡沙。
我去泰國,從印度洋的沙灘上,裝回一小瓶沙。
我去土耳其,從地中海的海灘邊,裝回一小瓶沙。
我去美國,從大西洋的海邊,裝回一小瓶沙。它是彩色的,由我親手製作成型。我把這幾個瓶子放置在一起,自我欣賞。
看了沙灘、有了沙瓶,我開始嚮往沙漠。特別是讀了三毛的作品,看沙漠簡直成了抑制不住的狂想。我購買的掛曆,多為沙漠圖景。太奇怪了,很多沙子飛上天空,就成了災;很多沙子積聚大地,就成為景。
二○○一年以後,我在多次的聚會中對朋友說:自己絕不貪生。一旦把當做之事做完,就自我了斷。了斷的方式有二:或向東,淹沒於大海;或向西,消失於沙漠。我的一個同事聽了如此詩意的死法,當時就表態,與我同行!人的一輩子都在尋找:從最初的找奶,到最後的找死。村上春樹也說了:「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所以我深信,死亡是可以選擇和設計的。
二○○九年夏我到新疆,終於看到了沙漠,也終於把狂想變成了狂喜。我快步而行,鞋裡全是沙。毫不在意,只想一個人獨自體味沙漠,體味沙漠之熱,想像沙漠之死:大風起兮,黃沙扶搖八萬里;我的陰魂即飛舞,也涕泣。看那浩淼的沙與海,人最有身世之感。由此,更理解旅遊於我的意義|無非是尋個名義,找個藉口,真正需要的是尋找到一塊陌生之地。面對陌生,可以暫時忘記現實,仔細回憶從前,盡情想像未來。在一個沒有靈魂的時代,它是多麼地美好。
算了算:從看沙到看沙漠,我用了六十餘年。一輩子啊!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總是淒涼調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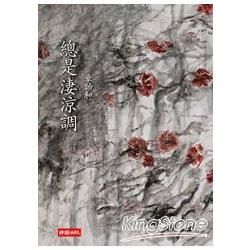 |
總是淒涼調 作者:章詒和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4-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3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中文書 |
$ 221 |
現代散文 |
$ 221 |
文學 |
$ 221 |
現代散文 |
$ 221 |
文學小說 |
$ 22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總是淒涼調
人在陰影中待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時間和生命,是無法沖洗和帶走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章詒和
大江東去響寒潮,總是淒涼調。
這不只描繪了程硯秋唱腔之所以表達這分悲傷,也刻劃了章詒和數十個寒夜裡的驚悸;他們一個用那低迷委婉、延綿起伏的純粹聲腔,一個用那嘔心泣血、如椽之筆,訴說那個荒謬時代難以言喻的傷痛和扭曲。
人生向晚,處在動蕩的政治時局與瑣細生活之間的雙重夾擊下,更加重了章詒和內心的悲情與恨意。這本書裡因有告密、臥底而顯得沉重,而這些告密者、臥底人,都是她父母的朋友,甚至還聯繫著兩代人的情誼,所以她在下筆時常淚流不止,書寫期間章詒和三赴新疆,希望天山下的一草一木和浩淼的沙,讓蒙塵的心靈得以修復,還原人心固有的溫軟澄澈。
這些殘陽裡的人物,消散了紅塵,因為現世浮華和晚世尊榮都會隨風散去。
作者簡介:
章詒和
章伯鈞的女兒。
一九四二年生於重慶,中國戲曲學院畢業,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著有:《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雲山幾盤江流幾灣》、《這樣事和誰細講》等書。
章節試閱
他那支筆是怎麼練的?──讀李長聲一到東京,就認識了李長聲,那是二○○八年的春季。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很快成為朋友,似乎是認識很久的朋友。你問日本的歷史,他能告訴你;你問日本的風習,他能回答你;你問日本的文學,他能說出個子午卯酉來;連點雞毛蒜皮的問題,也能給你個完滿答案。單這個本事,我就佩服得不行。用父輩的老話形容,叫「日本通」,今天則稱之為「知日派」。去東京的淺草寺,離廟門尚遠,已然人流如織,熙熙攘攘。很敗興!看看旁邊的李長聲,走得精神抖擻,講話興致勃勃。我不禁問道:「你陪國內的朋友來過...
»看全部
作者序
自序◎章詒和
這本書,因有「告密」、「臥底」兩文而沈重。告密者、臥底人,都是父母的朋友,甚至聯繫著兩代人的情誼。幹這行當的文人,不惜出賣朋友,出賣靈魂;但仔細想來,他們也是可憐人。「不做咬人狗,即爲盤中餐」。所以,我下筆的時候淚流不斷,而心情至今也未能平靜。
告密、臥底是一個時代政治的特殊需要,特殊行爲。無論是職業的臥底,還是兼職的告密,曾是我們這個國家非常普遍的社會行爲。這種人類的醜行,曾被大家視爲是「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馮亦代語)的光榮使命。罪惡與光榮交結糾纏,問題是嚴重性的。而更嚴重的問題...
這本書,因有「告密」、「臥底」兩文而沈重。告密者、臥底人,都是父母的朋友,甚至聯繫著兩代人的情誼。幹這行當的文人,不惜出賣朋友,出賣靈魂;但仔細想來,他們也是可憐人。「不做咬人狗,即爲盤中餐」。所以,我下筆的時候淚流不斷,而心情至今也未能平靜。
告密、臥底是一個時代政治的特殊需要,特殊行爲。無論是職業的臥底,還是兼職的告密,曾是我們這個國家非常普遍的社會行爲。這種人類的醜行,曾被大家視爲是「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馮亦代語)的光榮使命。罪惡與光榮交結糾纏,問題是嚴重性的。而更嚴重的問題...
»看全部
目錄
目錄
自序
山雨欲來
告密
-李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讀後
臥底
-馮亦代《悔餘日錄》讀後
管弦誰家奏太平
-野夫《塵世•挽歌》序
人生風景
若生在明清,就只嫁張岱--史景遷《前朝夢憶》讀後
很後悔,沒爲他寫一個字--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讀後
他那支筆是怎麽練的?--讀李長聲
像冬天飄搖的蘆葦---讀《宮女談往錄》 ...
自序
山雨欲來
告密
-李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讀後
臥底
-馮亦代《悔餘日錄》讀後
管弦誰家奏太平
-野夫《塵世•挽歌》序
人生風景
若生在明清,就只嫁張岱--史景遷《前朝夢憶》讀後
很後悔,沒爲他寫一個字--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讀後
他那支筆是怎麽練的?--讀李長聲
像冬天飄搖的蘆葦---讀《宮女談往錄》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章詒和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4-01 ISBN/ISSN:978957135356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1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