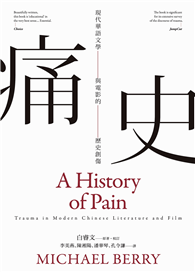暢銷書《巴別塔之犬》作者最新力作
八年前一場家庭悲劇,兒子離家出走,杳無音訊;
作家母親在離別歲月裡,改寫過往著作所有結局;
兒子卻在此時因殺人罪嫌被捕。如何能得到寬恕?
書的結局可以重來,人生的結局,不應該有遺憾。
書中書的型式實驗媲美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榜,譽為作者歷年最深情且引人共鳴的傑作
暢銷書《巴別塔之犬》作者卡洛琳.帕克斯特寫出了她至今最引人共鳴的作品--既是一樁緊張的謀殺疑雲,也是一個母親令人動容的反思,琢磨著一個母親如何能真正瞭解自己的孩子。
奧塔薇亞.佛斯特本來是個暢銷作家,目前正處於事業上的寒冬。在這本強而有力的小說開頭前幾頁,她剛抵達紐約,要把她最新完成的草稿--一本開創性的新書--交給她的編輯。不過就在穿過時報廣場時,她看到跑馬燈跑過一條新聞標題,宣告她的搖滾明星兒子,米洛.佛斯特,因涉嫌殺害女友被捕。
奧塔薇亞和米洛已經好幾年沒說話了,導致兩人疏遠的原因,是米洛小時候發生的一件悲劇。然而奧塔薇亞還是忍不住拋下一切,飛到舊金山,想要搞清楚狀況。
奧塔薇亞本來要交給編輯的書,集結了所有她寫過的小說重新改寫的最後篇章。她在其中改變了書中人物的結局,並將她藏在其中的私人經驗移除,尤其是關於多年前那恐怖的一天的部分。這些「最後篇章」以及改寫過的結局穿插在卡洛琳.帕克斯特的《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之中,像一片片散落的拼圖,拼出了米洛和奧塔薇亞共有的難堪過往。
是她逼兒子殺人的嗎?米洛真的殺了人嗎?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隨著小說情節逐步開展,揭露出令人震驚的事實,奧塔薇亞必須思考,她自己的故事該如何結局。
作者簡介
卡洛琳.帕克斯特 (Carolyn Parkhurst)
擁有美利堅大學藝術創作碩士學位,著有暢銷書《巴別塔之犬》、《伊甸園的鸚鵡》,及《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卡洛琳.帕克斯特具強烈感染力的角色描寫,以及細心鋪陳的寫作技術,一向受到普遍讚譽。她在《如果人生可以重來》這本書裡呈現了一個如俄羅斯娃娃般的故事,抽絲剝繭探討人會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去改寫自己的過去。一如《巴別塔之犬》這本初試啼聲的驚人之作,帕克斯特靈巧地探索人類心裡最幽暗的地帶,創造出一個情節精巧、後勁無窮的動人作品。
帕克斯特目前和丈夫及兩個孩子住在美國的華盛頓。
譯者簡介
鄭淑芬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修畢學分),主修國貿、英文、翻譯。具備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英譯中證書,目前專職翻譯。譯作有:《不抱怨的關係》、《真愛旅程》、《領導之道》(時報)、《忠誠檔案》、《忠誠吾愛》(八正)等三十餘本。
譯文賜教:ajanejane@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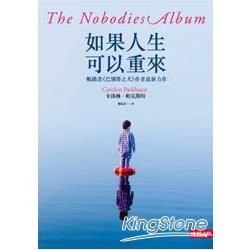
 2011/05/23
2011/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