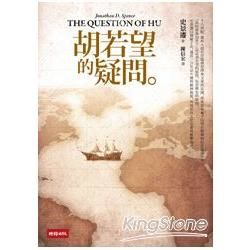序
胡若望最令人驚奇的一點,也許就在於我們竟然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中國的傳記傳統大量記載了學者與政治人物、思想家與詩人、道德高尚的人物以及言行異於常人的隱士。商人如果富有而樂善好施,武人如果英勇捍衛國土或平定內亂,也有可能見諸於史冊。然而,胡若望卻不屬於前述的任何一種人物。他出身寒微、生活貧困,也沒有地位顯赫的親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過粗淺的教育,所以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幫人抄寫文件;他與人衝突時雖然勇敢,卻缺乏謀略;他雖然信奉天主教,在教會裡卻沒有升上多高的職位;他雖然在一七二二年曾到過歐洲一次,並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的時間卻都被囚禁在瘋人院裡,針對這段經歷他也只寫了兩封簡短的信件,其中一封還遺失於寄送途中。
然而,關於胡若望這個人的詳細記載卻保存在世界三大檔案裡:羅馬的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倫敦的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以及巴黎的法國外交部檔案(Affaires Etrangeres)。這些資料之所以留存下來,主要是因為當初在一七二二年把胡若望從廣州帶到歐洲的耶穌會神父傅聖澤(Jean-Francois Foucquet)心中的愧疚使然。胡若望在一七二六年從法國返回中國之後,巴黎與羅馬便有流言指稱傅聖澤對待胡若望頗為苛刻。剛升上主教的傅聖澤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於是針對自己與胡若望的關係撰寫了一份詳盡的記述,交給他的友人與教會高階人士傳閱。他稱自己的記載為「真實敘述」(Recit Fidele)。其中一份抄本由聖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取得,他是路易十四政權時期的著名史官,也是傅聖澤的朋友。後來,這份記述連同聖西蒙的其他文件收入了法國國家檔案館。另有一份抄本在十八世紀後期流入公開市場,而在十九世紀被捐贈給大英圖書館。第三份抄本則是歸入了教宗檔案,連同傅聖澤其他未發表的著作、日記與書信本,送交時間可能是一七四一年傅聖澤去世之後。
這三份「真實敘述」的抄本各自都有頁面邊緣的筆記和作者的評注,可見得傅聖澤只要有空,仍然持續潤飾及闡明他自己的記述。比起羅馬和倫敦的抄本,法國的抄本沒有那麼多的附注,顯示這份抄本可能是最早的版本,也許是傅聖澤親手遞交給聖西蒙,因為聖西蒙的影響力可能有助於證明他的清白。大英圖書館的抄本附有一、兩封其他抄本裡所沒有的信件,抄本頁邊還有許多注記,但也有缺漏之處,並且在內文裡提及若干「事後補上」的文件,但卻未見這些文件附錄其後,可見這個版本出現的時間應是介於另兩份抄本之間。羅馬的抄本不僅有幾個簡短的注解是在巴黎與倫敦的抄本裡所沒有的,顯示這是三份抄本中時序最晚的一份,而且還附有一疊非常珍貴的信件,標示著從「A」到「N」的字母。這些都是「真實敘述」裡提及的信件。此外,羅馬的抄本還附有一七二四到一七二五年間,傅聖澤和另一名耶穌會神父戈維理(Pierre de Goville)談及胡若望的所有信件。
收藏在梵蒂岡檔案的其他資料,連同十七與十八世紀的各類中國文件,還收藏了一份目前所知僅存的胡若望親筆信件,是他以中文寫給傅聖澤的信,日期可由間接證據推算為一七二五年十月。在廣州地區的高階官員呈交給皇帝的機密奏折當中(這些奏折皆收藏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近來以影本印行),雖然沒有提及胡若望的姓名,卻詳細記載了他前往歐洲所搭乘的法國艦隊在中國的到港與離港狀況。此外,奏折中也記錄了有關樊守義(Louis Fan)的不少資訊。樊守義是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比胡若望早了十年前往歐洲,並且在胡若望動身前一年回到中國。關於胡若望在歐洲的這段歷史,還有些資料可見於巴黎警政官員與夏宏通(Charenton)精神病院先後幾位院長的早期檔案當中。這些檔案皆保存於巴黎蘇比茲宅邸(Palais Soubise)的法國國家檔案。一七六四年發行的新聞報《猶太通訊》(Lettres Juives)曾經節錄胡若望的故事,但內容頗多斷章取義之處;後來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裡,也根據這則內容不完整的報導而增寫成一篇短文。
不過,我們對胡若望的瞭解,終究還是得仰賴傅聖澤的記載。不同於現代的某些記史者,傅聖澤沒有試圖藉由抹除過往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反倒精心整理與保存了所有的短箋與信件,即便資料內容對他呈現的形象不盡正面,他也不以為意。我並不認為傅聖澤對待胡若望的方式是正確的,但我卻是因為他所保存的記錄,才得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因此,即便我認為我成功批判了他,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勝利的一方。
史景遷
布拉克島 一九八七年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