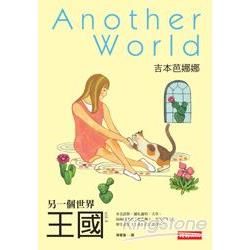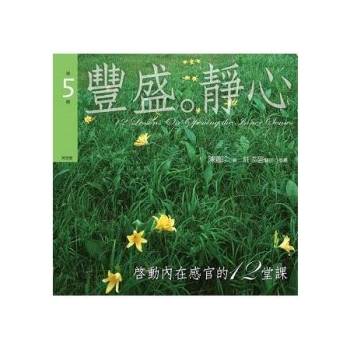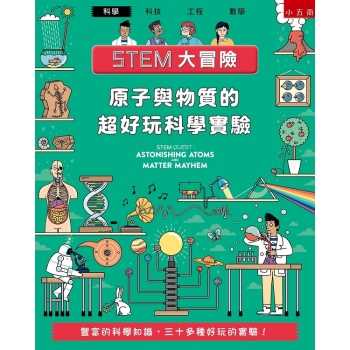米克洛斯、蘭札羅特、天草。
海風吹拂的美麗島嶼上,充滿了生命。
畢生鉅著『王國』的完美終結!
《王國vol.4另一個世界》與《王國vol.1、2、3》不同的是,主角不再是雫石,而是雫石的女兒--片岡諾利。諾利的爸爸是命理師、媽媽是藥草茶達人,而她自己則善於運用石頭的魔法,很會用石頭搭配手環,設計出別具心裁的手環。
諾利和爸爸、媽媽,和深愛爸爸的爸爸2,曾一起每年前往陽光遍地的希臘米克洛斯島長住度假。這是一個大度開闊的地方,不只為家族遊客,也不只為旅遊者。是一個能讓許多帶著不想留給子孫祕密的人,悠閒來到的美之境界的地方。但父親在諾利十歲那年過世後,其他家人怕觸景傷情,都不敢再踏上這個美麗的風車之島。
剛剛和同性戀人分手的諾利又來到米克洛斯島旅行,卻在那裡遇到了紀諾--他就是爸爸過世前預言的「貓國女王」的僕人。紀諾之前也和死去的太太到這個島上來度過蜜月,所以每年都來此回味。諾利和紀諾的相遇是命運的邂逅,於是,另一個故事開始了。
作者簡介:
吉本芭娜娜
1964 年生,東京人,日本大學藝術學文藝科畢業。本名吉本真秀子,1987 年以《我愛廚房》一文獲第六屆「海燕」新人文學賞,陸續又獲「泉鏡花」、「山本周五郎」等大獎。1989 年崛起後,迅即成為日本當代暢銷作家,著有《廚房》、《泡沬/聖域》、《甘露》、《哀愁的預感》、《蜥蜴》、《白河夜船》、《蜜月旅行》、《無情/厄運》、《身體都知道》、《N‧P》、《不倫與南美》、《柬鳥》、《王國vol.1 仙女座高台》、《虹》、《羽衣》、《阿根廷婆婆》、《盡頭的回憶》、《王國vol.2悲痛、失去事物的影子,以及魔法》、《王國vol.3 祕密的花園》、《原來如此的對話》(和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對談)等。
譯者簡介:
陳寶蓮
輔仁大學日文系畢業、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曾任東吳大學日文系及輔仁大學日文系夜間部講師、《中國時報》編譯。譯作有《身體都知道》、《不倫與南美》、《王國vol.1 仙女座高台》、《虹》、《阿根廷婆婆》、《王國vol.2 悲痛、失去事物的影子,以及魔法》、《王國vol.3 祕密的花園》、《嫉妒的香氣》、《當下的戀人》等。
章節試閱
我叫片岡諾利,雖然奇怪,但真的是我本名。
媽媽生我的時候,正是她和外曾祖母住在沖繩、專心栽植諾利果的時期。媽媽是那種一旦投入一件事情、便完全不想其他事情的類型,因此,毫不猶豫地給我起名諾利。
媽媽說,諾利果是一種非常好、葉子可以泡茶、果實可製萬能藥的溫和強悍植物,雖然味道有點怪。希望你能像它那樣長大,即使醜一點也沒關係。
我說最後那句話多餘時,媽媽總是從不同的角度回答我,「妳看過嗎?那個果實的奇怪模樣。像是雪白鬆軟的麵包,坑坑疤疤長滿眼球似的種子。」我說「沒聽過」,媽媽沒聽見,繼續說,「我那時初遇諾利果,戀愛似的著迷,想不到別的名字,只覺得這世上我最喜歡的東西就是諾利果。」
幸好,我的外表沒有那麼糟糕,但是媽媽的願望很快就應驗在我身上。我知道媽媽是當真的。當我後來領悟媽媽是不希望我遺傳爸爸的虛弱體質,希望我能強壯長大,外表如何都無所謂時,也慶幸有這個奇怪的名字了。
「我們的名字好像接龍造句。」紀諾說。
彼此做甚麼工作?為甚麼從日本來到這裡?都還不敢談。孤獨的旅人在開放同時也小心翼翼。
彼此的眼睛都在說,因為喜歡這個島,所以一個人來旅遊,現在只要知道這些就夠了。彼此的聲音裡都藏著「現在不要多談」的願望。
坐在比較靠近店面的地方,看著前方面對大海、襯著平靜海面、高高低低的各國各色人頭背影。夕陽還在海平面上方,光漸漸變紅,人們的臉頰都紅通通一片。大家穿著悠閒舒適的薄衣,喝著飲料,聊天說笑,相依相偎。男男女女和家族遊客,都在等待夕陽沉入大海。
「想不到今天不是獨自度過這像節慶般的時間。雖然一個人度過也很幸福。我本來想直接下坡,在停車場那邊看夕陽的。」我說。
「啊,那個有風車的地方。」
紀諾說。我盯著他淺笑時鼻子擠出皺紋的模樣。
不是喜歡,也不是討厭,只覺得這個人是我認識的人。
從小,在我心底深處,就有一個獨自蹲下的地方。我想,他也是擁有那個地方的人。
雖然每個人都有那樣的地方,但在那個地方特別用力的人,可以從言談和態度輕易知道。
「你來這島很多次了?」我問。
「嗯,我喜歡這裡,我喜歡這島上的每一天。」紀諾說,
「死去的太太只和我來過一次,是度蜜月。有關她的回憶,像糖果般到處都有,我每年都來此回味。談這種事情,有點不好意思哩。」
那和我幾乎相同的動機,又讓我一驚。
這世上怎麼有這麼相同的人呢?
「我有一段時期也是每年和家人來,所以,即使一個人也敢來。我們家其他的人說,爸爸死了以後,因為太傷心,不敢來。可是我不同,偶而會來這島,為了珍重取出一件件有關爸爸的回憶、或哭或笑而來,我一定是個幸福的孩子。」
「我剛才在石階上看見妳的後腦勺,就知道妳是個幸福的孩子。」
紀諾說。我沒要他解釋。
只看到後腦勺,就知道妳是個幸福的孩子。我像品嚐甘甜清香的水果,細細玩味那句話的意義。
夕陽漸漸變大,我們沉默,凝視著它。
海浪聲音澎湃洶湧。像對微醺的腦袋施展魔法般,陣陣重複。
透明的光包圍整個世界。夕陽將它的美,均等分享這裡的每一個人。雲的顏色時時刻刻變化,似乎預約了一個即將來臨的美好夜晚。每個人臉上都現出感謝的神情。對他們來說,今天是怎樣的一天?我不知道。但是,應該可以就此重新開始吧,看到這美麗的景色,感受到那不管今天或明天、寂寞與否、聰明與否、曝露度多寡、所有的人都陶醉其中的不可思議時間。
即使心情狂亂的人、吵架中的情侶,只要身在這裡,也會先看夕陽吧。這樣,就有一點甚麼改變了。瞇著眼睛凝視美麗的橙紅色彩時,獸性的本能會從內心主動做一次全部轉換。每個人都領會那美麗的雲彩光輝是上天贈送的禮物。
夕陽倏地消失在水平線上面一點的雲中瞬間,眾人嘆息,回到原來的世界。看看杯子,再點一杯飲料,絮絮交談。
在這裡看夕陽的回憶,像島上繁複交織如迷宮的道路那樣濃密,在我腦中展開。
每一條小巷,每一家商店,每一棵樹下,我和家人都曾經走過。
感覺到如今近乎解散的我們家人當時緊緊黏在一起的甜膩悶熱肌膚味道。一起擁有那種慵懶至極的感覺,以同樣節奏度過一天高低潮的情景,悠悠甦醒過來。
那段時期把大家緊緊黏在一起的,是年幼的我?年老的外曾祖母?還是身體不自由的爸爸?我不知道。或許恰好是一段家人不能不緊密相助的時期。
對小孩子來說,那種記憶是決定今生幸福與愛好基礎的一輩子束縛同時,也是隨時能取出的幸福百寶箱。
「跟你走在一起,感覺得出你曾經和腳或眼睛不方便的人住過很長的時間。」紀諾說,
「行走的速度,不過分呵護,配合我和馬路、建築物、人潮的位置狀況,自然變換自己位置的樣子。」
「你過度解釋了。我只是習慣而已。我爸爸眼睛幾乎看不見,長了腦瘤,壓迫到神經,晚年時幾乎不能走路,我從小就常幫他推輪椅。」我說,
「那個經驗這時候能派上用場,真好。而且,和你走在一起時,鮮明地想起我爸,莫名感到高興。我來這裡,就是為了回憶那些點點滴滴。」
是啊,我都忘了。爸爸的速度就是這種速度,慢慢地走,彷彿世界是如許值得細細品味。我再度咀嚼那份味道,做個深呼吸。每一件事都緩慢舒暢,不必去想以後的事和要去的店家。清風吹拂,隨時看到貓以異乎人潮流動的速度橫過眼前。
清香甜美的空氣像蜜一樣濃稠包圍著我。
「你父親甚麼時候走的?」
「幾歲啊?四十出頭吧。」我說,
「現在這個是法律上的父親,我跟他的姓,叫他爸爸2,大概六十歲。」
「聽你的口氣,好像當時就有兩個父親。」
「我是真的有兩個爸爸啊。」
我說,擠過擺滿繽紛色彩T恤的店前。
「我叫已經過世的親生父親爸爸,叫另外那個爸爸2。爸爸死了以後,還是這樣叫。
我出生時有很多事情,媽媽和兩個男人住在一起。直到我很大以後,才知道哪一個是我真正的爸爸。不過,我們是很幸福的家庭。以後有機會再告訴你。你呢,腿不好,眼睛看得見嗎?」
「看得見。只是因為陽光刺眼,戴上太陽眼鏡。腿是小時候車禍的後遺症,不拄手杖不好走。
就因為腿不好,認定自己出不了遠門,於是拼命畫畫,不知不覺畫得很好,能靠這個生活。」
是嗎?他是畫家。我終於明白,他那纖細、帶點女性的感覺,還有鞋子、提袋上沾著一點顏料的原因。
「有需要我幫忙的,儘管說。這島上很多坡路。」
我說,對他不是慢性重病,鬆一口氣。
「不,我不想妨礙你的旅行,不用管我。」
「我沒有急著要去哪裡。」我微笑說。
我十歲時,曾和爸爸單獨在米克洛斯島共處兩個星期。
那段回憶在我的生命中是何等重要?如果沒有那些日子,長大以後的我會是如何不同?想起來就有點害怕。
我到現在才明白,我們父女最初也是最後共度的那段時間,是爸爸只關注我、有意將其存在的一切確實傳達給我、為我耗盡了一切的時間。
我還小,不能好好照顧爸爸,但他不曾生氣,沒有抱怨,只是拼命包容我。
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究竟是老天的安排,讓我不會對荒誕的父母失望而走到今天這個方向?還是只因為媽媽和爸爸2想一起去米蘭玩?或是爸爸已知來日無多,想製造只屬於父女倆的回憶?所以才有了那段時間。
我的父母不是可以好好談論這種事情的人。他們各有個性,基本上都是隨心所欲、不勉強自己、很像小孩的人。
我只知道一件事。
爸爸2和媽媽都希望能多一天、甚至多一秒的時間陪伴爸爸。他們都打從心底、幾乎像宗教似的認為,爸爸不在以後,他們的人生,根本不存在。
他們大概時時在想,如果可能,就讓時間停止吧。媽媽停下幫爸爸處理事務和做家事的手,爸爸2放下他的工作,只想凝視爸爸。
可是,如果露骨表現出來,會給爸爸體貼別人的心帶來負擔,所以,他們還是努力照常過日子。
那種無奈的悲傷,總是強烈傳達給我。
媽媽和爸爸2想到太陽穴抽痛的程度,拼命告訴他們自己:看,這人今天還活著,明天也還活著吧,就不要多想了。我雖然年幼,也能理解那份緊張感。
與此相反,爸爸只是心存感謝,靜靜做好心理準備,面對可以脫離這副累贅肉軀的時刻接近。他低調而確信,雖然對大家抱歉,但該是時候了。
那份心情當然也傳到媽媽和爸爸2身上。
他們要保持開朗的心情,備感辛苦,大概都難以負荷那樣的心情,所以要同時離開一下,暫時忘掉一切吧。
我叫片岡諾利,雖然奇怪,但真的是我本名。
媽媽生我的時候,正是她和外曾祖母住在沖繩、專心栽植諾利果的時期。媽媽是那種一旦投入一件事情、便完全不想其他事情的類型,因此,毫不猶豫地給我起名諾利。
媽媽說,諾利果是一種非常好、葉子可以泡茶、果實可製萬能藥的溫和強悍植物,雖然味道有點怪。希望你能像它那樣長大,即使醜一點也沒關係。
我說最後那句話多餘時,媽媽總是從不同的角度回答我,「妳看過嗎?那個果實的奇怪模樣。像是雪白鬆軟的麵包,坑坑疤疤長滿眼球似的種子。」我說「沒聽過」,媽媽沒聽見,繼續說,「我那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