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逝水年華》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承襲第一卷優雅精鍊的文字風格,敘述主人翁年少時期的人生回憶。在第二卷的第一部中,敘事者在貢布雷遇見了美麗大方的吉爾貝特,兩人若有似無的情感,讓情竇初開的他苦嚐思念的滋味。
昔日同窗好友布洛克說:「女人最想做的事,其實就是做愛。」布洛克所謂的「獲得幸福的全新的可能性」把敘事者對周圍世界的看法給攪亂了。兩人甚至還一起去了一家打炮屋,認識了一個名喚拉謝爾的妓女。雖然那裡的妞兒姿色平庸且水準太低,但他仍然很感謝布洛克,讓他得知幸福,以及對美的占有和享受。
只是好景不常,吉爾貝特此時卻跟敘事者漸行漸遠。對於因為分離而引起的焦慮,只能一味地咬牙忍耐著,企圖有朝一日能擺脫那樣的感情,讓兩人曾經漾起的愛情漣漪,成為自己日後充滿溫情的回憶。
在此同時,敘事者仍然持續前往斯萬家,透過斯萬夫人的人際關係見識了許多不同以往的生活經驗,儘管父母對此感到苦悶且不支持。此外,還結識了自己最心怡的作家貝戈特,雖然他稱讚敘事者是個聰明的孩子,但不得不承認,貝戈特的形象和為人都與敘事者心目中的樣貌南轅北轍,就在這一刻,他心目中的那些貝戈特的作品都一起往下墜,只淪落為某個留著山羊鬍子的男人平庸的消遣。
作者簡介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7-1922.11)
出生在巴黎一個藝術氣氛濃郁的家庭,但從小就因哮喘病而被「逐出了童年時代的伊甸園」。他的氣質內向而敏感,對母親的依戀,對文學的傾心,為以後的創作埋下了種子。他青年時代經常出入上流社會沙龍,在熟悉日後作品中人物的同時,看穿了這個社會的虛幻。父母相繼去世後,他痛感「幸福的歲月是逝去的歲月」,開始寫作《追憶逝水年華》。在生命的最後十四年中寫成的這部巨著,猶如枝葉常青的參天大樹,屹立於文學之林的最高處。他借助於不由自主的回憶(無意識聯想),將逝去歲月的點點滴滴重現在讀者眼前,使時間在藝術中得以永存。
譯者簡介
周克希
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曾從事黎曼幾何研究與教學。 1984年起翻譯文學作品,先後譯有《三劍客》、《王家大道》、《追憶逝水年華(節本)》、《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小說,與人合譯作品有《基督山伯爵》、《追憶似水年華(第5卷)》等。在時報出版的譯作為:《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第一部貢布雷》、《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第二部斯萬的愛情 / 第三部地方與地名:地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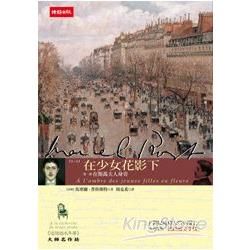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