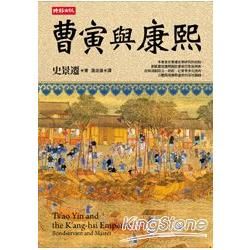史景遷史學研究起始之作,開啟西方漢學新面向。
細膩書寫康熙寵臣曹寅的家族興衰,
反映清朝政治、財經、社會等多元面向,
立體再現康熙盛世的浮世織錦。
* * *
曹寅作為康熙皇帝的家奴,以歸順旗人的漢人身分,遊走滿漢二元社會,署理攸關稅收的兩淮鹽政與御用供給的江寧織造,聲勢日隆,其一生仕途和家族起落與康熙密切相關。史景遷企圖透過曹寅來反映康熙的統治手腕與清初政經社會面貌,也重構曹雪芹筆下《紅樓夢》背後的曹家真實景況。
本書為史景遷師從明清史學家房兆楹所做的博士論文,擺脫以往西方學者著重在西方因素影響東方歷史的研究觀點,重新觀察明末清初中國社會的滿漢關係與社會變革。本論文榮獲珀特爾論文獎(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不僅是史景遷一生學術著作的起點,也為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提供新面向。
作者簡介: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甫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簡介: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前朝夢憶》、《孫逸仙》、《只爭朝夕》等。
章節試閱
第四章 南巡(節錄)
曹寅與南巡
負責料理南巡諸般事宜可不是一件輕鬆的差事,而這就是曹寅於後四次南巡期間在江寧所必須執行的任務。他之前在江寧就見過皇帝了,因為他的父親曹璽自康熙二年起即署理織造,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死在任上。如前所敍,皇帝在十二月抵達江寧,親臨撫慰喪家,特遣內大臣以尚尊祭奠,並欽賜喪家御書。曹寅身為曹家長子,主持治喪事宜,應該接待過康熙。
十五年後,康熙三度南巡,由曹寅接駕。曹寅視事江寧織造,織造衙門和宅邸被移作行宮。皇帝第一次駐蹕織造衙門是在康熙二十八年,當時是桑格擔任江寧織造,往後四次南巡,均以此為行宮。康熙三十八年,皇帝駐蹕江寧一週,就是在這次巡行時,康熙召見曹寅寡母,親切話家常,並御書「萱瑞堂」三字送給她。時人視之為浩蕩天恩;年邁老母常奉召覲見,並得到皇帝稱許,甚至御賜綢緞;而老母得到皇帝欽賜御書,更是無上恩寵。皇太后亦與曹母交談,更增殊榮。
康熙在這趟巡行交待曹寅一件特別的差事。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十四日諭旨提到皇帝親祭洪武陵寢時發現牆垣多傾圮,命江蘇巡撫宋犖與曹寅會同修繕。康熙還御書「治隆唐宋」四字,命曹寅製匾勒石。曹寅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摺子裡奏報,他與代理總督陶岱、宋犖及地方大小官員踏勘,並預估所需工料,委派江防同知丁易監工,共同議定動支「官吏俸工」銀兩進行修繕。不過,因為這年夏天多雨水,要等到秋涼時節才動工興修。俟修繕完竣後,即將御書製匾勒石。曹寅分工委派相關官員,動用公共銀兩支付,整個任務籌劃得十分俐落。
南巡結束後,曹寅又上了兩道奏摺,一則恭謝天恩,軫恤百姓,一則代表母親感謝皇恩,寫道:「臣寅母子焚頂捐麋,難以上報。」康熙針對這兩道奏摺並無特別指示,不過在康熙四十二年四度南巡之前,皇帝下了一道指示:
朕九月二十五日自陸路看河工去;爾等三處千不可如前歲伺候。若有違旨者,必從重治罪。
由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的那趟巡行,曹寅的接駕安排奢華鋪張,康熙並不認同,而在密摺裡表達此一意見,很可能是真心反對。康熙三十八年的南巡確實很奢華──「視甲子(指康熙二十三年那次的南巡)已逾十倍矣。」
不過,康熙四十四年這趟南巡時,曹寅已是位居要職,又接任兩淮鹽巡鹽御史,而康熙顯然已經精於品味,也樂於接受曹寅的奢華款待。這趟南巡可以特別仔細研究,因為一位無名氏──顯然是扈從之一,或是深知內情的人士──留下一份關於這趟南巡的記錄。如果再輔以大學士張英的回憶,我們便能相當詳細地勾勒出康熙四十四年曹寅的行跡。張英曾於康熙二十八年隨同南巡,並留下他沿途吃足苦頭的有趣描述。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三日,皇帝離開京城,三月二十五日抵達魯南大運河畔的魚台縣。江南文武百官在此恭迎皇帝大駕。諸臣之中有自江寧兼程趕了兩百五十哩路來接駕的曹寅。顯然康熙的每一次南巡,曹寅與江南的文武百官都得這樣千里跋涉,而且一定也所費不貲;而且,他們還得比皇帝早到──他們在魚台縣已經等了十天,皇帝才終於現身。百官接了駕之後,便隨皇帝南行,原本就已可觀的扈從隊伍更形龐大,造成相當的混亂。這就是張英在南巡時晚上就寢時所碰到的問題:
余先一日曾遣輜重、僮僕、帳幕至宿處相候。此時昏黑中見家人來迎,深幸有即次之安。俾其指視,而彼已恍惚不能記憶原處。蓋于幕一色,空曠之地頃刻又增營幕,最難記識。
又軍中例不許高聲呼喚,至夜尤嚴,故但低聲問之。有頃,一僕遠聞,疾趨而前。蓋已越數十幕;倉卒來迎,一旋轉間,而彼又茫然矣。饑疲已極,求息肩不可得。又越數刻始得達帳房,已漏下三鼓矣。
這件事發生在啟程之後未久,而張英先前也沒有露宿野外的經驗。曹寅可能不曾有過這麼狼狽的時候,但許多巡行的規矩一定令他十分厭煩。所有參與南巡的人都必須自備輜車,自行載運帳幕、寢具、炊具,但在皇帝整裝啟程之前,所有輜車不得離開營地。結果到了入夜,輜車都還無法抵達,而隨扈只能呆坐枯等,愈坐愈餓。就算輜車到了,也還有麻煩;十里之內的井水、泉水都留給康熙和隨扈,其他的人只好老遠去找水餵馬炊飯。他們還得等康熙就寢之後才能休息,而在黎明前收拾好帳幕、用具,在行宮之前靜候。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底,曹寅與皇帝緩緩南行,狂風驟雨令之無法渡黃河,也困住了他們與隨扈,皇帝還得從自己的儲備中拿出額外的糧食。三月三十日,皇帝抵達江南,當地紳衿與駐地官兵恭迎聖駕;他們應該也跟在陣仗之後。四月一日,隨扈渡過黃河。寥寥數語卻是蘊含複雜;以下是張英陳述他在康熙二十八年渡黃河的情景,曹寅肯定也碰到類似的難題:
自宿遷五鼓啟行,岸上行四、五十里,聞上已登舟。予靠四、五人亦登舟,然舟行稍遲,又五、六十里聞上已登岸。予輩四、五人又登岸,行至清河已將日落。蓋是日行二百餘里。余僮僕八人皆又不及至,隨一僕,牽一馬。予令其前,尾之而行,先是乎與京江、厚庵、運青同行,予墜馬、濕衣。而諸君已疾馳,予力追之不能及。
至清河,聞上已渡河,且令侍從臣皆於今日渡。予攜一僕三馬,至河邊,已昏黑。已無可如何,有禮部筆帖式在此相候。予遂偕之渡河,留三馬一僕於泥沙間以待後人。
張英的麻煩還未結束。這個筆帖式派人另外找船,而僕人竟然迷路了,於是筆帖式就去找他,結果自己也迷路了。最後,張英獨自一人拖著沉重的步伐在黑夜裡尋找皇帝的蹤跡。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底、四月初,曹寅一定是跟著康熙;因為他在常規的官僚體系裡並無一定品秩,又不在自己的轄區,他在扈從行列中的地位很可能並不重要。四月二日,漕運總督桑格奏請康熙進入淮安城,先遣侍衞在前開道,太監抬的三十多頂轎子緊隨在後,後宮女眷坐於其內,而曹寅不太可能在這陣仗之中扮演角色。然而過了兩天之後,曹寅開始與大吏重臣並列,因為此時康熙已進入揚州巡鹽御史和江寧織造的轄區範圍了。
四月四日晚上,皇帝在揚州附近登岸,接駕的不僅有官吏,還有揚州城的鹽商,進獻古董、古玩、書冊、字畫,皇帝納之。翌日,曹寅以巡鹽御史的身分,祈請皇帝移駕至鹽商特別在一處園林裡所安排的行宮。皇帝欣然同意,偕太子、皇十三子、宮女一同前往。戲碼、宴飲已準備就緒,皇帝一行人在此地稍作休息。這般排場自然手筆不小,皇帝估計應要花上數千兩白銀,這筆花銷是由鹽商支應,曹寅並未出一文錢。
四月七日,曹寅聯同兩位大臣設御宴百桌,這是曹寅頭一筆大的花銷。說來奇怪,設宴的這三位大臣本身剛好代表三大統治集團──八旗精英、漢官精英和皇家精英──韃靼將軍馬三奇、中堂大人張玉書和曹寅。這三位大臣也進獻禮物,皇帝收下馬三奇的一套萬古書、兩只西洋瓷杯、一籃鯉魚,曹寅的一只玉杯、一架白玉鸚鵡,張玉書的幾本書。南巡的慣例是官員進獻各色禮物,皇帝挑選幾樣,其餘歸還。但鹽商的待遇又有所不同。在曹寅等人進獻禮物之後,揚州鹽商又進獻皇帝六十件古董,太子四十件古董,皇帝、太子全部欣然接納。鹽商自然沒收到任何回禮;曹寅和官員獲賜御製詩詞(大概是皇帝親書的)等小禮物。
四月十日,康熙至蘇州;城外幾哩處已設好戲台,皇帝在八駕馬車簇擁下騎馬進城,隨從有女眷坐的轎子,城內家家戶戶門前設案焚香,撐起五顏六色的篷幕,沿街懸掛五彩繽紛的燈籠來迎駕。皇帝的行宮設在李煦的織造衙門,正是李煦聯同江蘇巡撫宋犖祈請皇帝進城的。江南、山東、福建的官吏前來見駕之後,普陀山的一個和尚繼之奉召覲見,李煦設宴、安排幾齣知名的戲。
翌日,陰曆三月十八日(陽曆四月十一日)皇帝壽誕,氣氛更為歡慶。鄰近各省文武官員、告老還鄉的大臣、鄉紳、學士、和尚前來向皇帝賀壽,進獻禮物。皇帝以內務府供用周備為由,婉拒了許多禮物,並賜宴省級大員,欽賜禮物,總值不超過一千兩銀子的扇子、竹器、絲綢、糕餅。曹寅獲得欽賜對聯:「萬重春樹合,十二碧雲峯」。這頓飯應該是李煦出的錢,但他卻什麼也沒收到。
這時駐蹕蘇州的康熙,交待李煦和曹寅辦一樁差事。李煦奉命募資以供應原總兵嚴弘的二子讀書,這時的嚴弘既貧且病,無力負擔。嚴弘二子長大後可報部擢用。曹寅則奉命編修刊刻唐詩。曹寅後來提到他是在四月十二日奉旨編修刊刻唐朝詩集的,但是正史關於這一天的記載,甚至詳細描述這趟巡行的日記,都沒提到這道諭旨。可能皇帝起初是私下交辦的,因為這畢竟不是包衣和織造的職掌範圍。皇帝要確定此舉能成功,才會昭告天下。
康熙自蘇州起駕前往松江府,從四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二日駐蹕該地。曹寅再度隨侍皇帝,皇帝命曹寅等人核實御賜張雲翼的禮物。張雲翼是松江府提督,在康熙駐蹕松江府時,以宴筵、戲劇、騎射操演的鋪張排場博得皇帝歡心,但又能維持睿智、正直的聲名。曹寅與兩位僚臣奏報禮物清單,而清單上的袍子、帽子等衣物都是皇帝穿戴過的,這表明皇帝十分賞識張雲翼的接駕(幾天前,皇帝才將坐騎賜予張雲翼,張雲翼是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蒙受御賜最隆的官員)。要曹寅等人將禮物編目清楚,一來避免禮物給錯人,二來也昭告世人皇恩隆重。
四月二十三日,康熙離開松江府前往杭州,在此停留七天;五月二日離開杭州,又在蘇州駐蹕一週。這段期間並未提及曹寅,他可能在清點完御賜張雲翼的禮物後,先回江寧去打點皇帝回鑾江寧的事宜。
五月十四日,皇帝回鑾至江寧,曹寅主持接駕。午時,皇帝通過西華門,諭令侍衞不得驅離百姓,任之圍觀南巡行列,然後進駐織造衙門。當地文官武將都到織造衙門來迎駕,儀典一結束,曹寅隨即設宴。宴後,駐地官兵進獻禮物,然後又赴總督阿山籌備的另一場宴席。第二回宮筵結束後,各官晚朝覲見皇帝。
曹寅似乎很懂得送禮討皇帝歡心的門道,他又進獻櫻桃。皇帝龍心大悅,說要送至京城進過皇太后後他才用。於是便挑了差官帶著櫻桃騎馬進京,居然短短不到兩天,櫻桃就送到了(櫻桃應該是由官差騎馬,接續在沿途驛站換馬傳送,到京城總計兩千三百里路,平均時速十六哩,這是當時傳遞文書急件所規定速度的兩倍)。這裡,皇帝的炫耀作態迎合了滿人快馬疾馳的喜悅,以及漢人對彰顯孝道的崇敬。那晚稍後,曹寅再次進宴搬戲。
紅樓夢中的南巡
關於曹寅公開參與南巡事務,正史和野史都沒有更多的記載。若是曹雪芹沒有寫下《紅樓夢》,是無從了解南巡對個人造成何等的影響。《紅樓夢》第十八回寫的是元春回賈府省親。這一回細膩舖陳省親的細節;賈府裡大手筆籌備元春省親,元春隨扈的陣仗,形同將皇家巡行寫入小說。
賈府的輝煌精準反映出曹寅為康熙安排一場又一場的宴筵與演戲。雖然曹雪芹從未清楚交代賈家如何積累家產,這份空白或許可以從曹寅身為康熙家臣經營絲、銅、米來填補。曹家雖然沒有出皇妃,但曹寅的兩個女兒都嫁給郡王,皇帝還親自過問這兩門婚事,命正白旗包衣佐領主持曹家長女的婚事,並賜御宴。所以,賈家的社會地位和財產都在提升,並為皇帝所垂顧。
曹雪芹必定聽過家人說起這些事情,而把昔日的輝煌寫入小說裡。曹雪芹當然也會用自己在家裡親歷的事情作為小說題材,極有可能他那嫁給鑲紅旗郡王納爾蘇並產下子嗣的姑母,回曹家省親時給年幼的曹雪芹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有時,曹雪芹的描述也會如實反映往事,顯示除了家族相傳和個人親身經歷之外,也可採擷史料。比方說,曹寅在第五次南巡前上了一道奏摺,「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內河船隻,預備年內竣工(在康熙抵達之前)」;曹雪芹在《紅樓夢》某一回裡如此描述南巡:「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如果我們把底下的描述看成史實、家族傳說以及後來個人經驗的混合,並經過小說家可能會用到的手法,加以誇大渲染或是輕描淡寫,或可從中窺見南巡對曹家的影響。為求慎重起見,此處討論的省親主要是用曹雪芹筆下的元春回賈府省親的情節,而不是史家所載的康熙駐蹕曹家。
當賈府確定元春省親的消息後,便挑了相鄰的兩府邸之花園,方圓約三里半大的地方,命人彩繪圖樣,以修葺作為省親別院。同時還派人聘歌女、教席,置辦樂器、道具;這就花了賈府三萬兩銀子,另外花二萬兩銀子置辦花燈、花燭及各色簾帳(曹雪芹暗指派去置辦的人在中間吞了不少銀兩)。
此後,工匠、石匠絡繹出入賈府,將金、銀、木料、磚瓦等所需建材搬進賈府。原有的牆垣、樓閣,以及下人住所盡行拆除以為施工開道;所幸此處已有河道,不需再引新水道。諸如竹樹、山石、亭榭欄杵等物,可以自園中他處挪用;善用手上已有的材料,改建也可不必花大錢。牆垣亭閣俱用水磨磚砌成,白石台階鑿成西番蓮花模樣。房屋內部布置華麗,四周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山水,或翎毛花卉,雕檈五彩,銷金嵌玉。小說中借眾人之口,一語點出為何這般炫耀景象的理由:「雖然貴妃崇節尚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
工事持續了夏、秋兩季。到了十月,一切準備就緒:挑選十二名歌女,在教席教導下已學了二十幾部戲,十二名妙齡道姑、尼姑也學會誦經唸佛。這些事花了三萬兩銀子;另外又花了二萬兩銀子採辦織品:妝蠎酒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金絲藤紅漆竹簾、盤花簾七百掛、椅搭、桌圍、床裙、機套七千件。古董文物俱備,匾額對聯懸掛,鸚鵡鳥獸等點綴眼目,口福之物亦買全。布置妥備後,賈政上呈題本,奏報色色斟酌妥當。賈政接獲諭旨,元春將於正月十五日省親。
元春歸寧前一週,宮內太監前來檢視各種安排,一一查看元春更衣、休息、用膳和接受家人問安的房間。另有太監巡查各處,以確保防備無虞,並隔離所有禁區。還有太監詳細向賈家人講解必須遵守的禮節。府外有工部官員與當地警衛,察看街道是否潔淨,是否有閒雜人等。
元宵當日五更,歷經一夜無眠,賈府家人依品位穿戴整齊在門外靜候,經過幾次誤報後,十來個太監飛報貴妃駕到。隨後不久,先後有十來對太監騎馬緩緩前進,繼之是元春的隨駕,一對對龍旌鳳扇,後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後是七鳳黃金傘迎面而來,又有執掌太監手捧香珠、綉帕、漱盂、拂塵等物。最後是元春本人,坐著一頂由八名太監抬著的金頂金黃綉鳳版輿。
元春更衣後,又上輿進園玩賞。此刻已是黃昏,成千五彩燈籠閃耀。值此季節光禿的樹枝,黏上各色綢綾紙絹和通草為花;原本空無一物的池塘,有荷荇鳧鷺諸燈,皆以螺蚌羽毛做成。正式接見過後,元春與家人話家常,並開筵席,之後是家人的詩文競比;宴後上演四齣戲,彼此交換厚禮。
《紅樓夢》裡關於賈妃省親最重要的部分,大概是對安排接駕事宜的描述。但仔細推敲其中細節,卻會得到顯然不太可能的結論:對曹寅而言,接待南巡所費不貲,但幾乎可以肯定,這並不像某些作者所講的那般可怕。《紅樓夢》中提到特別花銷用了五萬兩銀子;這個數目對讀者來說雖然是筆巨款,但檢視賈寅家產的結果顯示,這個數目完全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曹雪芹也指出,只要稍稍整頓家產就可以勻出款項,而所需的人力則從家中僕役調遣。再者,營建省親別院的花銷,只需一次支出;建成之後,只消隔一段時間修繕即可。既然皇帝在康熙二十八年曹寅視事織造前駐蹕江寧織造衙門,而營建的費用可能已由曹寅的前任桑格支出了。無論如何,南巡的花用是由公費支借,儘管皇帝反對這樣的做法。至於古玩、奢侈之用的開銷,正如小說中的人物所說的,「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最後,曹雪芹還提到,元春回宮後,奏聞皇帝家人如何盡心接待她。皇帝龍心大悅,諭令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賜賈家。這些賞賜形同現銀。康熙可能也是以如此的方式獎賞曹寅;這類獎賞不見得為人所知,也和南巡記載中的馬匹、詩句、扇子和筆墨等御賜頗為不同。
第四章 南巡(節錄)
曹寅與南巡
負責料理南巡諸般事宜可不是一件輕鬆的差事,而這就是曹寅於後四次南巡期間在江寧所必須執行的任務。他之前在江寧就見過皇帝了,因為他的父親曹璽自康熙二年起即署理織造,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死在任上。如前所敍,皇帝在十二月抵達江寧,親臨撫慰喪家,特遣內大臣以尚尊祭奠,並欽賜喪家御書。曹寅身為曹家長子,主持治喪事宜,應該接待過康熙。
十五年後,康熙三度南巡,由曹寅接駕。曹寅視事江寧織造,織造衙門和宅邸被移作行宮。皇帝第一次駐蹕織造衙門是在康熙二十八年,當時是桑格擔任江寧織造,...
作者序
初版前言
本書描述清史曹寅(一六五八至一七一二年)的生平,但這並不是一本傳記。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的時代構連,並給予制度同等的重視。所以,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裡,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中國正史裡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織造、巡鹽御史時,這意味著什麼。曹寅的所做所為自然要予以關注;但他可能做什麼同樣重要,或者,更精準地說,律例規定他應該做什麼,與曹寅同時代的人處在相同的官位時又會做什麼。
本書涵括的範圍超過曹寅的一生。本書勾勒的情節始於曹寅祖父所處滿人鞏固天下時期,迄至乾隆朝曹寅孫子的時代。想當然爾,有鑑於曹寅是滿人統治者的包衣奴僕,他們的故事勢必鮮明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與表現方式的變易,本研究的歷史背景正是清朝本身。儘管所觸及的範圍,不能期望可以盡訴滿人統治頭一百年的種種變遷和活力,但至少可以呈現它繽紛的樣貌。
曹寅的曾祖父在努爾哈赤(一五五九年至一六二六年)時遭俘擄,被納編進這位剽悍、足智多謀統治者新設立的組織之一包衣佐領,努爾哈赤先求鞏固自己的實力,然後在一六一六年稱帝,號天命,國號金,以與明朝競逐天命歸屬。曹寅祖父的事業始於皇太極(一五九二至一六四三年)時代,他自命清朝崇德皇帝(一六三六年),當時滿人還盤據在明人抗守的長城以北,學習、實行漢人的官僚制度。不過,一六四四年滿人定鼎中原,運用許多滿人自己的統治策略。這點可以從曹寅父親的生涯窺知,他在順治皇帝(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一年)的內務府裡當差,於康熙朝輔政大臣攝政期間外放江寧織造,這是一個對滿人統治者有特殊用途的職位。曹寅的一生,從幼時到辭世,都是在康熙朝(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中度過,突顯了康熙時代摸索中的治理手段。不管是曹寅還是康熙,都不會凡事視之理所當然,他們兩人總是密切關注經濟和政治局勢;他們稱不上對其所見皆有建設性的回應,但他們樂於通權達變,他們彈性因應自然改變了中國官僚傳統的模式。譬如,康熙利用南巡之便親自查訪各省民情,發展出密摺制度以祕密奏報來輔助他對局勢的掌握。他拔擢曹寅署理江寧織造,但並未將其職責限縮在律例所規定管理江寧城內的皇家織場上。曹寅必須平糴米價、購買銅斤、督導漕運、創辦文化事業、押運佛像給寺院,奏報高官行止和收成情況。曹寅還出任兩淮巡鹽御史,徵集每年兩百萬兩的例行稅銀,還得另行籌措五十萬兩以供皇上的各種度支。
康熙一朝並非承平安康的時代,它不像清代爾後各朝因循舊制、抗拒變革。十七世紀末這個時代,前明遺民對新朝的威脅依然時時可見,一度與滿人結盟的藩王和邊疆部族亦群起叫陣,皇權的集中才剛剛開始鞏固,滿漢文化之間的扞格化解不易。曹寅對其生涯或許幾經盤算,不過這一切似乎不太需要;環境對他的眷顧一如對他的先人。這不是一個讓新人如魚得水的時代,它比較適合邁向新時代的舊人;在一六七五年這一年,還有什麼比得上一個有著古典漢文化涵養的滿人包衣更令人嘆為觀止的呢?曹寅就是這樣的人。像曹寅這樣的人具有多重用途,而他成功、忠誠的賞酬是相當高的。
不過,到了曹寅嗣子曹頫的時代,他遭遇到的是雍正皇帝(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皇權集中的局面,而皇權的集中化往往是通過整肅閣臣來實現。曹頫沒有能力適應這個時代,迎接這個時代新的挑戰,而導致家道中落。到了曹寅的孫子曹霑(雪芹),才來到故事的盡頭,他在乾隆盛世的時代膝下虛懸、窮困潦倒。若非曹雪芹動心起念,追憶曹家的興衰起落,否則曹家有可能從此湮沒在故紙堆中。結果就有了《紅樓夢》這部小說,作者雖然尚未完稿,但這部小說普遍被視為中國小說的扛鼎之作。這部小說刻畫細膩,如今我們可以看到,在曹雪芹文學意象的背後,透露著他祖父曹寅真實的官宦生活和流金歲月。
若能綜合制度、文學、政治種種文獻,整體觀之,曹寅個性自然躍然紙上。他是一個嗜好美物的閒散之人;他在滿漢文化中,在騎射和詩賦中,在南方柔和氣候的清談機抒中,發現美好事物。曹寅飽滿的美學品味,同時取悅了滿人和漢人。曹寅有時會突然滿腔熱血、正義凜然,譬如康熙四十三年他有意大刀闊斧改革鹽政,又如康熙五十年他挺身撻伐科場醜聞的不公裁決;不過,他大體上還是安於隨波逐流。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也署理幾個有利可圖的肥缺,他懂得見風轉舵,利用機會謀利,但從來不竭澤而漁。
不必過度渲染曹寅個人的重要性。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於他的生平可以告訴我們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以及他所運作的那個制度架構。本研究的主旨,就是把曹寅的一生當作「典範」(paradigm,借用科學家對這個概念的定義)來呈現:「(科學)發現始於對反常異例的察覺,亦即,認識到自然現象與主導常態科學的典範預期不一致。然後,對反常異例的領域繼續從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調整典範理論而使得反常異例可以預期時,才停止探索。」
我從事這項研究的初衷,是因為曹寅的獨特性很難在清史中被歸類。隨著研究的開展,一切就愈來愈清晰,曹寅之所以顯得特殊,它反映出我們對清史的內容,對中國官僚體制的性質,有太多想當然爾的看法。如今,是康熙皇帝的私家臣屬,因而被外放到行省署理重要的財稅職務,皇上透過曹寅可以遂行財政控制大權。這種皇家私人的臣屬,自然超越京畿、各省官僚體系的行政流程,而這群人是可以被明確界定,其扮演的特殊功能也是可以被分析的。有鑑於西方先前的研究,對清朝頭一百年的各個面向幾乎沒有著墨,本書試圖自空白的歷史中,勾勒出這一變化多端的複雜時期,而本書的發現必然是試探、初步的。不過,假使我的立論可以成立,反常異例變得可以預期,那也稱得上是小小的發現了。
※孔恩(Thomas 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統一科學國際百科學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tied Science),2, NO.2, (Chicago, Unirersity of Chicage Press, 1962),頁五二至五三。
二版前言
本書自出版以來已歷經二十一年,其間我們對本書的兩位主角──康熙皇帝與其包衣曹寅──的認識,有著驚人的增長。康熙所收到的奏摺,連同他在奏摺上的硃批,已分別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影印付梓。而由曹寅與其子、嗣子草擬的奏摺,以及與他一同署理織造、充當皇上耳目的李煦、孫文成的奏摺也另行出版。北京典藏的清初檔案,如今已對學者開放,可與台北典藏的史料互為補充,而擲地有聲的中、英、日專書專論或剛剛完稿,或正在蘊釀之中,都大大深化我們對清代國家機器運作,皇帝與其官僚體系、家人關係的理解。
但是,真正促成有關曹家知識突然湧現的原因,是來自中國學者重燃對《紅樓夢》和其作者曹雪芹的神迷。以這部章回小說和其作者為研究宗旨的兩大叢刊於一九七九年創刊,發表了一系列的歷史資料、美學詮釋和深度論辯,令人嘆為觀止。《紅樓夢學刊》這份季刊係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小號字體印刷,每期平均約有三百四十六頁。而《紅樓夢研究》集刊,自一九七九年創刊以來,每年出版一至三輯,同樣是小號字體印刷,每輯篇幅大約有四百九十二頁。
《紅樓夢集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辦的。這些期刊的文章儘管多以小說中的角色為題,但每年總會有二十幾篇論文在某種程度上觸及曹家、曹家親友的歷史背景。
而這些雨後春筍般的學術成果,又會對本書的立論效度帶來什麼樣的衝擊?雖然我們對那個時代與曹家的了解因而大為拓展,但我認為我的基本立論還是站得住腳。其中有四點對我尤其重要。第一,曹寅與皇帝的特殊關係,而其源於兩人少年時代的接觸,曹家的包衣身分,以及皇家保母選自與曹家有關的家庭這個事實。第二,這種特殊的地位對於理解曹寅的仕途是如何開展,密摺制度何以發展成為只有皇帝可以看見祕密情報的管道,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曹寅闖進的是一個奇異的文化和經濟世界,它超脫了區隔滿、漢領域的顯著藩籬。第四,曹家位於南京(江寧)的萬貫家產,以及曹家在雍正朝期間的隕落,必然令曹雪芹深深感嘆,因而充實了《紅樓夢》的重要面向。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對學術新成果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表達敬意,同時我也要承認,如果今天重寫此書的話,一定會十分不同。在英文出版物中,陶博(Preston Torbert)、張得昌(Chang Te-Ch’ang)、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分別扭轉了我們對包衣組織、內務府財務,以及這時期稅收的理解。吳秀良(Silas Wu)分析了整個奏摺制度,並揭示康熙與諸皇子之間意想不到的面向。白蒂(Hilary Beattie)、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改變了我們對滿人征服漢人及其對漢人地方社會衝擊的看法。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則對個人生活中滿漢的融合提出新見地,而白彬菊(Beatirce Bartlett)的著作全然推翻了我們評斷皇帝決策的方式。
這些著作僅牽涉到拙作的歷史背景而非核心論證,不過近來許多中文研究成果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陳國棟(Ch’en kuo-tung)、趙中孚、張書才深入探討曹家入旗的問題。朱淡文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八月《紅樓夢學刊》的文章謙稱為〈曹寅小考〉,詳細剝析曹寅幼時為康熙的伴讀,而且他的母親姓顧不姓孫,所以一代大儒顧景星是曹寅的舅舅。顧平旦認為曹寅略懂日文(《紅樓夢學刊》: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王利器加入有關曹雪芹家世的爭論,重申小說家的母親馬氏,在丈夫──即曹寅的兒子曹顒──過世後生下曹雪芹(類似我在本書的主張)。這反駁了馮其庸的說法(載於馮的著作和《紅樓夢學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論文),宣稱曹雪芹是曹頫的親生兒子,而曹頫則是堂弟曹宣的親生兒子。而從北京檔案的文獻發現,又推翻了王利器、馮其庸(以及我自己)的觀點,該文獻事涉康熙二十九年曹寅南下接任蘇州織造一職之前為家人捐納監生一事。根據張書才等人的分析(載於《紅樓夢學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顯示曹寅在康熙二十九年時有一個三歲大的親生兒子曹顏;而當時二十九歲的弟弟曹荃有三個兒子:曹順(十三歲)、曹頔(五歲),而曹顒當時才兩歲大。不過,曹寅過繼了弟弟的長子曹順為嗣子,這或許是出於擔心自己這支香火可能無法延續的緣故。
近來有關李煦一家的研究幾乎也同等複雜,其中最為重要的或許要屬徐恭時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一九八○年十一月)所發表的論文。徐恭時認為李煦與康熙的關係,較之曹寅更為複雜,因為李煦的母親文氏是康熙的保母之一,而李煦的妻子王氏,又是康熙妃子的姨媽,這位皇妃替皇帝至少生了三個兒子。曹寅則是娶了李煦的堂妹。中國大陸這些細膩的研究,無疑逐漸扭轉我們對曹家的認識,儘管主要面貌不會因此而改觀;而台灣方面的研究,在質方面雖可與中國大陸並駕齊驅,唯在數量上不及中國大陸。
今年有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湧入《紅樓夢》大觀園裡的曲徑亭閣,這與在神隱文本裡上窮碧落下黃泉般挖掘人名的做法截然不同。這座園林出自曹雪芹的想像,以及他對先祖曹寅一生繁華的追念,北京當局如今則是以混凝土、木材、瓦塊、灰石予以重葺它,而上海也正在打造另一處的大觀園。曹雪芹幻夢的世界,如今化為中國式的迪士尼樂園,裡面還供應冷飲和冰棒。
對於隨著遊園而被激發出學術熱情,想要加入紅學論戰的人而言,如今也有了新的工具協助他們去探索。深圳大學的電算中心與中文系聯手合作,開發出一套可以搜尋小說全文的軟體系統。磁碟上的軟體,可以在所有IBM及其相容的個人電腦上操作,只須幾秒鐘,就可以依下列主題對《紅樓夢》進行全文的檢索:雙音節詞語出現的頻率、助動詞的用法、擬聲詞、教育、服飾、料理飲品、醫藥、鬼魂和風流韻事。而曹寅可就沒這麼好命了。
史景遷
一九八七年九月於紐海文
※譯按:史景遷在上文引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分別提到曹寅的弟弟曹宣和曹荃。其實曹宣即是曹荃。曹宣字子猷,別號芷園、筠石,因避康熙帝玄燁(玄、宣音近似)諱而改名曹荃。
初版前言
本書描述清史曹寅(一六五八至一七一二年)的生平,但這並不是一本傳記。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的時代構連,並給予制度同等的重視。所以,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裡,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中國正史裡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織造、巡鹽御史時,這意味著什麼。曹寅的所做所為自然要予以關注;但他可能做什麼同樣重要,或者,更精準地說,律例規定他應該做什麼,與曹寅同時代的人處在相同的官位時又會做什麼。
本書涵括的範圍超過曹寅的一生。本書勾勒的情節始於曹寅祖父所處滿人鞏...
目錄
初版序言
二版序言
第一章 內務府
第二章 京城與蘇州,詩詞與社交
第三章 織造曹寅
第四章 南巡
第五章 兩淮鹽政
第六章 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 曹家的沒落
附錄
一、生絲價格: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1712-1726)
二、江蘇米價: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06-1722)
三、新種米產量:康熙五十四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15-1722)
四、有關《紅樓夢》的假設
註釋
初版序言
二版序言
第一章 內務府
第二章 京城與蘇州,詩詞與社交
第三章 織造曹寅
第四章 南巡
第五章 兩淮鹽政
第六章 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 曹家的沒落
附錄
一、生絲價格: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1712-1726)
二、江蘇米價: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06-1722)
三、新種米產量:康熙五十四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15-1722)
四、有關《紅樓夢》的假設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