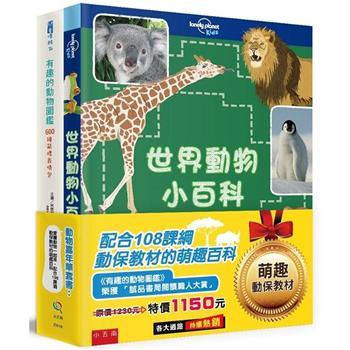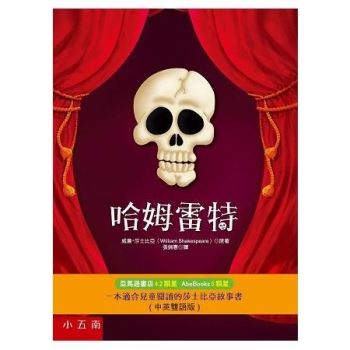第二章 堯舜的治化
〈堯典〉所載,為堯、舜時事○1。將堯、舜的法天、知人、仁民、愛物,以及施政布德的行事,用簡約樸質的文字,描繪得秩然有序。細玩其文,使我們對於先聖帝王的修為、形象,不僅油然而起敬慕之心,同時更使我們覺得,也惟有如此,才是最為適中、最為當行,而心安理得的舉措。這也就難怪歷代硏讀〈堯典〉的人,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帝王之學,盡在於斯矣」了。數千年來,不只是形成了我國文化的重心,而且更為有國有家的人,樹立了一個永遠無法改變的典型。於此,不僅可以窺探我國文化的淵源,同時更表現了一個當然之理的王道思想。孔子的祖述堯舜,孟子的言必稱堯舜,固為我們耳熟能詳,即使先秦各派各家,亦無不以堯舜是稱。凡此記載,可使我們了解到:往大處說,治國平天下,固然要以此為典範;往小處說,就是日常處人、應物、行事,又何嘗能不講求此「當然之理」的行為?基於這個理由,是以不揣淺陋,敢將一愚之私,冒昧地提出來,就敎於方家。
一、堯的形象
古籍所載,文字雖然簡質,可是如論其描繪技巧,我們細加玩味之餘,覺得實不讓於今人。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古人是如何的刻畫。經文說: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僅僅用了二十七個字,就將堯的修為、形象,和盤托出,使我們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我們現在所以不覺得文字生動、傳神,甚至還有隔膜,不能體會的感覺,這是因為語言的轉變所致,現在如果把原文寫成:
當古代的時候,有一位帝堯,名放勳;他,敬事節用,就像日月一樣,照臨四方,洞察人情;治理人民,完全效法天地自然的文理,敏於通達的思考,態度寬容、溫和可親,同時又能誠心誠意地為人民犧牲、奉獻而不懈於位,更能讓賢推德;因此,他的德澤,能廣被四海,感通上天下民。
而對原文的隔膜,不就馬上可以消除了嗎?不僅隔膜可以消除,同時堯的形象,也就立刻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這不也就是《論語‧泰伯篇》孔子所說:「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嗎?由這段話,更可進而使我們體察到,堯的盛德,已經到了高不可及的地步。這又叫人民如何能名?一位帝王,有德若是,還不能導國家於正途,得到人民的擁護、愛戴?這種形象的建立,對後世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其價值又豈是我們可以估計的?這使得歷代的帝王們,不但知所修德,同時還要知所愛民。凡不修德、不愛民的君主,均為人民所共棄。而《中庸》所說:「大德者必得其位。」《大學》所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的見解,應當是從此產生的。我們中國的文化特色,在這裏似乎也可以看出一點端倪。而「仲尼的祖述堯舜」,孟子的「言必稱堯舜」,乃至形成儒家思想的中心,當非偶然。這種完全出於領悟、自覺的德治主張,不也符合於現在的民主政治?起碼並無衝突、違背的地方。
二、堯的治化
堯的治國化民,主張由明德而親民。這種主張,為孔子所承。《論語‧為政篇》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正是對堯德治的闡發?既講德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修身。所謂修身,簡言之,就是正己。亦即孔子所說「己身正不令而行」之意。而修身之要,在於明德。能明德,方可親民、化民,而使四海歸心。是以經文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這種由修身而親民、由近及遠、逐次推展的為政措施,顯然為儒家所承。而《大學》說:「明德、親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不就正是這段文字的說明?經文中的克明俊德,就是修身,親九族就是親民。協和萬邦,就是平天下,黎民於變時雍,是寫堯平天下之後的和睦太平景象。〈堯典〉僅用了三十個字,就能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渾然賅括,這的確不能不使我們讚歎其描繪技巧的高明。尤其是在行文層次上的推展,更可見其已經到達了爐火純靑的地步。在這種逐漸推展的過程中,帶給我們的啟示,那就是先聖帝王,不僅貴德,而尤其貴行。也只有在行中,方可愈見其德的可貴。《大學》所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訓示,豈是虛言?只是我們未加深考詳察罷了。
三、堯的作為
文化是隨著生活的需要而產生。換句話說,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化。在堯、舜的那個時代,生活文明,究竟到達何種程度,現在我們雖然無法肯定,但是觀象授時,經近人董作賓先生的考證,應該相信是確切不誤的○2。由於觀象授時的確定,這可使我們想像到,當堯舜時代,很可能已經是各部落定居下來,從事開墾、農、牧、漁兼有的時代。因為有此需要,所以才有此作為。天文學家高平子先生說:「我們先民為什麼對於天象曆數有這樣濃厚的興趣呢?第一是中國民族在黃河流域,很早就建立起一種農業社會。而對於季節來臨的預推,是農業社會最迫切的要求。第二是在中國傳統的宗敎觀念裏,宇宙的最高統治者——不論其名為『上帝』(多見於詩經),為『眞宰』(見於莊子),為『天』(各古籍普通應用)——和有形的蒼蒼者天,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因此觀象敬天,成為『天子』的一件政治上和宗敎上的雙重任務。」○3又說:「所謂曆法者,其要在於順應天行,制為年月日時配合之規定,以預期天象之回復,節候之來臨,俾人類社會之活動,如耕種、漁牧、狩獵、航行、營建、修繕一切民生日用之作息,皆可納入於一定週期之中,凡事有所準備。」○4這種見解和說法,我們是樂意舉雙手贊同的。因此,〈堯典〉中的「敬授民時」,是完全為了生活上的迫切需要,而不得不有的措施。這也可說是我先民向天空發展的第一步,是值得一提的大事。經文說: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經文中所說的「乃命羲和」,是槪括的說法,包含自下文「分命」以後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子,命他們分別掌理春、夏、秋、冬四時的工作。鄭氏康成認為羲、和乃重黎之後,掌天地之官。又疑羲和為羲伯和伯○5。這種見解,可能是受了周官六卿所列天地四時、各有所掌,遂以為羲和為羲伯、和伯掌天地,再以下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這樣才能與周官六卿的說法相合。其不知周官六卿之制,在唐虞之世,可能尚未形成,是以羲和四子,不可以為六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仍以為是命羲和四子。這說法,我們認為才是正確的。
經文所言,一方面道出了堯的法天以授民時,同時也是堯用人的開始。他首先任命羲、和四子,敬順天道,取法自然,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轉,以求得季節上的契合,然後再將時令,敬謹地傳授給人民。因此在〈堯典〉中,也確實能分明地將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象,展現在我們的眼前。您看,他寫春天的景象,是多麼地明晰,經文說: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ㄐㄩㄝˊ)民析,鳥獸孳尾。
總命以後,再分別地予以指派,使職有所專,所以就再特別指命羲仲為春官,居住在東海附近的嵎夷一帶、有一個叫暘谷的地方,每天恭敬地迎接初昇的朝陽,並指導人民治理春耕。等到日夜的長度相等,在傍晚朱雀星宿全部出現的時候,就依此種景象,把這天定為春分。這時人民在白天已分散在田野展開春天的各項工作,鳥獸也開始交尾乳化而生了。這樣的描述,雖然很簡略,但因能掌握季節的特徵,所以春天的景象,卻能很淸楚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春天寫完之後,接著就描述夏天。經文說: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首先在這裏必須提出解說的,第一為「申命」的申字,作「重」解,這是在總命之後,又以專職分命而加重申之意,與前文「分命」的分字是互文。就意義說是相同的。第二為「宅南交」這一句,根據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說:「宅南交,當以宅南為句,交上當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第三為「南訛」,僞孔說:「訛,化也。平敘南方化育之事。」孫星衍說:「訛,俗字,當為譌。」《史記》作南為。《索隱》說:「為,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關於「南訛」的解說,我們認為《索隱》的說法為優。第四為「厥民因」的因字。孫星衍以為:「釋詁謂儴、因也。說文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蓋以襄通儴也。」因氣溫上升而解衣耕作,非常合於時宜。我們對以上的字詞,先作分析了解,然後再來欣賞經文,就容易多了。那是說:再特別指任羲叔為夏官,居住在南方的大交山,勸導農民耕作,並敬謹地祭日以測量其影的長度,等到白天最長,夜晚最短,而且在黃昏大火心星出現在南方的時候,就定這天為夏至。這時人民也因氣溫的上升而解衣耕作,而鳥獸的毛,也稀疏得可以看到皮膚。夏天的景象既是如此,而秋天又是怎樣的呢?經文說: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鳥獸毛毨(ㄒㄧㄢˇ)。
這段經文比較平易,要不著在文字上多作解釋,就可看出它的含義。那是說:又特別指派和仲為秋官,居住在西土一個叫昧谷的地方,每天敬謹地送別西下的夕陽,並勸導人民從事秋收的工作,等到夜間和白天一樣長、並在傍晚虛星出現在正南方的時候,就依此種景象,把這天定為秋分。這時人民和易可親(秋收的喜悅),鳥獸也都生出了整齊潔淨的新毛。到了冬天,景象又有所不同,經文也有同樣明晰的描繪。經文說: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ㄇㄠˇ),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ㄖㄨㄥˇ)毛。
這是說:又特別任命和叔為冬官,居住在北方一個叫幽都的地方,勸導人民謹愼蓋藏,小心門戶。冬天日短夜長,等到昴星傍晚出現在正南方的時候,就依此種景象,定這天為冬至。這時人民家家都躱在屋內生火取暖,鳥獸也生長出厚厚的細毛。
這種畫龍點睛的描述,確實帶給我們一個明晰的槪念。尤其是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人民,會覺得格外親切而眞實。即使是熱帶的人民,看了之後,也會有分明的感覺。現在仍然在流行著的所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農諺,大槪就是我國農業社會,隨著季節的轉移,而所作的實際的適應行為吧。這種固定的分派任命,目的在使職有所專,而所謂的勸導人民耕作蓋藏,也只不過是依時令的來臨,告訴人民應作的準備(案:《正義》云:「因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6其他各官,當可由此推知。),其主要任務,乃在觀測日月的運轉,氣溫的升降,以及動植物的生態變化,統計出一個大原則,來作為制定曆法的主要參考。詳細情形,而今我們無從得知,不過這種做事的方法,卻是非常有條理、有次序、有規則的,套句現在的話說,那也是十分科學的。
關於四宅(宅嵎夷、宅南、宅西、宅朔方)的說法,先儒多就經文所載為釋,總希望能找出一個實在的地方,故不惜多方探賾、引申,然而古史幽邈,終難詳悉,是以所說不一,比較之下,愚以為三國曹魏王肅的說法,較為可取。他說:「(四宅)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這意思是說:負責觀測春、夏、秋、冬天象的官署,均設在帝都,而測候所則設在四方經文所指載之地,將他們所觀測的實際資料,不時的向官署報告,而各官署加以整理後,再向國家元首報告,然後再根據四方實際觀測的眞實紀錄,而制成曆法,這當然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日。近人丁山於其所著〈羲和四宅說〉一文中說:「此四方所指,竊又疑其皆京師近郊之地。……蓋因羲和所居之地,立土圭,測日景,造為官府,猶後世觀象臺、天文臺之因其職而名其官府焉。觀象天文,每世之設,皆在京師,是知暘谷、幽都,必不出平陽之野(帝王世紀:堯都平陽)。後之學者,不知于平陽四郊求羲和四宅,以九夷當『嵎夷』,以交趾當『南交』,以山海經神話之『幽都』,當虞書之『幽都』,亦見其枘鑿矣。總之,虞書四宅,其制度蓋猶晉之靈臺,隋之秘書省,唐之司天臺,宋之太史局,元之太史院,明之欽天監,蓋觀象者所居官府之名。」○7這說法,我們是同意的。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堯的觀象授時,確實是一件大事,而歷時亦長,由經文的記載,也可以使我們體驗得出。經文說: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這是觀測天象的總成績,它在當時明顯的價值是「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儘管古人以為太陽繞地而行,然而其得日數,卻與現在所用的陽曆(地球繞日一周所需日數)相同,均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經文所說三百六十六日的原因,是舉的成數,這在古籍的注解中,可以看得很淸楚。至於月繞地球一周所需的時間,是二十九日多一些,所以月有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日)的分別,合大小盡以每年十二個月計算,全年僅有三百五十四、五日,較地球繞太陽實際所需的時間(日數),相差十餘日,故必須閏月以補足其相差的日數。所以才有三年一閏,五年二閏,十九年七閏的出現。這是古人一個很大的發明,如不置閏,就難以穩定的控制季節,若干年之後,那就要春秋倒置,而冬行夏令了。由於我們的祖先,很早就發明了這樣完善的曆法以「授民時」,並借以釐定百官的職掌,使依時而行,所以各種事功,才能在分、至、啟、閉不失其常的狀態下,而分別的盛興起來。
一件事功的完成,當然要仰賴於眞知灼見,以及完整的計畫和正確的領導。而知人善任,尤不可少。讀經至此,我們應該得到很大的啟示才對。茲將《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所製有關觀象授時圖附此,借供參考。
四、堯的求賢
我們遍觀中外古今,凡有道之君,明哲之主,未有不求賢若渴,以治其國的。以一人的知能有限,而衆人的才力無窮,是以欲有所作為,必借衆賢人的力量,方克有濟,捨此而期於國治,那無異於緣木求魚。堯本來就是一位聖君,不僅有見於此,而且也為後世立下了典範,茲就其任事、讓國二端,分別言之於後:
(一)、求賢任事
才難之歎,無世無之。而當堯之時,求賢任事,尤見不易。由以下經文的記載,足可以支持我們的這種看法。經文一則說: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ㄧㄣˊ)訟可乎!
堯有感於求賢的不易,而一人之所見有限,所以才發出「誰能順應時勢為我登用賢才」的慨歎。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這個問題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其他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根本也就要不著多事徵求了。大臣放齊,馬上就向帝堯推薦說:「您的胤子丹朱,有知人之明,他一定可以把這個工作做得很好。」帝堯以很驚異的口吻說:「丹朱,他口不道忠信之言,又好逞口舌之爭,如何可以!」再則說: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ㄔㄢ)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當堯之時,所面臨的問題,就經文所言,是百事待舉。在這種情況下,焉有聖君在位,而不積極的從事於各種建設,而謀求增進人民福祉的?統籌運用人才的人既不可得,因而只有退而求其次,所以他也就於不知不覺間,發出了「誰能順利地為我完成國家各種建設」的嗟歎。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堯的無時不以國事為憂,不以民生為懷的心胸了。四凶之一的驩兜向帝堯推薦說:「共工可以,而今他正在聚集人民、從事各種建設呢!」帝堯聽了之後,馬上長歎一聲說:「噢!他說話非常動聽,可是當他實際從事的時候,卻往往違背命令,在表面看來似很恭順,其實卻沒有比他再傲慢的了,因為他最善於陽奉陰違。」三則說: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ㄍㄨㄣˇ)哉。帝曰:吁!咈(ㄈㄛˊ)哉!方命圮(ㄆㄧˇ)族。岳曰:异(ㄧˋ)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高重源說:「近年地質學家,就冰山、冰川所存留的古代遺跡,證明歐、美各洲,在洪荒之世,均有洪水的跡象。我國江河發源的地方,今尚存有雪山冰川不少,可知古代洪水之患,並非我國特有的事情。」○8驗諸我國古籍所載,這說法是不錯的。既然堯時有洪水為害,而堯又是一位聖君,治理洪水,應為當務之急,這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當堯目睹「滾滾大水,無邊無際,圍繞著大山,淹沒了丘陵浩浩滔天,正在為害著地方,人民也無不在歎息」的情況下,也就不自覺的發出「有沒有能治水的人呢」悲憫之言。當時諸侯之長的四岳及在朝的衆大臣同聲回答說:「鯀可以。」那知帝堯對鯀早已有所察知,立即說:「不可以,他違抗命令,處事不合常理,不能與同事和睦相處。」四岳向堯建議說:「就請先舉用他吧!試用可以的話,再正式任命好了。」在這種不得已的情形下,堯也只好勉強以為了。所以就接著說:「那就讓他去治水吧!不過要敬愼從事啊!」後來經過九年的漫長歲月,鯀並沒有完成治水的功績。
從以上三段經文的敘述中,我們不僅可以深切地了解堯有知人之明。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大公無私的風範,以及不遮掩其「敎子無方」的家醜。這都是常人所做不到的。由於堯能知其子的「嚚訟」之惡,故能不以一人病天下。驩兜、共工,為四凶之二,互相推薦,堯深知其「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是以不用。而最後的用鯀,實因當時「未得能者故也」○9。因此,雖然明知其「方命圮族」,可是面對「湯湯洪流」,耳聞「下民嗟歎之聲」,又如何能不姑且一試,以寄望人民的痛苦,早日得以解除呢?後以事實證明,堯的觀察,是絲毫不爽的。這不就是堯有知人之明的確證?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尚書:華夏的曙光的圖書 |
 |
尚書:華夏的曙光 作者:李振興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7-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尚書:華夏的曙光
《尚書》是我華夏民族最早的一部史料彙編,內容包括《虞書》(堯舜時代)、《夏書》、《商書》、《周書》。所記大多是政治性的文誥。《尚書》是文化的根源,也是一部「政書」,包羅內聖外王之理,,乃至天文、地理、敎育、經濟、官制、刑律等,無不含蘊其中。李教授改寫時採取力求淺近的做法,盡量做到深入淺出,使它大衆化、通俗化。讓人願意接近它、閱讀它,進一步借以喚起國人硏究《尚書》的興趣,以期達到發揚固有文化的終極目標。
作者簡介:
國家文學博士。
曾任:政大中文系教授。
現已退休。
著作:《說文地理圖考》、《王肅之經學》、《尚書流洐及大義探討》、《尚書學術》等。注譯作品有《東萊左氏博議》(與簡宗梧教授合譯)、《顏氏家訓》。
章節試閱
第二章 堯舜的治化
〈堯典〉所載,為堯、舜時事○1。將堯、舜的法天、知人、仁民、愛物,以及施政布德的行事,用簡約樸質的文字,描繪得秩然有序。細玩其文,使我們對於先聖帝王的修為、形象,不僅油然而起敬慕之心,同時更使我們覺得,也惟有如此,才是最為適中、最為當行,而心安理得的舉措。這也就難怪歷代硏讀〈堯典〉的人,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帝王之學,盡在於斯矣」了。數千年來,不只是形成了我國文化的重心,而且更為有國有家的人,樹立了一個永遠無法改變的典型。於此,不僅可以窺探我國文化的淵源,同時更表現了一個當然之...
〈堯典〉所載,為堯、舜時事○1。將堯、舜的法天、知人、仁民、愛物,以及施政布德的行事,用簡約樸質的文字,描繪得秩然有序。細玩其文,使我們對於先聖帝王的修為、形象,不僅油然而起敬慕之心,同時更使我們覺得,也惟有如此,才是最為適中、最為當行,而心安理得的舉措。這也就難怪歷代硏讀〈堯典〉的人,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帝王之學,盡在於斯矣」了。數千年來,不只是形成了我國文化的重心,而且更為有國有家的人,樹立了一個永遠無法改變的典型。於此,不僅可以窺探我國文化的淵源,同時更表現了一個當然之...
»看全部
目錄
【出版的話】
【導讀】先民智慧的曙光 李振興
第一章 認識《尚書》
一、為什麼稱作《尚書》
二、《尚書》的編集
三、今文《尚書》
四、古文《尚書》
五、偽古文《尚書》
六、《尚書》的大、小序
七、《尚書》的流傳 八、應有的體認
第二章 堯舜的治化
一、堯的形象
二、堯的治化
三、堯的作為
四、堯的求賢
五、舜的攝政
六、舜的即位
七、結語
第三章 皋陶陳謨
一、前言
二、大義探討
三、結語
第四章 禹貢山水
一、禹貢...
【導讀】先民智慧的曙光 李振興
第一章 認識《尚書》
一、為什麼稱作《尚書》
二、《尚書》的編集
三、今文《尚書》
四、古文《尚書》
五、偽古文《尚書》
六、《尚書》的大、小序
七、《尚書》的流傳 八、應有的體認
第二章 堯舜的治化
一、堯的形象
二、堯的治化
三、堯的作為
四、堯的求賢
五、舜的攝政
六、舜的即位
七、結語
第三章 皋陶陳謨
一、前言
二、大義探討
三、結語
第四章 禹貢山水
一、禹貢...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振興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7-20 ISBN/ISSN:978957135590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