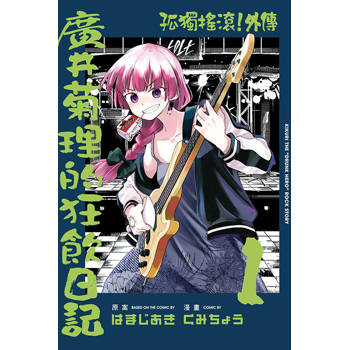推薦序
薛瑞柏醫師不僅是位傑出的精神科醫師,同時也是勇敢的抗癌鬥士。在三十一歲那年不幸發現罹患腦瘤,本著醫師與科學家的研究精神,薛瑞柏醫師深入鑽研癌症相關的各種研究,彙整抗癌的自然保健方法,為癌症的防治提供紮實的科學基礎,並出版其前一本著作《自然就會抗癌》。此書在世界各國都引起極大迴響,並被翻譯成三十五國語言於五十個國家出版。書中強調,每個人體內都有癌細胞潛伏,但造物者同時為身體設計了精密的防禦機制,只要透過營養、運動、心靈等調整就能啟動這機制。巧合的是,薛瑞柏醫師的觀念與我多年來推廣的預防醫學完全相同。除了飲食、運動、呼吸、睡眠、壓力等種種生活習氣的調整,我個人認為健康的關鍵,還是在心念轉變。當我們以轉變的心念重新去理解世界或幫助他人時,其實才真正踏出自我療癒的第一步。
與癌症和平共存了十九年之後,薛瑞柏醫師發現腦瘤復發且情況不樂觀。即使如此,薛瑞柏醫師仍勇敢面對,除了配合專業醫療協助,也持續運用營養、瑜伽和打坐冥想等方法積極對抗病魔。在本書《我們能說好多次再見》中,薛瑞柏醫師真誠地自我省思,多年來由於對工作的熱愛而忽略身體極限。長時間強忍時差、與體力透支在世界各國奔波,過度勞累導致身體節奏紊亂、癌症復發,但他與癌症多年共存的經驗遠超過醫學上的預後值,也早已是成功抗癌的最佳範例。事實上,疾病受到體質、環境、遺傳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疾病的復發也不代表努力付諸流水。健康要靠自己主動積極追求而得,並非被動等待而來。如果不能深入檢視及調整生活習氣,則我們離應有的圴衡和諧只會越來越遠。
薛瑞柏醫師運用率真細膩的筆觸陳述對抗病魔的無助、恐懼,脆弱時家人朋友如何成為最有力的後盾,真摯的文字刻劃觸人心弦。難能可貴的是,薛瑞柏醫師以自身作為示範,分享在生命的關鍵時刻如何平和且心存感恩,同時不放棄任何可能痊癒的希望,讓親友與自己的道別不會是生命的最後一次再見。如此樂觀與豁達的態度也正是本書希望傳達給所有讀者的。在我個人多年的臨床經驗也見到許多類似的實例,在面臨重大疾病打擊時,能夠樂觀且不放棄希望的病患往往會有較好的預後效果。即使面臨生命的威脅,正向的病患把每個當下都視為上天所賜予的禮物,謙遜並坦然面對人生的恆常與無常。相反地,以憎恨埋怨的負向情緒面對疾病的病患,往往把生病的責任歸咎他人,不僅治療的效果不佳,離開人世時也可能抱持沉重的遺憾。
面對未知,我們不免感到恐懼,對於疾病的不安有如塵埃覆蓋心靈。放下恐懼,最好且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回到慈悲。慈悲的力量至柔卻也最剛強,唯有抱持感恩慈悲的念頭,我們才能無條件接受生命的原貌。當我們心存法喜且從容面對順逆境,正向樂觀的態度會為我們帶來韌性與勇氣。對於課業、工作、或生活的一切,我們總是做好準備功課。事實上,如何坦然面對人生的最後一刻,也是每個人都應該準備的心靈功課。人生是持續成長與淨化的旅程,種種經歷都是幫助修鍊琢磨的課程,生命終點,只是旅途的最後一個導師。
生老病死或種種人生旅程,好比天空下雨,雨珠落到樹葉,滴下入川,川流入海,蒸發後終究又回到大氣中。生命循環就如同花開花謝、四季輪替那般自然。生命中的每次行進、每個轉彎,都雕塑我們的心靈與智慧。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曾為維護健康,盡力實踐均衡與和諧,以最好的準備迎接每一天?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曾珍惜所有緣聚,不留遺憾,且不虛此行?生命中的許多疑惑,在《我們能說好多次再見》中都能找到解答。此次薛瑞柏醫師卸下醫師的身分,以病患的角度闡述與疾病摶鬥的心路歷程。雖然他在書中表示自己並無宗教信仰,但字裡行間不難發現,謙虛地傾聽自然,活出人與自然的和諧與榮耀,就是薛瑞柏醫師奉行的信仰。
楊定一(長庚生技、長庚大學、明志科大、長庚科大董事長)
後記
法蘭克林.賽文-薛瑞柏訪談
編輯:為什麼書寫《我們能說好多次再見》這本書,對大衛來說很重要?他希望讀者從這本書獲得什麼訊息?
法蘭克林:他想透過這本書向他的讀者說再見,並分享幾個有關末期疾病的議題,感性的和實際的都有。他寫到夜裡產生害怕狼人這種非理性的恐懼,也寫到他死時可能會有一道白光迎接他,他寫到如何維持尊嚴、懷抱希望,並提到比較實際的問題,譬如確定他的後事已經安排妥當。
這本書是既是醫師又是病患的大衛,面對重病時所寫下的獨一無二的見證,他希望對病人和看護都有幫助。
編輯:透過《自然就會抗癌》,大衛教導我們如何活得好,你是否認為,大衛有意透過《我們能說好多次再見》告訴讀者如何好好的死?
法蘭克林:這本書並非教人如何死得好,而是活得好,而且直到最後一刻。
大衛協助過無以計數生命走到盡頭的病患,而他本身也是癌症患者,由於身兼醫師和病患兩種身份,因此對死亡很熟悉。在這本書裡,他告訴我們面對恐懼時如何保持希望,當身體功能出現障礙無法自理時,如何付出愛並感受到愛,每天除了疲倦之外,如何賦予生活更多意義。
編輯:許多人面對罹患末期疾病的親友,不知該怎麼做或說些什麼,你認為在那段艱苦的時期大衛最喜歡聽到的話是什麼?對他幫助最大的舉動又是什麼?
法蘭克林:親朋好友的造訪是大衛最大的支助,並讓他覺得仍是「生命俱樂部」的一員。他不虛偽造作,反而讓原本不太自在的探病者放鬆心情,至於病患喜歡聽到的話,大衛寫道:「和一位跟病魔抗戰的人聊天並不難,你只需真心傾聽他並簡單地告訴他:『我為你的遭遇感到遺憾,我很難過,但我希望你趕快好起來,告訴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他對那些以為來說最後一次再見的親友說:「我們能說許多次再見。」打破可能發生的尷尬場面,而這句話也成為我們朋友之間的信條,甚至變成法文版書名,書出版時他還在世。末期病患對於時間和人情世故的認知,不同於前來探病並祝福病患早日康復的人,而允許並尊重這個差異很重要。
編輯:雖然治療無效,身體狀況明顯惡化,大衛在人生的最後一年如何保持樂觀的態度?他每天如何享受生命?
法蘭克林:大衛盡力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找到快樂,譬如朋友的來訪、聽音樂、看電影、一有機會就外出,以及吃,他寫道身體復原的徵兆之一是恢復食慾。他愛開玩笑,也被我們的笑話惹得哈哈大笑,讓我們感到很自在。當我們在照顧他的時候發生不幸的小事故,他會選擇包容,甚至苦中作樂。由於他的態度,和他在一起和照顧他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雖然身體狀況惡化,大衛仍然充滿希望,相信可以被治好,不過他同時料理後事。要在事實和希望之間取得平衡並不容易,你必須不斷地調適,而他告訴我們打坐協助他到達這個平衡。
編輯:大衛寫道他沒有完全遵守他在《自然就會抗癌》提出的建言,特別是他工作繁忙,操勞過度,經常到海外出差,上美國媒體談《自然就會抗癌》。他是否後悔人生最後幾年工作得如此賣力?
法蘭克林:他一點也不後悔,即便死前數週的最後一次訪談,他也這麼表示。為了幫助癌症病患有重新掌控生命的新體認和工具,他所展開的論戰對他意義重大。他說他寧可完成他所做的但只活到五十歲,也不願一事無成地活得更久。他非常喜歡結交新朋友,和聽眾溝通,發現新療法,他的人生很完滿,他為此感到很快樂,他唯一的遺憾是不能陪伴年幼的孩子長大。
編輯:在《我們能說好多次再見》一書裡,大衛寫道:「我可以感受到你對覆盆子和青花椰菜的信心已經開始動搖……我聽見你喃喃嘀咕:『如果自然抗癌療法的最佳代言人大衛,如果以自然抗癌的思想、吃飯、走動、生活的大衛自己都病倒,那麼《自然就會抗癌》還足以借鏡嗎?』」不過他仍然說他完全支持他在《自然就會抗癌》所提到的方法。他為何這麼說?為何這些方法沒防止大衛復發?
法蘭克林:大衛覺得他的復發可能會導致某些讀者誤以為《自然就會抗癌》所鼓吹的理念無益,當他想到有人不願採納他推薦的方法,只因為一個看似有理但不合邏輯的念頭,將他所寫的東西一筆勾消,他就感到痛心。對他來說,這就好比你不願做化療,只因為化療對別人沒用,數以千萬的癌症病患做過化療後還是死了,但是一般人面對癌症時,不會拒絕這個痛苦至極的療法。
作為《自然就會抗癌》的化身,大衛覺得他的死很可能引起巨大的負面效果,就像吉姆.費斯(Jim Fixx,於一九七七年推出了一本名為《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的書,提倡跑步對健康的好處,不過他本人卻於一九八四年跑步時心臟病發猝死。)在一九八四年跑步時心臟病發猝死,因此他寫這本書清楚重申他支持所寫的每一件事,甚至寫到他坦誠面對絕症,毫不掩飾。他希望藉由此書安撫和協助癌症病患,並繼續鼓勵他們為生命奮鬥。
終究只是一個臨床案例而不是一個科學實驗,他覺得有必要強調他的建議有堅固的科學證據做基礎,的確有益健康,而且不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大衛最初的預後頂多六年,但卻活了十九年,若說他從他的療法得到許多好處也很貼切,而他想將這些好處分享給他的讀者。
編輯:在《我們能說許多次再見》一書裡,大衛提到你和其他兩位弟弟一直堅如磐石地陪在他的身邊,因為你們讓他安心,跟他保證他的病沒有讓他產生太大的變化。那段期間裡,你們還在哪些方面給他慰藉?
法蘭克林:很幸運的是,我們四個兄弟感情融洽,隨時互相扶持。十九年前他第一次診斷出腦癌時,我們就在他身旁,二○○○年他第一度復發,我們也和他在一起,而這次我們很自然地陪伴他。當你病得很重,你需要喜愛的人協助你一起做繁瑣的決定,尤其是和醫療有關的重大決定。此外,也得處理比較實際的問題,如家庭、財務、身體疼痛,或更平凡但未必較不要緊的日常瑣事,如吃得好和睡得好。
而生病時有喜愛的親友陪在身邊,在心理上也很有幫助。比方說,大衛到了夜裡很怕吸血鬼和狼人,他雖然明知自己的恐懼不合理性,但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於是我們睡在他的病房裡好教他放心。當我們不能陪他時,我們央求表兄弟或朋友陪他,我們很幸運有個感情很好的大家庭。
編輯:大衛在這本書花了許多篇幅提到他的三個小孩,你覺得這本書多少也是寫給他們的一封信嗎?
法蘭克林:想到他將撇下孩子離開人世便讓他很傷心,他和他的長子沙夏有過多次感性的談話,當時十五歲的沙夏很想陪在他的身邊。不過另外兩個孩子;兩歲的查理和七個月的安娜,將對他們的父親沒有任何回憶。對大衛來說,能告訴他們離開他們讓他感到多麼難過是很重要的,他想留下一些回憶好教他們記得他。
編輯:大衛希望在既有的療程裡加上一個新型療法:為他的腫瘤量身製造一種「疫苗」,而你發現一個病患曾在比利時魯汶做過這種療法並改善病情,於是你帶大衛到魯汶做嘗試。你認為大衛盡可能嘗試各種另類療法,在心理上對他幫助?
法蘭克林:你必須一直抱著治癒的希望。腦癌一開始的預後便很糟糕,所以病患不覺得走投無路是非常重要的。大衛肯定不認輸的好處,不過必須有證實有效的新型療法做為後盾,而比利時魯汶的馮古爾教授所研發的腫瘤疫苗療法,的確產生一些壽命延長又沒有副作用的案例,所以值得一試。
在巴黎腫瘤醫師的建議下,大衛做了另一種療法:注射「癌思停」(Avastin,抗血管新生藥物),抑制供給腫瘤養份的微血管生長。這一次給他希望的是一些嚴謹的醫學研究證實該療法能幫助某些病患。不幸地,從臨床角度來看,這兩種療法對大衛都沒有奏效,不過卻讓他自覺擁有重新主宰自己的能力,能更積極對抗疾病。
作者大衛.賽文-薛瑞柏之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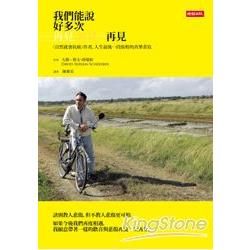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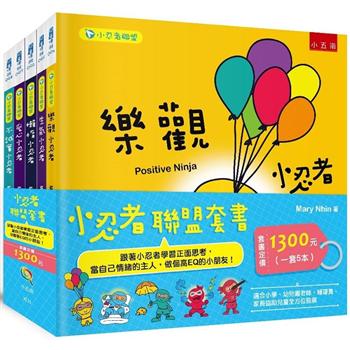
![如果停不下來,就先學會慢下來:52種簡單易行的正念練習,幫你化解壓力,找回專注力[靜心升級版] 如果停不下來,就先學會慢下來:52種簡單易行的正念練習,幫你化解壓力,找回專注力[靜心升級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17/2011760340723/2011760340723m.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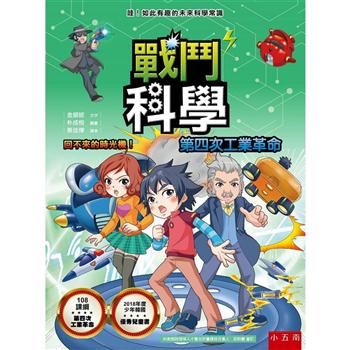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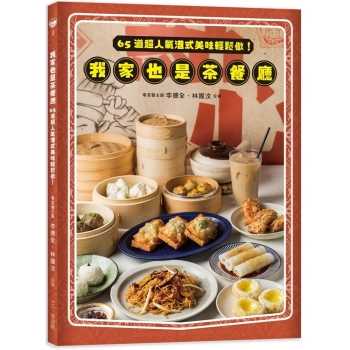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